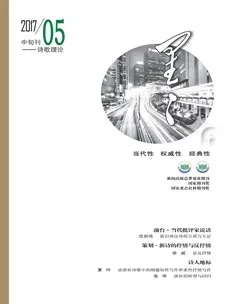嘗試定軌新詩傳統的史地情結
梁平一直以他沉穩的書寫行進在百年中國新詩的進程中。他的寫作,既有新詩發展的傳統賡續,也不失對文學藝術高端的執著追求,更有著精神性的現實徹照和深邃的內在經驗釋放,他基于詩歌自覺同時又肩負使命感的寫作,在當代詩壇卓有建樹。尤其是,當很多詩人在為地域書寫而囿于邊緣化的曉風殘月不能自拔時,他卻加載地域以歷史的寬闊與厚度,表現出駕馭現實題材的游刃有余。他的詩歌寫作最不缺乏的是縱橫捭闔的自信。他表達風趣,直入歷史中的現實,不高蹈、不艱澀玄虛和怪力亂神。在很大程度上,梁平的詩歌為飽受外界詬病的新詩建制與擴展提供了本質化的參照。
一
在《成都詞典》中,梁平站在家國情懷的高度,以有悖于歷史虛無主義的勇氣寫出了自我經驗中的當下,他筆下的詩行穿越歷史與現實、生活與時空,展現了厚重、大氣的中國式詩性語境。他的思考接地氣,自覺并軌“福克納半徑”,并進行了豐富性的開拓,機智而不高蹈,內蘊而富有力量。這種辨識度極高的風格給當下詩壇注入了“熟詩”的沉穩與勁道!
風骨是他詩歌的一大核心元素,讓他從意義指認與身體力行兩端,進入詩歌的當下,突入精神的現場。這么多年,他一直以一線詩人的活力予當代漢詩以鮮活的記憶與進階的拓展。在詩歌中,他力求以簡約的筆法和樸素的思辨探知歷史真相與現實語境的復雜體驗,最大限度地把個人化的筆觸公開化公共化,因此我們看到訴諸于筆端的詩意,總是呈現開放的姿態,詩行中的脈絡凝含著歷史深意與生活妙悟。在對歷史、現實、文化和個人精神世界的感悟與思考的全面精進中,梁平的表現已經為詩壇公認。
這是梁平的追求,他在創辦《草堂》詩刊時宣稱的“有溫度有質感的大唐風骨,有顏面有尊嚴的當代詩歌”,即是對自我的詩心一份歸納、總結與期許,回到他的《成都詞典》中,寫實依然為他所愛,作為書寫一部“詞典”的出發點,無疑呈現了建構美學的決心,這些散落于成都的“地名”,不單單是景致的可觀,更有著歷史的可讀。在《惜字宮》里,本意為珍惜先人倉頡所造之字的來之不易,可詩人卻從“惜”里析出別樣的具有現實諷喻的深意——
越來越多的人不知道倉頡,/越來越多的人不識字。/與此最鄰近的另一條街的門洞里,/堆積了一堆寫字的人,/但寫字的不如不寫字的,/更不如算命的,兩個指頭一掐,/房子車子票子位子應有盡有,/滿腹雞零狗碎,一臉道貌岸然。(《惜字宮》第三節)
基于批判的詩性介入,梁平在詩行中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種帶著個人風骨的歷史思考。在詩意的打開過程中,他完全拋開了那種狹隘的屬地自戀情結的浮泛抒情,徹底擯棄了吆喝“土特產”一樣的發聲,而是即刻沉入內在,于深邃的時空中完成精神洞察,重構有價值的思辨,獲得歷史與現實交織的宏闊詩意。
通常,一個作家的風骨,必須建立在獨到見解和自主學理的精神遠涉之中,梁平詩歌里的風骨,和他的詩心息息相關,在泥沙俱下的詩歌現實,在甚囂塵上的文學環境里,他一直有著清醒的認知,保持著純種品味的職業操守,以及平行于現實又不拘泥于局限的氣度。作為詩人的梁平,其超邁顯而易見。這些年來,關于詩歌邊緣化的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梁平認為:“面對中國詩歌現狀,一切歸于詩歌陷入低谷、走向邊緣的哀怨都是無助的。只有經過認真打量,才知道這種哀怨和我們所接觸的詩歌真是大相徑庭。老實說,我對中國新詩發展到今天的那種堅實和多元形態充滿了樂觀,堅定我樂觀的理由,正是因為中國有詩歌的操守,中國更有詩人的操守。”
世界藝術史告訴我們,興起于西方19世紀美術思潮的寫實主義,逐步發展為涵蓋繪畫、文學和哲學的一種方興未艾的流派,且產生了巨大影響,卻由于過度的現實和實際糾纏而表現出對理想主義的排斥。但梁平筆下的“寫實”是包容了理想化的想象,他拒絕新寫實主義的婆婆媽媽,他的詩,力求去碎片,去虛妄,去不實,去言不由衷,去空洞無物,去表面濫情。
在中國,傳統文學視野里的寫實主義,充滿闡釋、反思、剛性與求是的情感基調。韓愈就主張“養氣”和“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強調“以輔時及物為道”……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世界,中國文學的筋骨就伴隨著仁義和道統生生不息,進而凝成彪炳千秋萬代的文化血脈。即便新詩百年,脫離政治語境的“詩言志”,意味更為純正,卻也一樣有著旺盛的生命。在新詩發展史上,無論是“以哲理做骨子”的宗白華,還是主張“中國詩歌一定要有我們自己民族特性”的艾青,抑或是“一生風骨凝成詩”的牛漢,都讓新詩傳統“風骨”猶存。他們作品的求真意志,無疑都能讓讀者感受到傳統文學氣度的無處不在。而梁平,顯然有著相襲而來的詩寫自覺,他的詩,灑脫而有節制,起筆收筆講究內在擴充、經驗決斷與意義環繞。
顯然,“現實”作為一種參照,其所接綴的“主義”并非一種概念化的指稱,而是詩人洞見現實現象,提煉精神結晶的文本表現。在《成都詞典》中,梁平的批判比以往更強力,諷喻更顯赫,他不美化現實所見,不顧忌命題潛伏的危險,文本的“手到擒來”與“目擊成詩”可能性增大了,淋漓地呈現出藝術性的尖刻與不留情面。
那天倉頡回到這條街上,/對我說他造字的時候,/給馬給驢都造了四條腿,盡管,/后來簡化了,簡化了也明白。/而牛字只造了一條腿,/那是他一時疏忽。/我告訴他也不重要了,/牛有牛的氣節,一條腿也能立地,/而現在的人即使兩條腿,/卻不能站直。(《惜字宮》第四節)
人性遽然的顯意,讓詩歌遠離軟骨病。作者運籌帷幄:黌門、落虹橋、燕魯公所、少城路、龍泉驛 、紗帽街、藩庫……這些成都歷史的胎記,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道道刻痕。如此大面積地專注于生活記憶的當下體悟,呈現出建構美學在當代詩歌中的多重投影,正如著名作家阿來說的寫出了“社會更寬廣的東西”。放眼當今漢語詩壇,梁平的“現實”不是憤青筆下嘩眾取寵的逆行火焰,而是地域及其人文景深的洞察、激情與理趣,是智性的形象化表達,這份詩學的沉實沒有安之若素之心,分行的有效性就會很可疑。在宏大的歷史面前,梁平因執有“入世”的深刻而全身心地享受著詩意的地理史學之美,感受著史實中的日常,因了大情懷的托底,故能撇開詩壇熱鬧,不管世相如何喧嘩,他都保有“一顆享受詩意的安靜的心”。
二
整體看,《成都詞典》是一部厚重的詩性“史記”,保有地理詩學的宏闊底蘊,文本格局有范,基本上都是4節,每一首都寫實而不拘泥于實景,有依托,有動靜,有聯想,有機智,既觀照了地域,又映照了古今,更主要的是能在當下性的詩意場景中對接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哲學的升階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文史,產生了別樣的詩學意義。詩人的思緒在史實與現實中翻云覆雨,游刃有余,展現了智性的自信和詩成天然的功力。
走馬的街上,/馬尾巴甩出的聲響,/比那時的辮子還要招搖。/辮子沒有階級,/馬屁股的肥碩與瘦削,/看得出花翎的尺碼。/一拐彎就是都督衙門,/都得滾落下馬,/官靴與馬蹄經過的路面,/印記高低深淺,/都是奴相。(《走馬街上》第一節)
鮮活的即景描寫與即刻的思維火焰媾合,生成活力四溢的詩性敘事,這是梁平的拿手好戲。與一般地域性詩歌因作者筆力不逮容易滑進鄉土頌歌的僵化戀曲不同的是,梁平能夠駕輕就熟地把率性之真與思考之深,恰到好處地點染出來,詩行中的聲色與無處不在的判斷,于尖銳而又節制的情感判罰中,歷史獲得了新生,而歷史背后的人性勾連,更加引人入勝。
我的前世,/文武百官里最低調的那位,/在皇城根下內急,把朝拜藩王的儀式,/沖得心猿意馬。照壁上赭色的漆泥,/水潤以后格外鮮艷。/藩王喜紅,那有質感的紅,/豐富了烏紗下的表情,/南門御河上的金水橋,/以及橋前的空地都耀眼了。/照壁上的紅,/再也沒有改變顏色。(《紅照壁》第一節)
“我”,作為書寫主體,“意識介入”一開始就被迅疾調動起來,詩人以大膽的夸張,穿越到歷史現場,進入“歷史官場”,見證“權力”的表情和“烏紗帽”影射下的人性齷齪。紅照壁的“紅”,把巨大隱喻下的專制性語境描述得淋漓盡致:“照壁上的紅很真實,/甚至比血統厚重。/金戈鐵馬,改朝換代,/御河的水,流淌一千種姿勢,/那紅,還淋漓。/紅照壁背后的意味”。一壁如鏡,照歷史,照古今,記錄官場現形:紅得畸形,紅得猥瑣和僵化。如果詩人僅僅是出離于憤怒,鞭撻過往的頑疾,這種單一層面的對立性思維,就沒有多大意義。顯然,梁平是懷有警覺的,他把自我的內省帶進了詩里,“前世的毛病遺傳給我,/竟沒有絲毫的羞恥和難堪。”;“……我的來生,/在我未知的地方懷抱荊條,/等著寫我。”自我教育是詩人靈魂度化的關鍵,也是詩歌求真問道的不二指標。像巴金老人的懺悔一樣,“我”有過的,我不回避,不僅說出來,還要寫下它們,是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審視的勇氣是詩歌卓立有度的關鍵因素。今天,不少詩人總是把自己抬得很高,如圣潔的神明,特偽。梁平的“真我”塑造,一定程度上,對詩界充斥的虛假起碼也是一個提醒。
梁平詩歌的最大特色是不拘泥于小格局、感覺化的意氣書寫,而是大開大合,集經驗性、知識性、藝術性、思想性于一爐,展現了當代新詩的正氣。他自如的表現手法,不拘的介入方式,穩重的建構思路,率真的推進氣勢,為碎片化、反智化、粗鄙化的當下漢詩修補了形象,榫接了傳統精華。《紅照壁》這首詩歌依然延續他大手筆的出神入化。以“小我”接入思考的真實,以“大我”提純詩意的成色。在一塊“紅照壁”上,展開了回望歷史的聲色犬馬、刀光劍影與前朝舊事,既有否定的立場發聲,亦有價值衡定的自我研判,更有看待生活與生命的超脫與淡定。詩起興于“我在”的視角,甫一打開,便轟轟烈烈,一瀉千里。值得注意的是,詩人雖情感傾瀉如洪,卻并未擠占理性邏輯對全詩的操控,縱橫捭闔中不乏批判的幽默閃現。詩開門見山于“我”,最后又戛然而止于“我”,鑒照于一壁,從前世分鏡頭到現實的公正辨析,收束于“等著寫我”的豪邁氣度。
三
梁平的作品兼具詩學、史學與理學價值,他的寫作始終堅守時代前沿,以今鑒古,在時間的河流里打撈歷史的沉船。美國詩人布羅茨基也說:“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很顯然,“巴蜀”是梁平詩歌記憶的全部,他一直身處于這片奇特的“地域”,在審視中體驗生活,在歷史的地域投影中探索與挖掘。梁平自己也說,“我的寫作有很強的地域性,我是希望構建我自己的詩意地理學。我很多作品很刻意寫重慶,寫四川……” 他生活的成都,市井與歷史的交匯,具有樣本意義,必然也給他留下難以忘卻的烙印,地域詩性與地理詩學,以及歷史文化與分行語境的多重融合,產生的能量巨大而深遠,因而在表達上,更有先機之鋒利。“我就是你的爺。/那一根壓死駱駝的草的遺言,/在舊時草垛之上成為經典,/草就成了正經八百的市。”(《草的市》)這首詩的前四行,如小說《百年孤獨》開篇的第一句話一樣,張力十足,耐人尋味。
《草的市》還折射出如此意味:在中國農耕時代的商業鏡像中,萬象的市井,匯聚了往來不絕的騾馬牲口。在商賈云集的古驛成都,人畜熙攘,草料補給等日常情景被詩人的想象捕捉,并賦予趣味性的細節以歷史光芒的閃動。“過往的騾馬,/在堆垛前蹬打幾下蹄子,/草就是銀子、布匹、肥皂和洋火,/留在了這條街上。”在歷史記憶里,草是通行的貨幣,可以兌換成銀子,也可以換取布匹等日用品。騾馬們吃飽喝足,“能夠再走三百里”——草讓商品貿易走得更快更遠。——這個頓悟,不正契合了“一帶一路”的深意?詩人對歷史的現實語境有著自己獨特的深入洞察和審美。“至于沾花的偏要惹草,/草很委屈,即使有例外,/也不能算草率。”在敘述中,歷史語境因詩意的習得而被重構,語言綿密流暢,沒有絲毫的疏離感,讀者從中最大限度地捕獲閱讀的智趣與快感。
“藝術家之有別于常人的,僅僅在于其感覺敏銳;他較易覺察世界上的美與丑,并予以生動描繪。”這是索爾仁尼琴在《為人類的藝術》中的一句切中肯綮的話,以此推論詩人梁平,便可探知他詩歌的藝術堅守,即借喻于人性,讓尖銳感閃耀在刀刃上,把歷史寫成火熱的現實。例如——
在根的血統上,/忠貞不二。在燈紅酒綠里,/草扎成繩索,勒欲望,/勒自己的非分。草的上流,/草的底層,似是而非,/在不溫不火的成都,/一首詩,熬盡了黑天與白夜。/草市街樓房長得很快,/水泥長成森林,草已稀缺,/再也找不到一根,/可以救命。(《草的市》末節)
梁平的詩歌中有敏銳、真摯、樸素的內核,因為他的身體里住著一個自由的靈魂,一直保持豐富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的思想見解。“在根的血統上,/忠貞不二。在燈紅酒綠里,/草扎成繩索,勒欲望,/勒自己的非分。”他約束自己的欲望,但又無限延伸自己的想象,在一首詩里“熬盡了黑天與白夜”。“草市街樓房長得很快,/水泥長成森林,草已稀缺,/再也找不到一根,/可以救命。”在細致的描述中,詩人把自己對人生、對生命的感悟加以形象化提煉,而更具藝術感染力;普通的生活場景一旦注入詩性情懷與文化思想,就能自動生成有溫度的精神立場。他用心探索和挖掘意象的共鳴,使這首詩歌具有了“一種精神上的高貴感”。
有人統計過,梁平所有創作的二分之一都是在抒寫故鄉,他竭盡所能去呈現生活的微芒,鉤沉瑣碎的歷史記憶,打撈世事遷謫下的地域符號,挽留正在消弭的人文情懷,讓詩性的文字在時空中穿插,去竭力復活歷史與今天的對應的可能。他深知在現代化進程中,許多古老的城市胎記正被推入徹底湮滅的危險境地,作為詩人的責擔,有必要從殘剩的地名回溯文明基因,破解宿命所厄的世道。《草的市》令詩人腳下的這片土地變得更加厚重、真實,語言在重溫歷史片段的同時,也在創造著世界,從而彰顯詩歌特有的文化含量和歷史智慧,這是詩歌難度的有效實踐,誠如梁平的自白:“我不是對這個城市的緬懷,而是在對這個城市幾千年歷史的追究、對這個城市的血緣以及我的血緣的指認,勾畫出我所以為的城市精神。”
四
審美紛呈的《成都詞典》,其推陳出新的豐富性緊系地域卻又視閾寬廣,也暗示了梁平在藝術創造上的審美個性,他的迂執大大超越了歷史詩學與詞條典故那種網格分割的單調。那些呈現在詩中的地名與場域,被詩人看作意義編碼的雄關漫道和精神的符號印記。詩人的眼光一旦觸碰它們,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坍塌與賡續,頹敗與新生,權謀與物理,消逝與挽留……就自成詩意的達觀。
是的,梁平是一個性格達觀的人,他深知,人類記憶中的歷史是避免不了碎片化的,但文化氣場的完整性可以或者只有詩歌才能串聯而成。這份“執意”讓我想起曼德爾施塔姆是詩句:“當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聲音里/聽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詩歌的意義被梁平點燃。他詩歌里的現實完全迥異于當下流行的被捧得過了頭的“現實主義”當紅詩人的行為藝術。那種捏造事實的“負面新聞分行體”不僅傷害了文學的尊嚴,也喪失了寫詩人的文學敬畏。同樣是人性批判,他的來頭有根,即出芽于歷史土壤。同樣是現實苛責,他的指向有度,因物緣情,始終張揚著理性的審美之光,具有穩健而積極的藝術魅力。猶如德瑞克·沃爾科特那樣,通過強烈的歷史感的恒定思索及感受,形成了詩歌領域的包容特質與“獨立于他繼承的任何傳統”的風格。
他遵守去蕪存菁的藝術方略,表現出導向煙火人間,同時也尊重技巧為藝術帶來的境界與魅力。他整合生活化的抒情與識見獨到的敘事于一體,造意與造境同步,在風趣而形象化的書寫中將地方性的詩意合理化與最大化。
氈房、帳篷、蒙古包遙遠了,/滿蒙馬背上馱來的家眷,/落地生根。日久天長隨了俗,/皇城根下的主,川劇園子的客,/與蜀的漢竹椅上品蓋碗茶,/喝單碗酒,擺唇寒齒徹的龍門陣。/成都盆底里的平原,一口大鍋,/煮刀光劍影、煮抒情緩慢,/一樣的麻辣燙。(《少城路》末節)
“蓋碗茶”、“龍門陣”、“麻辣燙”……密集的方言口語入詩不覺得突兀,且還顯露予抒情以美妙的墊襯,這是梁平的“手段”。詩歌作為主情的產物,受制于人的情感,尤其是瞬間的即時性的情緒推動,因而才有“真味”存留,否則刨除這一層,過于理性,那就是科學或理學,而關于科學和現代詩歌的關系,美國詩人哈特·克蘭在1930年就說過,科學的真理與詩人的真理是完全不可兼容的兩碼事,他以但丁和布萊克引證——科學追求的“真理”與詩人形而上學的、超邏輯的“真理”有著根本的不同。在《成都詞典》中,詩人梁平遵循“史”的客觀,挖掘“詩”的真味,入理又悖理,機妙地達成矛盾的統一。其實在人們的感知中,感性的詩歌與理性的科學確實不是一條道上的“客”,達爾文的進化論強調毀滅與再生的正確,而詩歌的新陳代謝,則是兼收并蓄的衍生物,這是人文精神包打天下的核心,說得好聽點是大器。那么作為一個當代詩人,如何打造這個虛無但實在的“器”去承載需要的似乎又是無用的東西,就顯得很難,如果器大力小,關鍵時刻定會掉鏈子,如果器小難堪,又必然不能讓自我滿足,也就更難滿足于他人。梁平知道,巴適與穩當,是詩人時刻保持警醒的一種智慧。從這個意義上推論,梁平的詩寫,因找到了個人情感與社會意識的最佳結合點,故格局大,不小家子氣。綜合這組詩歌來看,其作為詩人的自足是滿滿當當的。歷史風物的輪回與蝶變,市井故人的感懷與惦念,情感深處的惆悵與敞亮,人生奔忙的局促與逡巡,內心的焦灼與守望,批判的強力與哀婉……總之,凡是情緒所能到達之處,就是他詩歌所指的道場,可以說,他的寫作寬度與他的生活半徑是吻合的,這種“忠于”本地之旅的不離不棄正是詩歌真誠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對于歷史與當下的態度,尤其是歷史真相背后的詩性可能,梁平激發出來的靈感與情愫,讓我想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的詩性闡釋:“什么是神圣?/一副面具,/用以稱頌被玷污的事物。”讀《成都詞典》,能明顯地感知到,梁平對在成都這個城邑的尊崇有著至上的情懷,但是,他不走那種低級別的正面粉飾,而選擇發現和批判,或者說,因為發現才批判,這點,他做得有板有眼!本著一顆“痛心”對待歷史,對待現實,才是可靠的,可塑的,可以“興觀群怨”的。他也說過“詩歌是一種永遠的痛”。
那時候保路的英雄們,/還在集結民怨與外強的勒索掙扎。/那時候朝廷割地賠款,嗆一口黑血,/屈辱開始有了疼痛。那時候,/這里的刀槍指錯了地方。(《藩庫》第三節)
這個片段,十分類似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在《歷史》一詩中的感悟:“歷史必須與曾經在這里的東西住在一起/握住并靠近撫摸我們擁有的一切——/我們死去,這多么枯燥而可怕,/不像寫作,生命永無休止。” (胡桑譯)梁平似乎是在以野史的真誠敘寫正史的文脈,“屈辱開始有了疼痛”,對割地賠款的史實,讀者的記憶幾乎停留在教科書的僵化教條里,而鮮活現場的復原,無疑如“一口黑血”那樣“嗆”人——這簡約的筆力背后,交織著詩人的痛心與歷史的痛楚,雙重情感的映照,挖出了歷史真相,且更加入心。同樣在《交子街》里,詩人也以駁雜而沉痛的心寫出了“從數字到數字以外的民族記憶”。
沒有人與我對話,那些場景,/在街的盡頭拼出三個鮮紅的繁體字/——落魂橋。落虹與落魂,/幾百年過去,一抹云煙,/有多少魂魄可以升起彩虹?/舊時的刑場與現在的那道窄門,/已經沒有關系。進去的人,/都閉上了眼,只是他們,
未必都可以安詳。(《落虹橋》末節)
對于舊朝的刑場,詩人賦予“落虹橋”的內涵遠遠超出了語義本身,而如此緊致詩人情感的詩,《成都詞典》里幾乎每一首都不乏其訴,幾乎都是寥寥幾筆,就奔瀉而下。這樣的詩,面貌拙樸,激情隱在,卻很管用。通常而言,時代語境是詩人氣場的云團。梁平的詩歌已經形成這樣的基本特征:不趕潮流,走筆敦厚,循序漸進。他的詩思注重“推理”,推因索果,升階有序,始終處在一個講究感性與理性互為平衡的狀態,往往集中筆力于一點,傾情寫盡寫透,處處閃爍語言智慧的花火。
當然,與耽于地域唱響的前著《三星堆之門》與《重慶書》那種濃烈而磅礴的史詩氣勢相比,新作觸動下的詩人心緒平和了許多,他深知為城市修典,得以“智”取勝。前蘇聯電影藝術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說:“我心中真正的哲學家都是詩人,反過來也一樣。任何影像不管多么震撼人心,都應蘊含著獨有和重要的思辨內涵,因為對我來說這兩者密不可分。”處在創作一線的詩人都清楚,以注重現代性的詩歌去建構大一統的命題,是一項頗費思量的工程,于是,詩人選擇沉潛之心,于回望歷史真相的細節中,開掘文化的日常性經驗與審美再造,并環環相扣,加持思考的重力。
誠如《道德經·道經第十四章》所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掌握傳統藝術規律,用以實踐思考的問題,通曉古今,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創新。梁平對成都這座城市進行了一場歷史的考古,他用心于史實,用力于深思,在成都的人文疤痕中撒鹽,甚至于不惜擠出淤積的濃湯腐肉,捕捉變遷的蛛絲馬跡,導向心靈深處的期盼,為熱愛的城市濯洗前世今身,延續文脈,激活傳統,夯實底蘊,擎舉精神,不辱使命地完備自己對于成都這座城的寫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