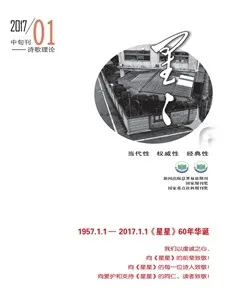身體隱喻,以及詩學的縮地法
畢竟是兩代人,老夫與李清荷不熟。隔著一個遙遠的“代”,2014年里,偶爾回眸,我像是看見清荷在河對岸點草成林,撒豆成兵,她是十萬朵桃花的王——女王,她用了100首詩來點染桃花的淺粉、血與脂膩。這似乎是一種來自于天命的針刺放血療法,她用一些近于極端的詩學修辭,把桃花演繹成了一種絢麗、打開、彌散的女性文化,有些寫法已經進入身體政治域界。我在《極端植物筆記》里描述過桃的桃樹、桃葉、桃花、桃實的四位一體的悖論,這讓我想到一個古代隱喻,說一個煉劍師為了鍛造出一把千古名刃,不惜把生命鍛打進去,精神成為劍芒,成為鞘中長嘯龍吟的精氣神。清荷互訓桃花,喻象如何回到喻體?就像博爾赫斯所言“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這分明是一個回環接龍魔術,但是,草本如何成為木本?但,她似乎做到了。
《布景者》當中抽空了桃花,清荷顯然移走了她的道具,匆忙間僅僅有些花瓣散落在字里行間,既像出于無心,又像是某種刻意安排。這樣,無香味的花瓣構成了清荷階段性的詩歌生命蹤跡,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色如故。色即是空,但空,未必就是色。在著意與放棄的過程中,桃花之王與詩歌女子移形換位,就像一朵迎風怒放的桃花,它吐出的夢境因為風的緣故,又為自己加冕了一層逆光的絲絳。我隱約感覺到,不從這個入口進入《布景者》,就找不到北,甚至容易成為“桃花瘴”的中蠱者。
《布景者》分為四輯,由于她沒有標注寫作時間,我的推測是:詩集是“倒編”而成的——從現在開始,逆時推向過去。在一個喧囂的時代,在一個人人深患名聲焦慮癥的時代,清荷安靜地盛開,用最可靠的生命直覺與奇思妙想,為我們繪就了一幅充滿女性感官與視域的心靈圖像。生命直覺的書寫技術調控有度,可以使女性文本在藝術性與個人性之間趨于和諧,也能使高蹈的女性主義趨于落地,詩人的生命與生活由此獲得了雅致以及款步蓮韻。在我看來,《布景者》也可以視作詩人的蹤跡史,既有現實在場意義上的,更有生命詩學意義上的,逐漸形成了她的直覺體悟式的創作傾向,這在《布景者》中表現為一種竭力叩問“境生象外”的韻外之致,講究情景與思的互嵌,大開大合的言語突變等幾個方面,由此形成李清荷詩歌口語與隱喻對撞生成的鷹翅風神與水體情韻。總體而言,我最喜歡第一和第二輯,第四輯《寫給項羽的后十二封情書》異峰突起,完成了她頂風書寫的高音部敘事。
從詩歌到詩學,人們隨處可見凝聚著詩藝的直覺和思想的升躍的辨析,以及寫作者的心靈與過往靈魂的碰撞。詩歌的語言文體,絕對不再是一個構成“問題的問題”。記得詩人袁勇說過,“非非”寫作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在變構和超越語言自身的同時,完成語言的使命,上天入地,找回語言的靈魂,提升語言的精神。一個詩人要在語言中閃光,到死為止!李清荷未必會相信、適應這樣的語言觀,她不過是在自己身體與現實革命的域場里,用泥土與語言,重新塑造了一個自己的詩歌仿生體,讓另外的自己與歷史往事、與一去不回的時光、與恩愛情仇,逐一進行一次一次的詩歌改寫與美學修復。身體是詩歌的導師,身體也成為經驗的受益者。
《布景者》之名,來自于詩集里的一首同名小詩:
麥地的勞作是自然清新的
我允許人們高聲贊美
災難的制造者是不可饒恕的
(他們將太多的矛盾推向事物發展的相反方向)
我允許他們把加于自己的無限榮譽摘取下來
走來走去的風景是傍晚數時間的人
那些是寶貴的
我允許時間為他們停下來
詩中出現了峭拔的《圣經》語式,那個高高在上的“絕對存在”,似乎降臨在我們的女詩人舌尖。這讓我想起耳熟能詳的場景:狼奔豸突的利欲街頭。一臉油汗的偽善者。急于出名的牙科醫生。高舉標槍的苦悶者。股票交易所門前沮喪的、悲痛欲絕的胖編輯……這些場景雖然不至于是“無知的風景”,但他們已經成為時代與生活的“布景者”。景觀的邊緣,“走來走去的風景是傍晚數時間的人”默然,一個欲望的舞臺布景完備,那些“寶貴的”展示時間蹤跡的人,似乎要伴隨時間的背影而去。那個“絕對存在”以女聲發話了:“我允許時間為他們停下來”。其實,人們極可能坎坷一生,最終發現自己終點,恰恰是發現浮士德博士臨終的起點:“停一停吧,你真美麗!”我再說一遍,就像博爾赫斯所言“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唯一不同的是,這樣的輪回,必須由一個人去實踐——我來了,我看見,我說出。
在我看來,一個成熟的詩人一生就是依靠幾個不死的隱喻,來集聚、來呼喚他們散落在這些隱喻四周的言辭斷片,這些階段性的隱喻就像他們的脊椎,最終擦亮了那詩意的額頭。隱喻既是詩人的面具,也是他們的臉。既是自己的異形,最終異形也成為了自己的主腦,自己反而消匿在隱喻的濃蔭以及氛圍之中。中國當代最為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詩人萌萌說得非常剴切:“字、詞,從它們一誕生起就攜帶著隱喻。即在字、詞的具體性和單一性的后面隱藏著它們與生俱來的、甚至是促成了它們誕生的象征性和隱喻性。詩,或許就是對原始語言的追問、追逐。”
如果說“桃花”儼然已經是清荷詩歌的一個隱喻的話,“布景者”卻是另外一層意義上的。從根本上講,隱喻已經是一種認知現象,是人們理解世界、進入事物的唯一秘密口令。隱喻既是人類固有的思維方式,也是共時性和歷時性、中斷性與連續性、單向性和重復性的雙重結構以及多重遞進模式。隱喻是在三個層面獲得生衍的——作為修辭的隱喻(修辭手法)、漢語固有的“隱—喻”范疇(比興、意境等古典詩學概念)和隱喻性(包括了詩學、語言學、修辭學、意識形態學等等),考察李清荷近年的寫作,她將更多的使用第一義和第二義,但有時會混同使用。在這個意義上,一些口語詩人“拒絕隱喻”的美學自況,如果可以立論的話,即便是在狹義修辭方面也顯得較為勉強,更何況他們不可能拒絕隱喻性,否則就沒有詩性寫作這碼事了。英國學者C.路易斯說,隱喻是詩歌的生命原則,是詩人的主要文本和榮耀。我贊同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在《活的隱喻》中的結論:隱喻不僅提供信息,而且傳達真理。隱喻在詩中不但動人情感,而且引人想象,甚至給人以出自本源的真實。他甚至指出,隱喻的詩歌性與詩歌的隱喻性乃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就是說,花開兩朵,還是一枝。
口語化寫作是一種大勢。但是,清荷的詩歌里過多的口語化傾向就不能引起必要的警惕。至少在我看來,我不太贊同口語不經純化的率性寫作,西爾維婭·普拉斯就練就了口語與身體、隱喻與情欲的平衡術。
前天晚上,我與青海詩人、作家辛茜談到清荷的文體時就認為,一個詩人應該有意識地對自己的語言體系至少進行兩次凈化:其一是必須對過往年月存留在我們意識里的大詞、根本無涉思向的套話進行祛魅;其二是必須對毫無棱角、毫無快感的庸詞進行祛魅。清荷詩歌里,她不經意間就冒出了諸如“泰山壓頂”“風和日麗”“指點江山”“鐵血丹心”等等套話,這些套話根植于意識深處的駢四儷六,它們是制式文化的友人,但分明是詩性的大敵,在我心目中就是捕食自由的天敵。喬治·奧威爾說:“用舊詞來制造新詞使它失去了任何真正的新鮮感,這樣做是不行的,但是僅僅隨意拼湊幾個字母來制造新詞也是不行的。你必須確定新詞的自然形態。就像商定新詞的實際意思一樣,這需許多人的合作。”清荷的語感、語式尚處于變化過程當中,我提出來,不一定正確,希望清荷引起反思。
我讀到《西街聊記》時,心頭涌起“微暗的火”,更有無以名之的況味——我寫作《人生如蚌,蚌病得珠——關于流沙河、何潔斷代史》長文時,去過城廂鎮,撫摸西街到槐樹街那些斑駁的青磚、風化的條石和松木門板。清荷利用詩歌的“甲馬”,展示了“詩學的縮地法”,她回到了50年前——
一條長長的街道巷子,像一條繩子似的
通向深處。我在街上,走過來
走過去。差點與數十年前的
流沙河擦肩而過。旁邊就是三清觀
他那時還是一個孩童,
或是一個留著帶時代印記的發型的
青年文學愛好者
……
那種強烈的在場感,想象中的幾個細節,凸顯了一種鐵鏈嘩動的動感,清荷的高跟朵朵朵地響在“故園”的場域,這不禁讓我想起卡洛斯·威廉斯筆下那個彎腰拔掉鞋跟釘子的描寫:
流沙河,一個在城廂鎮生活多年
在陰暗潮濕的槐樹街故居里
寫出《草木篇》的老詩人,是可敬的
如今,他院子里的鳳仙花開了
讓跟泥土一塊長大的我,覺得格外親切
矮矮的花圃里,一棵長得無比碩壯的
車前草,都讓我找到了當年流沙河
生活的滋味。只是我不知道,當年
作為幼童或者青年的流沙河,是否想到過
一個他鄉的女子,因為孤獨
因為無法讓夜變得更加妥帖,而以悲觀主義花朵的名義
駐足在他的門前?
結尾明顯弱力了,太白。我想,如果不是玫瑰之刺靠近了里爾克的手指,那也應該是“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偉業之于曼陀羅。清荷啊清荷,你有點冒險。
其實,謎底就是謎面,正如花,也可以不開。不論植物是否泄露這一秘密,你靠近的存在就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釘子,而且不容易拔掉。
至于在第四輯里的兩首長詩,清荷的詩歌“甲馬”繼續遠游,與項羽、與虞姬、與周瑜、與二喬、與浪子燕青等英雄美人稱兄道妹。既然不想“等待戈多”,那她就沒有從荒誕中離場。清荷一直在場。相對而言,清荷的個人天性是不憚于荒誕的。她一旦回到詩的字里行間,她就也承擔了“他人即地獄”的命運。為此,她毫無顧忌地攤開自己:
我們所熟悉的是彼此昨天的
心靈相通,而忽略偶爾的變更
我的懦弱被蠶食,碎裂增加
小喬,我宿命的妹妹
從嬰孩開始就與你一起入睡
汁液濃綠,馬蹄聲里我嫁給孫家子弟
不經意里安守婦道,也是在墓地
改變那些美好的愛情的品位
依靠余生里萌動的誘惑
打敗凌云之志,用沉落下去的一截理想護身
小喬,我們無形無體、秘而不宣
同性相憐,輕如鴻毛而蔓生枝節
應該說,詩行里有不少好段落,但總體上過于直白了,好的詩歌是獲得了感性與經驗之間的平衡,而更多地側身于經驗。詩歌和生活的關系,很像“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關系,徹骨的又是疏離的。詩能融入生活的肌理,可觸摸,有體溫,具有強烈地可感氣息,這就是詩的在場感。但清荷詩歌里更多的卻是俯身于悲情的在場感,由此產生了一種更為陌生的間離感。我就有點疑惑了:到底是要乘風歸去?疑惑是要與英雄美人手挽手回到現實?或者你就是要告訴人們——清荷乃是他們默化的情愛記錄者嗎?他們也是“布景者”嗎?長詩《人的世界不再安靜》的題記是:“清荷無情義,世界無情義。”也許,這是可以逆推、互訓的結論。既如此,夫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