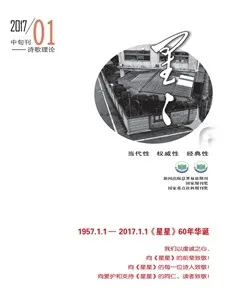對生存的深刻哲思
在眾聲喧嘩的詩壇,詩人散皮創制出了別樣的審美空間。散皮是一位懂得生命藝術的詩人。他的詩作,既有洞察人間世相的煙火氣息,又有超脫世俗的哲學思考。他不流于低俗的口語進行空洞的吶喊,也無形式實驗的造作。散皮的詩,是生命的詩。高蹈獨立,低調睿智,不刻意求新卻處處創新。他以敏銳的洞察力,警覺于“科技萬能論”帶來的生存困境,警覺于個體和現代文明共謀之后的異化形態。他從形而下的物質生活中,展現人的精神狀態及其異化行為。他所要表現的,并不止于敘述表層。而是深入現實的肌理,以極為常見的場景,對人的生存位置作形而上的思辨。
一、蒼白的生存景觀
面對工業文明下人的生存狀態,散皮有著深切的憂慮和質疑。這一點與美學浪漫主義者盧梭相契合。盧梭認為,歷史的進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長和負值效應——兩條對抗線交織而成的。在建設性的正值增長中,內含著破壞性的負值效應。而散皮所處的時代,正是科技理性帶來巨大狂歡的時代。人們沉湎于科技文明的正值增長,迷戀于無限膨脹的物欲。卻無視高度文明帶來的蒼白生存景觀。散皮具有詩人與生俱來的敏感和警覺。他以平實而干凈的筆質,將一幅幅繁華虛景定格,以此來顯示人們兩難的生存窘境。面對城市,散皮有著巨大的恐慌和焦慮,“篤篤的踱步排山倒海/道路逐漸合攏/街/其實空著”(《2015,街景》),身處繁華的都市,面對魚貫而出的人群,詩人的心是空的。“新聞都是城市的腰酸腿疼/削山采石/倒下了一具風景的破舊尸體”(《不是我一個人戰斗》),這是一個被謊言遮蔽的時代,新聞掩埋了城市殘忍的真實。“一盤驢肉端上了食譜/查了下百度/驢/無毒”(《慶功宴》),于生存的安全隱患中,人們極力從網絡中尋找安全感,并甘愿成為網絡的附庸。在詩人眼里,工業文明的代價是巨大的,他試圖構建另一個常態世界來影射當下現實,“那里有夢沒有魘/魘的形狀都被人供養/失去了夢行天下的清澈與涼爽”(《另一個世界》)。他感慨于城市噩夢對生命之種的扼殺,“他一定這么想著/這么留下來/躺在馬路上/等待風生水起”(《馬路上,一粒種子》)。“月亮找不到沉入湖底的空間/只好隱現在霧霾中”(《大明湖》),工業機械所帶來的霧霾恐慌,淹沒了人類詩意生存的棲居地。當旖旎的自然風光也只能成為記憶空間的一部分,“與虎聯在一起/只因為虎嘯的泉水/早已成為稀有動物”(《黑虎泉》)。面對這樣的生存環境,我們,究竟可以生存在何處?這是散皮留給我們的疑問。
二、畸形化的精神形態
在缺乏詩意的生存窘境中,人們畸形化的精神狀態是散皮最為擔憂的。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文明的道德乃是被壓抑本能的道德。赫伯特·馬爾庫塞曾經說過:“必要勞動成為一系列本質上非人的、機械的、例行的活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處于工業文明的機械化勞動中,人的本能被深度壓抑。在不同程度上,這種壓抑可能產生兩個結果。要么導致人對欲望的畸形渴望,要么導致人失去生存的詩情,變得呆滯機械。詩人散皮,以悲憫的情懷,捕捉人之精神被工具理性劫持的過程。他力圖從日常生活的底色中,挖掘戰栗的靈魂。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化描寫,散皮將生活的邊緣場景和時代元素進行糅合。從而發現脆弱的精神形態:孤獨、恐慌、疲憊、機械、麻木、自我分裂、多疑、敏感……在城市的爾虞我詐中,人們極度缺乏安全感,即使是在睡夢中也忐忑難安,“躡手躡腳進入淺睡區/并在那里不動聲色觀察睡姿/直到完全看不出秘密”(《清醒》)。“里面的人似乎刻意在復制我的生活/卻把我的生活布置成謀殺現場”(《鏡子里的影像謀殺了我》),這是人們于緊張的生活壓力下,孳生的意識分裂,人們所追逐的欲望深淵正是生命的墳墓。“我的凝視使我迷失在另一度時空/對我的凝視/令人毛骨悚立”(《恐懼》),這是人們窺探自我隱秘心理的恐懼。“我發現我還是像極了某某/好像越來越想念某某/某某/反正不像自己”(《他人》),被網絡所奴役的我們,正不知不覺失去了個性的獨立,而成為他人“某某”。“我的疆域比心遼闊/我的睡眠比夜晚更多/但我渴望進入狼群”(《獨狼》),在抒情主體“狼”的孤獨中,尋而不得的歸屬感也正是人類的心聲。面對人們因欲望而多疑敏感的神經,詩人冷眼旁觀,“‘像我一樣的人時刻盯著我的言語’/隱藏不夠深/泄露些許春光/一定是有人告密”(《天性》)。人們為一群家雀的遷徙而驚恐不已,“行人驚慌于天象異常/疑惑的眼神相互問詢”(《驚恐,抑或抗議》)。“與生俱來的宿命緊緊卡住了時間的出發地/忘記了嘆息、焦慮和回眸”(《今年夏天不同》),我們奔波于現代化的陷阱,導致技術思維的單向,只知道前進卻忘記了思考。面對當下精神狀態的隘化,散皮以詩求證,精神應于何處安放?
三、生命意志的建構與精神家園的尋找
散皮對物質和精神雙重困境的揭示,并未停留于簡單的表層描述,而是極力尋找生存困境的出口。他以豐盈的生命意志建構反抗的主體,以哲理化思考尋找精神家園。首先,在他看來,只有具有強力意志的生命,才能突破機械文明的枷鎖,到達自由的狀態。在他筆下,萬事萬物都是靈性的存在。他將堅韌的生命意志賦予一草一石、一磚一瓦,并以它們為抒情主體來反抗“異化”。“再小的顫動/總得有一種方式活著/再高的飛升/也是現在”(《暴雨夜,另一滴雨》),這是一個能思考的“雨滴”,它呈現著孤傲的生命尊嚴。詩人對生存現狀的逃離,以“石頭”倔強的姿態來完成,“它們試圖跳出當下生存狀態/走自己的路”(《逃離》)。“水/雕刻著我/我/描繪了水/內心只剩堅韌”(《與水為敵》),這是“鐘乳石”對內心堅韌的獨守,也正是詩人對一片絕美風景的獨守。“柏樹”緊密相連的家族根系,正是作者對豐盈意志的呼喚,“只有強勁的野草四處繁衍著/陌生人看不出地下緊握的家族根系”(《鄰近的痛》)。其次,作者希望從古典的人文氣質和西方先哲那里尋求精神的出口。然而散皮的尋求姿態,虔誠而不恭維。在詩人恣肆的想象里,與康德把酒言歡,討論生存哲思,“有多少虛妄被當做真實/哲學/讓上帝蒙羞”(《暗夜之思》)。對夏娃與蘋果的故事起因,進行新的解讀,“一支小蘋果竟然成就了人類,從一維爬向四維的神話”(《蘋果》)。詩人以生命時間的逆行來消解崇高,“我們設計多種想象把事件還原/讓掉到牛頓頭上的蘋果/返回到樹枝”(《萬有引力》)。散皮寫了許多關于時間的組詩,希望從時間與存在中追溯生命的啟示,如《時間的過往》、《時間之門》等。最后,詩人為顫抖的靈魂描繪了理想的精神家園,即未被現代文明染指的故鄉。那是長在詩人記憶中的、干凈的、神圣的存在。在《我是一個有故鄉的人》、《因為窮,才有意義》、《故鄉》中,詩人多次以熱烈的筆觸提及。
四、多元自由的藝術表達
詩人對人類生存狀態的呈現和精神出路的尋找,以多元而自由的藝術方法呈現。首先,散皮的詩歌語言是自由的,消解了詩歌本身的框架,具有敘事化傾向。例如《一次午宴的再認識》一詩,以具有較強故事性的情節展開。散皮的語言是具有極強包容性的,寫景詩有著古典詩歌語言的端莊,“初見面”、“長相憶”、“其聲音約約/其笑貌也約約”(《途徑蕪湖,未晤詹聲信》);敘事詩則融入時代元素,“朋友圈”、“WiFi”、“碰瓷”、“自媒體”、“春晚”、“《爸爸去哪兒》”……兩種語言的底色一正一反,亦莊亦諧,耐人品察。其次,在散皮筆下,詩體也是自由的,時而散漫,時而嚴謹。《慶功宴》以百度說明書的體式展開,極為幽默;樓梯體式的詩歌更是巧妙新奇,不僅是在字數、節奏上錯落有致,而且在詩歌題目、詩歌意象上前后對應,如《一個早晨的人生,不是人生的一個早晨》。另外,詩人擅于通過多樣化的敘述視角,陌生化的比喻來塑造審美空間,如《狗眼人間》、《最后的忠誠》中,以動物的視角,來描述人類的生存狀態。更為有趣的是,散皮以消解崇高的姿態,進行文本的戲仿。“春暖花開時想著姐姐/面朝大海/關心著狗糧/柴草和旅行”(《致X死黨》),這是對海子詩歌的戲仿。在《2015,街景》組詩中,從“父親的獨輪車”到“山海經”、“金字塔”,這是對精英文化的解構。
散皮的詩歌以獨特多樣的手法,呈現他對生命的深刻感悟。活在當下,工業機械統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動是遲緩的,精神是變形的,我們到底該生存在何處?然而只有豐盈的生命意志才能到達散皮的精神家園。正如作家王小波所說的:“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