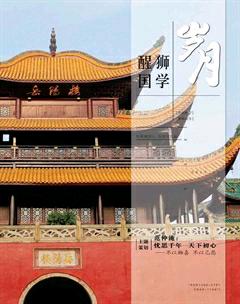范仲淹興學(xué)育人
唐寶民
提起范仲淹,人們總是會(huì)想到“政治家”“軍事家”“文學(xué)家”這三個(gè)頭銜兒,其實(shí),范公還是一個(gè)偉大的教育實(shí)踐家。范仲淹的官場生涯中,在多個(gè)地方擔(dān)任過地方官,每到一處,他都大力興學(xué)辦教育,在興學(xué)育人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
范仲淹的興學(xué)實(shí)踐,是從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開始的,這一年,他的母親謝氏病故,他傷心欲絕,按照當(dāng)時(shí)的規(guī)定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丁憂。當(dāng)時(shí)的南京留守,是著名文學(xué)家晏殊,晏殊一直以來就很賞識(shí)范仲淹的文才,知道范仲淹已回南京居住,就想邀請(qǐng)他出來幫忙辦教育,范仲淹欣然領(lǐng)命,便開始協(xié)助主持應(yīng)天府的教務(wù);他還向晏殊推薦了青年人富弼,以此來加強(qiáng)應(yīng)天府的辦學(xué)力量。范仲淹是一個(gè)極其認(rèn)真的人,在辦學(xué)過程中,一點(diǎn)都不敷衍,為了能隨時(shí)隨地掌握府學(xué)的情況,他親自搬到了學(xué)校里面居住。為了使學(xué)生們能養(yǎng)成有規(guī)律的學(xué)習(xí)生活,他制定了一套詳細(xì)的作息時(shí)間表,要求學(xué)生們嚴(yán)格遵守、按照時(shí)間表的規(guī)定去做。即使是到了晚上,他也還是不放心,而是主動(dòng)當(dāng)起了舍務(wù)監(jiān)督的角色,經(jīng)常深入到宿舍里檢查、責(zé)罰那些偷閑嗜睡的學(xué)生。那時(shí)的考試,經(jīng)常要求學(xué)生們根據(jù)命題寫文章,每當(dāng)此時(shí),范仲淹總是自己先根據(jù)命題寫一篇文章,以此來掌握試題的難度。在范仲淹的努力下,應(yīng)天府院的學(xué)風(fēng)很快煥然一新,并聲名遠(yuǎn)播,吸引了八方志士紛紛前來求學(xué)。
對(duì)于前來求學(xué)的人,范仲淹熱情地接待、并親自為他們講授;難能可貴的是,他還用自己微薄的俸祿招待他們吃飯、甚至接濟(jì)他們,有一回,有一個(gè)孫秀才前來拜謁范仲淹,孫秀才生活貧困,但頗有志向,流浪各地乞討求學(xué)。范仲淹熱情地接待了他,當(dāng)即贈(zèng)送給他一千文錢。一年之后,這位孫秀才又來拜謁范仲淹,范仲淹再次送錢給他,并問他:“你為什么四處奔走,不坐下來靜心讀書呢?”孫秀才回答說:“家有老母,難以贍養(yǎng);如每天能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就足夠使用了。”范仲淹聽罷,對(duì)他說:“我?guī)湍阍趯W(xué)校里找個(gè)差事,讓你每月有三千文收入去供養(yǎng)老人,如果這樣,你能安心治學(xué)嗎?”孫秀才立即驚喜地拜謝范仲淹,從此安下心來跟隨范仲淹學(xué)習(xí)。十年以后,有一位叫孫復(fù)的學(xué)者在泰山廣聚生徒、講授《春秋》,一時(shí)間名聲大振。這個(gè)孫復(fù),就是范仲淹十年前接濟(jì)過的那個(gè)孫秀才。范仲淹聞知此事后,感慨地說:“貧困的確是一種災(zāi)難。如果孫復(fù)一直乞討到老,這樣杰出的人才豈不是被埋沒了嗎!”孫復(fù)只是范仲淹接濟(jì)過的人才中的一個(gè)代表,類似孫復(fù)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他們都在受過范仲淹的雨露恩惠之后成長為了一方人才。
范仲淹在地方上任職,每到一處,他都大力辦學(xué),在他任過職的許多地方,都有他親手所辦的學(xué)校: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奉命移知蘇州,在南園購地創(chuàng)立了蘇州府學(xué);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知饒州,欲“興學(xué)校,明教化”,雖然未等府學(xué)建成就被朝廷召回,但他的想法卻在慶歷六年由知州張君實(shí)現(xiàn)了;寶元元年(1038年),范仲淹又知潤州,又“載新廟學(xué),置田養(yǎng)士”擴(kuò)建了州學(xué)……為了辦好學(xué)校,他還不惜花大價(jià)錢請(qǐng)優(yōu)秀的學(xué)者去講學(xué),從而加強(qiáng)了學(xué)校的師資力量:蘇州府學(xué)建成后,范仲淹聘請(qǐng)胡瑗來蘇州講學(xué);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為陜西經(jīng)略副使兼知州,他在城東南修建了嘉岑書院,并培養(yǎng)了張載、狄青等優(yōu)秀的人才;潤州府學(xué)建成后,范仲淹寫信邀請(qǐng)著名學(xué)者李覲來潤州執(zhí)教;第二年,范仲淹調(diào)任越州,再次寫信邀李覲赴越州“講貫”……慶歷四年,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相當(dāng)于副宰相),在這個(gè)職位上,他日理萬機(jī),但仍沒有忘記大力提倡教育,提出了設(shè)立學(xué)校培養(yǎng)人才的主張,主張?jiān)谥菘h廣泛設(shè)立學(xué)校,以便做好基礎(chǔ)教育;同時(shí)主張改建太學(xué),加強(qiáng)高等教育。在科舉考試方面,他也提出了新見解,主張變更考試的科目與內(nèi)容:“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聘矣;問大義則執(zhí)經(jīng)者不專于記誦矣。” 在著名的新政綱領(lǐng)《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了十項(xiàng)改革主張,其中第三項(xiàng)就是關(guān)于科舉改革的:“精貢舉,即嚴(yán)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yǎng)有真才實(shí)學(xué)的人,首先應(yīng)該改革科舉考試內(nèi)容,把原來進(jìn)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jīng)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jīng)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jīng)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xué)生有真才實(shí)學(xué),進(jìn)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shí)了。”范仲淹的主張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慶歷四年(1044年),仁宗皇帝詔令天下州縣設(shè)立學(xué)校,并改革科舉考試辦法。隨后,各個(gè)州縣都辦起了學(xué)校。范仲淹罷相、慶歷新政夭折,但各地州縣的學(xué)校卻如雨后春筍般的發(fā)展起來了。
范仲淹的興學(xué)行動(dòng),起源于他的教育思想,天圣八年五月,他在《上時(shí)相議制舉書》中寫道:“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xué);勸學(xué)之要,莫先宗經(jīng)。宗經(jīng)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提出“勸天下之學(xué),育天下之才”的主張,認(rèn)為這樣才能達(dá)到“國家勸學(xué)育才,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fēng)教” 的目的。范仲淹之所以重視教育,是因?yàn)樗J(rèn)識(shí)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認(rèn)為“賢者的價(jià)值一百個(gè)城也比不上”“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他主張大力興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民眾的文化品質(zhì)、為國家培養(yǎng)經(jīng)世致用的人才,令人欣慰的是,他所播撒的文化種子,結(jié)出了累累的果實(shí),其中不乏一些出類拔萃的杰出典范,除了前文提到的孫復(fù)外,還有張載、狄青諸人——張載是在延州嘉岑書院受教于范仲淹的,范公見張載少有大志,十分器重他,培養(yǎng)他認(rèn)真學(xué)習(xí)儒家經(jīng)典,張載果然不負(fù)所望,后來成了一名大哲學(xué)家;狄青也在延州嘉岑書院跟隨范仲淹學(xué)習(xí)的,范仲淹不遺余力地培養(yǎng)他、教他讀《春秋》、讀《漢書》,范仲淹說:“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在范仲淹的教育下,狄青成了一代名將,在抵御西夏的戰(zhàn)爭中屢立戰(zhàn)功。
羅家倫曾這樣評(píng)價(jià)教育家梅貽琦:“種子一粒,年輪千紀(jì),敬教勸學(xué),道在斯矣!”這句評(píng)價(jià),同樣可以用在范仲淹身上。范仲淹的興學(xué)育人思想及辦學(xué)實(shí)踐,為北宋時(shí)期的文化教育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在神州大地上播撒了教育的種子、發(fā)展了地方的文化建設(shè),從而提高了百姓的文化水平、使民眾的整體教育素質(zhì)得到了提高。為官一任,興教一方,雖然他在許多地方任職時(shí)間都不長,但他身后的累累碩果,卻向人們展現(xiàn)了他以天下為己任、以蒼生為己念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