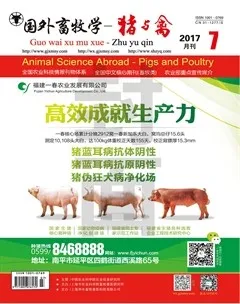斷奶仔豬腸道健康及功能:使用營養策略而非抗菌化合物控制斷奶后仔豬腹瀉(綜述)
摘 要:近幾十年來,通過預防亞臨床和臨床疾病,抗生素常被用于斷奶仔豬來促進它們的生長性能。然而,有關耐藥性菌株的出現和這些菌株及相關抗病基因對人類健康影響的關注日益增長。因此,歐盟(European Union,EU)于2006年1月1日開始禁止將抗生素作為生長促進劑用于生豬和畜牧生產中。另外,礦物元素,如鋅(Zinc,Zn)和銅(Copper,Cu)不可能用作抗生素的替代品,因為其排泄物可能會對環境造成威脅。因此,有必要開發飼喂方案,以使在不使用抗生素的前提下來控制與仔豬斷奶過渡期相關的疾病。因此,本綜述將重點介紹一些已知主要利用益生菌、益生元、有機酸、微量元素及日糧蛋白質來源和含量能夠改善腸道結構及功能和(或)提高仔豬斷奶后生產性能的營養戰略。
關鍵詞:抗生素生長促進劑;豬;日糧蛋白質水平;有機酸;益生元斷奶后腹瀉
中圖分類號:S815 文獻標志碼:C 文章編號:1001-0769(2017)07-0101-04
斷奶會給仔豬帶來極大的應激,導致胃腸道生理、微生物菌群和免疫力的顯著變化(Hampson,1986;Pluske等,1997;Brooks等,2001)。由于這些變化,仔豬在斷奶后表現出的特點是腸道紊亂高發、腹瀉和生長性能下降。在豬上,與斷奶相關的較差的生長性能是由多方面的應激引起的,包括環境應激、營養應激和心理應激(Williams,2003;Lalles等,2004)。斷奶時,仔豬需要應對與母豬和同窩仔豬已建立社會關系的突然中斷以及適應新環境產生的應激(Lalles等,2007)。另外,仔豬還要應對母乳的突然中斷,適應不易消化的以植物為主要成分的日糧,這些日糧含有復雜的蛋白質和包含多種抗營養因子的碳水化合物(Wilson和Leibholz,1981;Cranwell,1995;Lalles等,2007)。因此,仔豬在剛剛斷奶時采食量會驟然下降(Pluske等,1997)。雖然大約50%的斷奶仔豬會在斷奶后24 h內開始進食,但仍然有10%的斷奶仔豬厭食時間會長達48 h (Brooks等,2001)。抗生素和礦物質(特別是ZnO和CuSO4)常被用于斷奶仔豬日糧,用來控制仔豬斷奶后腹瀉(Post-Weaning Diarrhoea,PWD)發生,優化它們的生長性能(Verstegen和Williams,2002)。斷奶后腹瀉通常與胃腸道(Gastrointestinal Tract,GIT)中一種或多種腸毒性大腸桿菌(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ETEC)菌株的增殖相關(Fairbrother等,2005;Nagy和Fekete,2005)。由于飼用抗生素可能會誘發耐藥性細菌菌株的產生(Amezcua等,2002),歐盟(European Union,EU)在2006年1月開始實施了全面禁止在畜禽日糧中使用飼用抗生素。世界各地的其他國家同樣開始盡量減少或全面禁止飼用抗生素在畜禽日糧中的應用(Lusk等,2006)。因此,國際市場很可能會加大對不使用飼用抗生素所生產出豬肉的需求。根據EU的經驗,飼用抗生素使用的禁止通常會伴隨出現嚴重的生產后果,例如斷奶日齡的提高和每頭母豬每年生產的斷奶仔豬數量的減少(Hayes等,2002;Stein,2002)。另外還有對因日糧中高水平的無機鋅和銅引起的礦物質在環境中累積的關心程度也會提高。為確保生豬生產的利潤,勢在必行的是尋找能夠有效減少與剛斷奶期間相關的消化問題的發病率和嚴重性的飼用抗生素替代品。
因此,本文將重點介紹與某些已經能夠改善斷奶仔豬胃腸道結構和功能的營養策略相關的知識和可能的抗生素生長促進劑替代品(如益生菌、益生元、有機酸、微量元素和日糧蛋白質源及水平)進行綜述。
1 斷奶前后仔豬胃腸道的生理及代謝的變化
1.1 胃
胃的功能包括混合食物、部分消化食物、并且是對抗外部環境的屏障(Barrow等,1977;Zhang和Xu,2003)。為實現消化功能,胃內布滿了酸(鹽酸,Hydrochloric Acid,HCL)分泌細胞,可以保證胃腔內有很低的pH(Yen,2000),因為較低的pH是胃中的酶原轉化為有活性的消化酶所必要的條件(Khan等,1999)。另外,日糧蛋白質胃內消化的適宜pH為3.0(Prohászka和Baron,1980)。文獻報道,斷奶對胃中活性酶的影響尚不清楚。例如,Hedemann等(2004)發現,斷奶會降低胃黏膜中胃蛋白酶的活性,但不會影響脂肪酶的活性;然而,其他研究發現,斷奶后胃黏膜中胃蛋白酶和脂肪酶活性增強(Cranwell,1985;Jensen等,1997)。
較低的pH環境(即3.0~4.0)能夠殺滅許多致病微生物,包括大腸桿菌(E. coli) (Prohászka和Baron,1980;Modler等,1990;Yen,2000)。因此,除了對營養物質消化的影響,胃腔內維持較低的pH環境對腸道健康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可以減少進入小腸的致病菌的數量。
與母乳喂養的仔豬相比,斷奶仔豬胃中pH較高,其可能部分是由于斷奶后胃分泌酸的能力下降,同時由乳糖生成的乳酸也有所減少(Manners,1976;Efird等,1982)。斷奶后胃內較高的pH可能是仔豬在該時段對腸道感染敏感的部分原因。
斷奶還會降低胃動力,例如,Snoeck等(2004)發現,與未斷奶的仔豬相比,仔豬在斷奶后的第3天和第4天胃排空率會下降。鑒于仔豬斷奶后胃中pH通常較高,胃潴留導致致病菌增殖,進而引發仔豬發生PWD。的確,文獻記錄表明,在早斷奶的仔豬中,胃潴留是造成仔豬PWD的其中一個因素(White等,1969;Barrow等,1977)。另外,有研究報道,應激基因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受體2的激活與胃動力的抑制有關(Martinez等,2004),它在斷奶仔豬空腸中的表達被上調(Moeser等,2007)。雖然斷奶仔豬胃部是否存在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受體2還有待證實,但是,Moeser等(2007)發現,胃排空速率可能受腸道反饋的調控(Boudry等,2004a;Lalles等,2007)。其他影響胃排空速率的因素包括采食量和日糧組成(Rydning等,1985;Shi等,1997;Lalles等,2007)。例如,仔豬在斷奶后5周中日糧從以母乳為主日糧快速更換為以小麥為主的日糧,會導致胃排空速率的短暫性提高(Boudry等,2004a)。
1.2 小腸
剛斷奶期間小腸結構和功能會發生顯著的改變(Hopwood和Hampson,2003),這些變化會暫時性地導致斷奶仔豬的生長中止和腸道功能紊亂。小腸在仔豬的生長中有著很多的生理學功能(Cranwell,1995),但是本文主要討論其與營養物質消化、流體和電解質的分泌和吸收的功能。
1.2.1 小腸的形態
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斷奶會對豬腸道結構產生極大的影響(Hampson,1986)。小腸上皮層指狀的突出部分是絨毛,它可以增加消化道消化和吸收的表面積(Zhang和Xu,2003)。另外,存在于小腸絨毛基部的管狀腺體向著腸道內腔開口,其被稱為隱窩。隱窩含有上皮細胞再生所需的上皮干細胞(Zhang和Xu,2003;Llyod和Gabe,2008)。要使小腸擁有最佳的功能,腸絨毛需要長。然而,斷奶后,絨毛會出現短暫性的萎縮,同時隱窩增生。斷奶后的厭食被認為是造成這些改變的主要病因,因為斷奶后能量的攝入量與小腸構造呈正相關(Pluske等,1997)。同樣,McCracken等(1999)報道,斷奶后的厭食與隱窩肥大和局部炎癥反應有關:與飼喂乳代品的仔豬相比,在飼喂豆粕型日糧的仔豬中,采食量的減少而非日糧組成會影響空腸的上皮結構。
除了斷奶后采食量的降低,其他因素也會導致絨毛萎縮。例如,Kelly等(1991b)報道,在斷奶后前3 d,仔豬通過胃插管持續進行飼喂,其腸道絨毛高度(Villus Height,VH)會降低,而隱窩深度(Crypt Depth,CD)會加大。該作者認為,仔豬在斷奶后其腸道形態將發生改變,即使持續供應營養此類情況也將如此。雖然作者并未指出造成這些改變的具體機理,但這很可能與斷奶應激有關。例如,斷奶后2 d~ 3 d,仔豬血清中應激相關激素——胰高血糖素的濃度提高(van Beers-Schreurs等,1998)。由于胰高血糖素是一種分解代謝類激素,它有助于動員體內儲備的能量,并將其轉化為葡萄糖,因此van Beers-Schreurs等(1998)推斷,斷奶后仔豬與母豬分開并轉移至其他豬欄造成的應激,是導致斷奶后仔豬腸道結構發生改變的部分原因。最近發表的有關斷奶后仔豬腸道結構改變多篇論文,它們的總結列于表1。比較不同試驗中的腸道形態數據比較困難,因為試驗豬在日齡、品種、日糧組成和試驗環境上均不相同,并且還因為目前尚無VH和CD的檢測標準。
總之,可以確定的是,維持能量攝入量、減少斷奶應激是維持斷奶后仔豬小腸結構完整性的重要因素(Pluske等,1996b;van Beers-Schreurs等,1998;Moeser等,2007)。
1.2.2 消化功能
腸細胞的刷狀緣表面履行小腸的消化功能。腸細胞分別占隱窩和絨毛上皮細胞的90%和95%,這些腸細胞負責分泌消化酶(Cheng和Leblond,1974)。這些酶的作用部位主要是黏膜,可以很容易與胰酶區分,后者主要作用于腸腔內容物(Adeola和King,2006)。斷奶仔豬刷狀緣酶的活性已經被用作小腸消化功能成熟的指標(Henning,1985;Hampson和Kidder,1986)。
仔豬斷奶后,腸道中乳糖酶的活性通常會降低,這部分與刷狀緣乳糖酶活性下降有關(Montgomery等,1981;Kelly等,1991a;Motohashi等,1997)。然而,有關斷奶對其他刷狀緣二糖酶影響的文獻結果缺乏一致性。例如,部分研究發現,斷奶會造成斷奶后第1周仔豬腸道中蔗糖酶、異麥芽糖酶和麥芽糖酶活性的提高(Kelly等,1991b),而其他研究則發現斷奶后導致蔗糖酶、異麥芽糖酶和麥芽糖酶活性下降(Miller等,1986;Hedemann和Jensen,2004)。研究結果上的差異可能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如試驗設計、試驗日糧組成、動物日齡、分析和統計方法以及檢測時斷奶后天數。
在部分研究中,仔豬斷奶后3 d二肽酰肽酶IV、氨肽酶N和堿性磷酸酶活性降低(Tang 等,1999;Hedemann等,2003),但是在其他的研究中未發現相同結果(Marion等,2005)。這項研究的實用意義幾乎很小,甚至沒有,因為仔豬很少會在2周齡內斷奶。斷奶對三肽酶的活性沒有影響(Collington等,1990;Hedemann等,2003)。由厭食導致的饑餓和由絨毛萎縮引起的腸細胞發育不成熟可能是導致斷奶前后腸道刷狀緣肽酶活性降低的原因(Kim等,1973;Hedemann等,2003)。
有研究報道刷狀緣酶活性會出現一個短暫下降,酶活性通常在斷奶后3 d~5 d降至最低,而后逐漸提高(Hampson和Kidder,1986)。斷奶后前5 d刷狀緣酶活性的提高,可能是由于隨著日采食量的提高導致酶作用的底物供應增多(Pluske等,1997)。例如,相較于限飼的仔豬,持續供應營養物質的仔豬,其腸道中異麥芽糖酶和麥芽糖酶活性較高(Kelly等,1991b)。 表2總結了最近有關斷奶對仔豬腸道刷狀緣酶活性影響的研究結果。
1.2.3 腸道的分泌和吸收功能(液體和電解質)
隱窩細胞分泌液體和電解質以及從腸道腸腔吸收營養物質是小腸主要功能的一部分(Pácha,2000;Xu,2003)。小腸分泌是一個天然的生理現象,是營養物質消化和吸收必備條件(Kaunitz等,1995;Pácha,2000;Wapnir和Teichberg,2002)。然而,當流入腸道的液體和電解質超過流入血液的量時會導致出現凈分泌狀況,這可能是分泌型腹瀉的一個誘發因素(Pácha,2000;Wapnir和Teichberg,2002)。斷奶會減少液體和電解質的凈吸收,導致仔豬小腸對營養物質的吸收出現障礙(Nabuurs等,1994;Miller和Skadhauge,1997)。
斷奶后小腸吸收和分泌功能的改變具有腸部位依賴性。例如,Boudry等(2004a)報道,斷奶仔豬空腸對Na+依賴性葡糖吸收增強,而回腸中的情況卻相反。同樣的,空腸的基礎短路電流(basal short-circuit current,一種離子運輸的度量單位)提高。然而,作者認為應謹慎解釋空腸吸收能力增強的原因,因為這還伴隨著空腸絨毛萎縮和酶活性的下降。因此,空腸吸收能力的增強或許很少有或沒有生物學意義。剛斷奶時回腸吸收能力的降低可能由于后腸營養物質數量的增加而導致滲透性腹瀉發病率提高。
未完,待續。
原題名:Gastrointestinal health and function in weaned pigs: a review of feeding strategies to control post-weaning diarrhoea without using in-feed antimicrobial compounds(英文)
原作者:J. M. He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