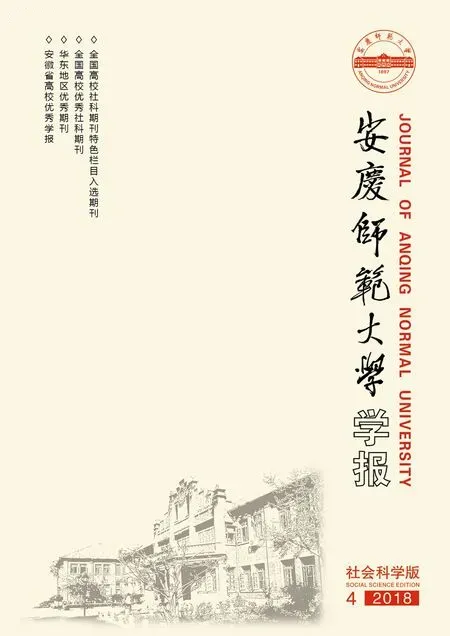個人與社會:20世紀初反獨身敘述何以可能
楊藝帆,林曉萍
(東北師范大學日本研究所,吉林長春130000)
新文化運動以來,自由平等觀念漸入人心。在此歷史環境下,青年追求個人自由之風潮一時興起,其中一重要表現,即為擺脫傳統家庭倫理、追求個人婚姻自由的“獨身主義”的提倡。此間,各報刊紛紛登載“獨身”“不婚”等報道,對獨身者何以獨身、獨身者如何自處,乃至于從醫學方面探討獨身之利弊等話題進行討論。同時,以“獨身”話題為素材的文學、藝術作品亦是屢見不鮮,民間亦有個人行獨身禮以表志①參見福五:《獨身者加笄》:“陳展媛,京綏鐵路局公務處長之妻妹,年來親友多為止說合,女士目睹女子醉心自由戀愛,多自尋煩惱,毅然拒絕。年及古禮加笄,故而行獨身加笄禮。號稱加笄禮,實際上無參照古禮。向祖先牌位三鞠躬、向家屬一鞠躬、向嘉賓一鞠躬,最后且有演說。”(《女朋友》1927年第1期。)、倡獨身結社之例。“獨身主義”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不可小覷之思潮。本文從“獨身”討論的另一側面——反“獨身”言論入手,來探討這場“獨身”討論究竟反映了社會對個體怎樣的關懷與期待,在此種歷史境遇中獨身者又是如何自我定位,進而從輿情熾熱中抽離出個人的境遇的抒懷,并試圖探尋獨身者們背后的時代脈絡。
一、立志不嫁:女子獨身互助團體與近代獨身論之興起
痛感于近代中國民主政治未經歷過真正的思想文化革命,而徒有其憲政外殼,難掩政治腐敗之實,1915年前后,新文化運動在文化領域中開展一場思想革命,以檢討和重新構建近代中國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形態。在此情況下,切人倫日用之要的家庭婚戀問題也開始為輿論所矚目,其中,又以女性的獨身問題尤為突出,開近代獨身問題討論風潮之先。
在新文化運動之前,雖有《獨身稅》(《東洋》1907年第1期)、《雜俎:侏儒女子之獨身》(《四川》1908年第1期)、《獨身的詩人:林和靖》(《學生文藝叢刊匯編》1911年第1期)等數篇報道女子獨身的文章,但就其內容而言,不過是供人們茶余飯后消遣娛樂之談資,在社會上并未形成氣候。1915年前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自發的婦女獨身互助團體逐漸發展壯大,例如獨身女子保險協會:丹來有所謂老處女保險協會創于十七年前女子至十三歲即可,加入此會如四十歲后尚未結婚,會中每年有一年之年金給之[1];女子不嫁會:江蘇南京石壩街有富家少女15人于1916年組織不嫁會,推舉葉寶蓮女士暫時總理會務,并制定規則,要求人會者“不但以終身不嫁為哲,且禁為種種冶艷之姿態”[2]。1917年江蘇江陰縣某女學校,有8名年長之女生,秘密創立了“立志不嫁會”,該會“以立志不嫁,終身自由為目的”[3]。
從不嫁會“以立志不嫁,終身自由為目的”為宗旨出發,不難看出這類行為的“叛逆”的特征:從其具體實施綱領來說,以“終身不嫁”和“禁為種種冶艷之姿態”等反女性化特征的行動來表達擺脫對男子的依賴、爭取與男子平等之地位的做法或稍顯極端而粗暴,以“終身自由為目的”的自我表達是或太過泛泛而模糊,尚且存在未對“獨身”行為的自我定位、價值取向進行厘清等問題,從而導致在今人看來其所作為僅僅流于表面。但毫無疑問的是,婦女的獨身動態的內在立場指向性是十分明朗的,即來自婦女對傳統家庭倫理之束縛的不滿及其追求自由生活與平等的社會地位之意愿。
這種女子獨身的動向引來報刊輿論的關注,以致漸成規模。最早討論起來是1915年盧壽篯刊登在《中華婦女界》的《婦人獨身生活問題》。文章認為,婦女追求獨身的原因在于“歐美婦人能力實際日漸進步,二十一國聯合婦人選舉權大運動會即其見端也”,用以說明國內婦人獨立之動態實為西風日漸之所在。他分析了包括不婚和離婚在內的兩種獨身的類型,并結合這兩種類型的獨身婦女的具體情況,討論了不能獨身的理由。在他看來,“受教育之女子,其組織家庭時對于所生子女實施教育,足為國家社會道德之源”,而且,獨身婦女失去了家庭之樂,在無經濟獨立能力時不應該追求獨身生活。作者雖然也諒解女子尋求獨身的苦衷,但認為我國女子能維持獨身生活者寥寥無幾,而所謂真正地追求婦女權利也不在于獨身,而在于“良人動作妻亦動作”[4]。此外,代表性的文章還包括丁福保在《中華醫藥界》發表的《論婦女獨身生活之運命》。丁福保與盧壽篯一樣,認為婦女是在受到歐美各國女子平權運動影響,在接受教育與實現經濟獨立的情況下,選擇了獨身,但是堅持終身獨身行為會導致婦女自身在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因為“自生理及心理上觀察之女子之腦力及體質,決不能與男子相競爭”,故而婦女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不能不依賴男子。文章還從近代醫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終身獨身有違生理需求,并引用外國研究之說,認為婦女性欲雖然不如男性,但仍有性欲,且在三十歲左右達到盛期,以此來作為其反對獨身的依據[5]。
從上述的“獨身”問題討論來看,其討論主體很大程度上限定于女性,對婦女獨身多持反對的立場。就盧文而言,文章表現出濃烈的家國情懷,“受教育之女子其組織家庭時,對于所生子女實施教育,足為國家社會道德之源”[4],強調知識女性對國家社會所能間接起到的作用,以此巧妙地將女性在家庭中的生兒育女的具體行為與國家社稷之道德風尚聯系起來,從而來喚起女性的社會責任意識。在承認女性對國家社會所能起到作用的同時,卻又以無經濟獨立能力時不應該追求獨身生活,我國女子能維持獨身生活者寥寥無幾為理由,把問題指向了女性實際經濟狀況的困窘,回避了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承認,而得出了女性應該照舊依靠男性的結論。丁文則直接從生理上否認了女子在社會中的競爭力,同時還將原本為婦女問題的討論主體泛化為對獨身行為的合理性的討論。無論是盧文還是丁文,均回避了婦女獨身行為向社會拋出的女性平權問題的回答。
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獨身”問題之討論迸發于近代女子獨身互助團體現象的出現,可以說,從此時起,對于女性的獨身問題的關注一直貫穿在近代獨身問題討論中,引發了五四時期社會對全體社會成員獨身問題的關注。1919年,胡宗瑗在《婦女雜志》上發表《獨身主義之研究》,文章分別列舉了各社說中所認為的男子與女子獨身之利害,尤其對男子獨身之利弊進行了詳盡的說明。在男子方面,作者認為獨身有利者有:“其一、無妻子之相累二易于謀生也;其二、無妻子之分愛情而便于研究學問也;其三、無所牽慮而能盡瘁社會公益且能以身許國也;其四、無色欲伐性而利于衛身”。而獨身其害在于:“其一、陰陽配偶乃天地自然之理”;其二、蓄養妻子以致謀生之道維艱;其三、彼主張獨身主義者謂娶妻生子則有害于研究學問;其四、娶妻則有妨于愛國或有害于衛身。”對于男子獨身之害,作者不以為然:“由以上各說比較而參觀之,則主張獨身主義者,無一正確之理由。其所持理由,大抵皆感于女子無學,致為男子之累。因之而抱獨身主義”。而至于另外一種“含有宗教之意味視情欲為罪惡,則女子學問任何高尚,在彼終無以易其初心”。可以看到,作者開始質疑“女子為男子之累”的說法,認為女子有學問便不至于成為男子的負累。但女子有學問是否進一步意味著女子獨立之可能?并不盡然。文章在分析女子獨身之理由時提出,女子獨身大抵與男子相同,但有兩種區別:“一避生產是也;二畏束縛是也”。對于后者所謂“束縛”之說,作者認為“女子之天性,終弱于男子”,因此女子一旦結婚,難免漸漸事事依賴男子,最終從天性上處于弱勢的說法,來否認婚姻關系中女子獨立的可能[6]。
從這一時期討論的特點來看,其一,討論的聲音從一開始具有著重談論女子獨身的強烈性別意識,漸漸將重點擴大到談論獨身行為本身,討論對象不拘于性別、年齡、社會地位,獨身行為的主體在討論中逐漸呈現多樣化趨勢。其二,這一時期的反獨身論中強調了女性獨身有悖家國責任的論斷,這種論斷的背后間接反映出了相對于以往這一時期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直視了女性在公共領域所起的作用,同時也逐漸走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女性受教育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上述的獨身行為主體多樣化的傾向以及對女性社會地位的關照也為此后獨身討論所延續,該時期的討論也為其后獨身討論的擴大鋪陳奠定了基調。
二、獨身者的自白:近代獨身者形象之探析
隨著獨身討論的展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不僅僅是或“堅強獨立”或“離經叛道”的獨身女子,其他獨身群體也漸漸為人所知。葛敬洪在《獨身主義的批評》中談到:“獨身主義這個名詞在我們中國本不成問題;因為除了那些在庵堂廟里敲木魚的僧尼,和道姑有的過獨身生活之外,其他青年男女不因別的緣故,純粹抱獨身主義的人,實在是很少數……可是自五四運動澎湃以來,智識界受了一番很大的改變”[7],獨身主義漸漸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輿情熾熱之下,人們不但持續關注著婦女(尤其是知識女性的獨身問題),而且也將目光放及社會全體獨身者。社會對獨身者的看法隨之通過以評論、短篇小說為主要載體的獨身論而自然流露。
有些文章將獨身者與已婚者置于對立的立場上,以已婚后家庭生活的瑣碎、束縛來反襯獨身生活的自由、浪漫,例如笑博《我為甚么羨慕獨身》從已婚者婦女的角度來告誡未婚女子,婚后生活極為單調,女子承受家務繁重的同時還要忍受孤獨[8]。也有不少文章對獨身者或為了自身的學業、事業或為了社會大我而獻身的精神示以欽佩,行文之中贊許之情滿溢,如原田實原的《唱母性尊重論的愛倫凱女士為什么獨身》便極力贊揚愛倫凱女士學習耶穌基督保持獨身,為了兒童與婦女事業而犧牲自我的行為,塑造出了無私的獨身者形象[9]。雖然這些文章中的獨身者形象似乎總是自由自在、勇于自我犧牲的,但獨身者們本身是否認可這種形象則尚未可知,下文一個獨身者的自白或能提供些許參考。
1923年,大學預科生、獨身主義者的羅元駿,在《我的獨身主義》中認為,“人之嗜好,至不相侔”,獨身不過是個人嗜好所向,而且“近來男子不娶,女子不嫁,抱獨身主義者,各國人數日眾,在我國數亦不少”,以此來強調自己獨身行為的普遍性。面對他人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如子獨身,寧非不孝?”獨身不孝論的責難,羅元駿一方面以現實生活中“慈母明達不欲干涉”明確從家庭本位的立場駁回不孝之說,另一方面則以社會為重的態度回應道:“夫個人為社會之分子,無后與一家一姓何關,烏得為不孝?”并進一步批判對反獨身論者存在傳統社會中拘泥于小家的保守一面:“此以我國歷來家族觀念,根深蒂固,遂致謬說流傳,貽害無窮,正不得不辭而辟之也”。一番一一辯駁,格局之大,頗有凜然之氣,然結尾之際卻又對自己的獨身行為充滿自嘲:“然元駿固甚屏情思于腦外,永度畸人生活,得以清閑之歲月,自由之身體,浸淫于學術,盡瘁于社會,毋不幸而為兒女之情所糾纏。”[10]從羅元駿的自白可以看到,一方面,雖然五四以來自由之個體的社會觀念日增,但個人主義并未在社會中扎根,羅的婚嫁為個人嗜好、個人選擇之說太過單薄,其論述最終還是要回歸家庭、回歸社會集體,從家中慈母明達,從羅本人自愿奉獻社會這一偉大志向等符合傳統倫理價值的說法中尋覓合法性,如是,也只能以“畸人”二字自認,可見羅本人心間苦澀的同時,也反映出了當時社會對獨身者的印象之一。那么,時下社會為何對獨身者留下“畸人”的印象呢?
1922年都良的《一部分女子的獨身問題》或能解釋一部分問題。首先,都良對獨身主義的評價定下基調:“獨身主義的蔓延無論如何總是社會上一種不好的景象,也盡可說是社會病態的表現。”[11]這個說法與羅元駿的“畸人”說法大體一致。在他看來,女子獨身的原因有五種:其一,秉受異樣氣質,懷抱純潔思想,真能拋撇一切情性的他們非但能夠安然過他獨身生活,而且還能遺棄榮利名譽以及其余種種欲望打破一切塵俗的觀念。從第一點來看,女子的超然姿態尚且不算是一種“病態”的表現,其后作者也認為這種獨身者僅鳳毛麟角。其二,受惡環境的逼迫、舊道德的制裁,不得不抱獨身主義或在特別情形下為他人而甘守獨身。這個說法道明了最初女子獨身運動的原因之一,作者也對處境艱難的女子予以了同情。其三,負孤介的性情高傲的意氣不愿過舊家庭制度下的瑣屑生活,又鑒于世上男子都不可靠或從別方面受了刺激,兢兢內懼甘自以獨身終局。其四,不滿意于舊婚姻制度,又不敢公然有所主張,用消極方法拒絕父母給他擇配的提議,表明任何人家都不愿就。其五,并未充分了解獨身意義,亦未經過徹底考慮,只震于獨身名詞的新穎漂亮,略一受著刺激便投身到那面旗子下去。在作者看來,她們所遇到的問題其實“并不是獨身問題實在,只是擇婿問題,換言之要改良婚姻制度罷了”。認為獨身主義的出現時由于當前舊家庭制度的存在與“書本上提倡自由戀愛”的雙重影響下,受教育女性一方面不具備徹底改變傳統家庭制度的能力,一方面又羨慕自由戀愛婚姻,于是不得不選擇獨身。經過上述討論作者認為選擇獨身是一個錯誤,主張婦女提出“緩婚”,認為“一般思想開明的女子非有特別苦衷總不應輕易提出獨身的主張,不妨退一步抱定一個緩婚主義罷”。言辭當中帶有責備之意,但這與其說是針對獨身者獨身行為本身,不如說是對獨身者們面對婚嫁人生大事時的態度進行批判,或消極以待或態度輕率,便以獨身自居,這在作者看來,終究是不能實現真正的兩性平等的,“緩婚”折中或許才是最好的選擇。從中可以看出,從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所強調的積極地進行社會性實踐的性格的流動與延續,其社會改造的愿景也漸漸和獨身討論這種日常生活融為一體。
但這種“文化改造”性格的緩和式的批評,在五四時代后期,卻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獨身有害論。1926年,彭道明在《婦女雜志》上撰文,以較為激烈的言辭極力反對獨身主義。在這篇名為《非獨身主義》的文章中,作者總結了獨身生活的幾個原因:一、生計困難;二、自私心盛;三、風俗淫靡;四、法律禁止(這些獨身者是殘疾者、犯罪者等時代的落伍者);五、理想太高(在知識階級占多數,且有部分人行同性愛之行為);六、時代關系(時代風潮,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不愿婚嫁)。作者借美國社會學教授之口來說明獨身生活對社會的弊病:“早婚有害,但人類晚婚與獨身之害,甚于早婚……據美國社會學教授鄂鵬(William Ogburn)研究:離婚與獨身之犯罪數四倍于已婚者。”而所謂未婚的犯罪方法包括“酒醉、邪行、無賴”。由此作者得出結論:“已婚男女多都屬社會上良好之公民,故能安分守己,無軌外之行動;男子得女子輔助,犯罪自必減少。”作者認為,獨身者最終的結局便是“寄生”:養老院、撫養院多為鰥、寡、孤、獨之人,寄生原因在于貧窮乏人照顧。而且,獨身者死亡率極高:未婚者死亡率比已婚者高,為年在八十歲以上不在此例。三十五到五十歲之間死亡率兩倍于已婚者。原因雖無調查,但可推斷:未婚者易輕生,漠視衛生常規;精神上未得安慰[12]。此文所論偏離了一開始針對婦女獨身行為所展開的討論的方向,新文化運動以來進行“文化改造”的初衷也儼然消失,從對社會的功用的角度出發,獨身者對社會而言已不僅是“畸人”,更是“罪人”。
報刊中討伐獨身者的除了上述激烈論調之外,亦有不少揶揄、調笑獨身者們的“假”主義。例如,洪白萍的《小說:獨身主義》就描寫了一位奉行獨身主義的青年哲學教授后在朋友家見到婦女月報總編輯吳女士,二人因討論楊墨哲學互生情愫,后結為夫妻的故事。小說對教授的“假”獨身主義表示嘲諷,認為所謂奉行獨身不過是未遇見意中人罷了,借此嘲諷時下獨身主義流行不過一時意氣,所謂的“主義”并不堅定[13]。靈蘭的《歌場:獨幕喜劇:獨身主義》則講述了一青年一面宣稱自己奉行獨身主義,另一方面又在心理暗中衡量兩個追求者誰優誰劣的故事,借此暗諷借主義之名,行朝三暮四之實[14]。可以說,此類批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在“自由戀愛”旗幟下,抱獨身主義以待價而沽,追趕潮流而游戲情場的部分青年的現狀,從這一意義上也不失為一種道德規勸。但另一方面,這類小說存在將獨身主義視為終身獨身、不與異性往來、保持所謂的“貞潔”等,從而將獨身這一蘊含的多種可能的行為固定化、結論化,而對獨身者行獨身行為并非為了絕對的“獨身”而“獨身”,主義所指向的目的是規避被傳統婚姻所束縛這一前提視而不見。
就此時的獨身批判論來看,獨身行為將個人從傳統家庭倫理中解放的功能已經不再重要,反之,這種帶有個人本位色彩的行為在國家走向全體化的過程中,被視為是違背“科學”與“人倫”之舉、是對社會全體“秩序”和“紀律”的挑戰與破壞,而獨身者的形象也經由“畸人”進而變為“罪人”。而五四以來的獨身倡導之所以徹底而激進,正是由于其群體是受過近代新式教育的知識群體和學生,理想主義促其主動或被動地勇敢以獨身來破舊的同時,過于注重理想而無所顧忌現實條件的獨身群體勢單力薄,難為長久之計,已然難以通過“獨身”解放自己。
三、近代獨身主義何以難以為繼
如果說,最早的獨身討論熱潮源于婦女獨身行動的興起,那么隨著問題討論的展開與深入,反對獨身的聲音漸漸成為主流,獨身行為被看作是“人類普通生活的一種變相,原非正大之途”[12],獨身行為的危害成為輿論焦點之所在。
論及獨身行為的危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獨身者個體本身所造成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危害,例如徐江左《言論:獨身主義底危險》便認為,人有和其他動物同有的肉體生活,有食欲和性欲的本能沖動,及人所獨有的精神生活,而“此二種生活不能相離”,“擬以獨身終老者……一旦因性欲的沖動,反陷入迷途,輾轉墮落;或因遏制過甚,轉生疾病者。又女子過期晚嫁,致罹難產者,在所多有;此皆由違反生理之故。”[15]這種“獨身行為將對行為主體造成危害”的描述又在輿論喧嘩中使得獨身者被“想象”成是“畸人”,他們或“傲慢自負,‘歇斯底里’性的多言和冷嘲熱諷,帶有殘忍性、用心過分”[16];或“恬不知恥,荒唐百端,不堪聞問”[17]。結果總是“孤僻頹喪和對于生活之厭惡與絕望”[18]。正是這種社會想象使得獨身主義在個體本位上遭遇滑鐵盧。
但如果獨身者僅是“畸人”,或許尚不足使得反獨身言論甚囂塵上。而是在近代,“畸人”身份所隱含的是無法背負起時代任務的“罪”,也即反獨身論中最被強調的獨身行為的另一方面的危害,對被具體表達為社會、國家、民族、種族甚至人類等某一社群的危害。正如黎景云在《論獨身主義之當否》中認為:“然則此主義當耶否耶,曰:其自為謀也,未嘗不善;若為家族謀,為國家謀,則吾未見其可也,當二十世紀以還,無一非弱肉強食,鄉蠻械斗,強凌弱也,國際戰爭,強吞若也,茍此主義實行,人皆效之,斯種不期弱而自弱,不期滅而自滅,豈非自取敗亡之道哉,吾之所以不能無疑者,蓋為此也。”[19]彭道明也在《非獨身主義》中說道:“獨身生活,原非正大之途,若實行之,充其量,必致優秀的種類,后裔漸衰,劣等的種類,生育日盛,社會何以進化,國家何以存留。”[12]
上述的反獨身敘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傳統中國儒家文化中以家族為本位的婚姻倫理道德定位在近代中國的延續。而家族本位的婚姻其目的是繁衍子孫,廣繼后嗣[20],“合兩性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嗣也”,這種延續后嗣的想法,在時人羽公看來,便是所謂“慮后之心”。羽公認為,“人生之意義,半在夫繼承遺傳之義務也。蓋承先啟后。雖為家族觀念囿之而又此見地也。但以古圣賢所謂君子疾沒而名不稱焉。其中微意,亦有以無后為慮之意也。夫名立于國家社會者。非立德立言立功不能有此報稱也。若無所立。歿而無名矣。于是不能不于家族中而思獲其名。”另一方面,隨著近代資本主義以船堅炮利打開國門,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主義焦慮情緒便籠罩著整個近代中國。如同克都列所言,東方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接受了赫爾德等宣稱語言獨一無二地定義了一個民族的論點,從而強調歷史是一種獨特的思想方式,民族不但有過去,還要求要有一個未來[21]。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打造出來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自由主義的行動指南,賦予了獨身行動浪漫、激進、理想化的藍圖。但是,隨著理性的權威在社會認可的逐漸確立,有組織的工作形態、為家國的無條件犧牲的集體精神開始為報刊宣傳所倡導,而與之相對應的,進化論意義上從古至今不斷進步發展的“民族”“國家”這一社群形態逐漸被塑造出來,在五四運動的革命政治觀念興起之際,獨身敘事便受到了更大的沖擊。隨著“公民”觀念在近代中國的逐漸確立,“廣繼后嗣”在近代的意義已經不再局限于家族內部“私”領域思獲其名,更是具有包括“國家存續”等事關國家民族等“公”領域未來的重大功能,相對應的獨身主義也便被視作破壞國家與民族“未來”的罪魁禍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反獨身論一步步吞噬獨身主義在近代社會的合法性。而婦女,作為傳統家庭中相夫教子、生育功能的主要承擔者,其獨身行為違背了傳統家庭道德倫理與民族國家的繁衍種族的期待,便顯得更加不可饒恕。
在獨身危害的指責中,輿論更多將矛頭指向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如吳罕庸在讀了東心一篇倡導女性獨身自立的文章之后以《讀“為什么獨身女子這樣多”以后》道出對社會的擔憂:“現今我國教育還沒有普及,這是大家知道的,所有的即為鳳毛麟角的女士們,倘若再不在大處著念,僅僅為了本身歸宿的恐懼,而迷惑了人類應負的使命,養成‘自矜’‘超然’等畸形的發展,這不是我國教育前途的惡現象嗎?再者倘若此風長存,知識階級的女子,都愿獨身以終,那末優秀民族將逐漸減少;而愚昧弱劣的份子,同時將倍增起來,結果中國的半殖民地位還恐難保吧。”[22]宜遠在《今日女子獨身的原因》中附言:“獨身的女子,大多知識充足,學問淵博,辦事干練,富有思想,倘使移她們的才力,用于家庭,那末對于家庭組織,子女教養,定多貢獻,所以這種自私性的獨身主義,間接直接影響社會不淺。”[23]憲昌在《高等敎育與婦女獨身問題》亦表達了知識女性的獨身行為將導致亡國之憂,他以羅馬亡國于男子不婚為鑒,告誡女子對于獨身主義千萬審慎:“女子既經受得起高等教育,聰明智慧,當然是社會上最優秀的分子,非實在有強健身心的人不能做到。根據優生學的原理,她們一定是社會的良母,所遺存的一定是最純粹幽雅的成分。但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這許大部分的強健身心的女子都取了獨身主義的態度,不是極可惜的一回事嗎!”[24]對知識女性的指責不單單在于其不繁衍后嗣,更是從優生學的角度,來強調女性對自身才力的浪費。而這種優生學的角度,還與獨身文明論息息相關。
20世紀20年代也存在部分報道將獨身主義潮流引為文明標志,將其與一文明發展程度掛鉤,例如,李宗武《獨身主義之問題》便指出:“法蘭西人口已在停止狀態,獨身的奉行程度與國家文明程度呈正比。”[25]其另外一篇文章《獨身的傾向與危險》中提到:“抱有獨身主義者,開化地區多于未開化地區,文明程度高者多于文明程度低者,女子較多于男子。”[26]被翻譯并刊登在《晨報副刊》的衛斯脫馬的《人類婚姻史:第七章:婚姻及獨身(續)》也介紹了文明國家出現獨身現象的原因,認為是由于隨著人們文化程度增加,更重視追求精神相契合的婚姻關系[27]。但這種獨身文明論的目的并非在于提倡獨身行為,而是在無形中提醒著另一個更為“文明”“開化”的“他者”,從而傳遞出一種“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的邏輯在便具體體現為優生論的提倡。李宗武“好種始得好果,好果之來,必自好種”,而現在獨身者一般為智識階級,智識階級不生產,“勢必逐漸遞減;而無智識階級,則依然竭力發揮其生殖本能”,從而導致“低能之男女,或更特別多產”,結果將導致“優良分子逐漸減少”,“而愚劣分子則逐漸增加”,使得“社會組織完全歸于低能男女之手,世界文明頓呈一落千丈之勢”[25]。這種“進步”的邏輯與半殖民地國家恐怖“落后”的民族焦慮交織在一起,勾勒出以歐洲普世價值所倡導的文明的、進步的未來,而承擔起向這一未來邁進的,無疑是知識階級及其后代。
此外,隨著近代國門大開,西方思想意識,如個人主義、公民權和公民社會“自由”等逐漸進入中國。“自由”之潛臺詞,是父權的資產階級核心家庭理想[28]。葛敬洪在《論說:獨身主義的批評(續)》說:“西國優美的家庭,他的主婦多半在家里主持家政,丈夫一早出門工作,到晚歸來的時候,他的夫人全身穿了很漂亮的衣裳歡迎著,房子里陳設得很齊整,什么東西都為他預備好了。”這種生活狀態如“天堂”。這與傳統中國家庭倫理當中對女性“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的定位恰恰是不謀而合的。故而“……鞠育子女,是天所賦我們婦女的職責;所以我們一面去努力服務社會;一面也不可把這個職責忽略不顧”[29]。反觀最初反對女性獨身論調,此時的女性已經不再是男性的負累,亦不再生性柔弱,相反,新式女性——學問品德具佳者——被要求找到家庭與社會的平衡,被強調應承擔起幫扶家庭,使其作為社會子個體而穩固國基的責任,同時運用其生育功能,繁衍后代而實現“國家”“民族”興盛和延續。雖不再是男子的負累,但女性在這場獨身主義討論中是否獲得獨立之性格呢?社會雖重視女性在公私領域的功用,但女性個人本位的訴求卻在討論中被淡化。回溯最初女子獨身團體的訴求,奉行獨身主義或許只是一場個人本位在全體性制度下無可奈何的大逃離。在新舊交替的半殖民的近代社會中,民族危機的迫近使得獨身主義并未能實現其最初性別解放的目的,獨身本身所含有的個人主義傾向也在革命全體性話語中被抹殺,并最終歸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