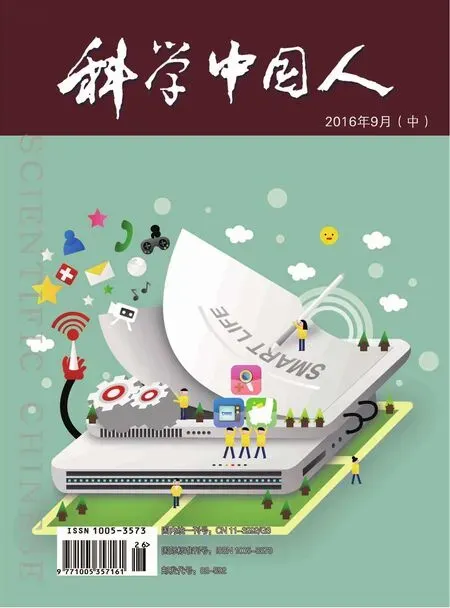張健:構筑大醫學之道
本刊記者 陳 浩
張健:構筑大醫學之道
本刊記者 陳 浩
2015年,“健康中國”被寫入“十三五”規劃,大健康第一次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這里所說的“大健康”,指的是一種全局觀,根據隨時代發展的各學科基本科學概念的演變與重新認知、疾病譜的改變以及社會需求應運而生。大健康圍繞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關注各類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和誤區,提倡自我健康管理,其核心理念就在于對生命全過程進行全面關注與呵護。這意味著,大健康不僅注重個體身體健康,還包括精神、心理、生理、社會、環境、道德等方面的完全健康。因此,大健康“治病”,也“治未病”。
財經小說作家梁鳳儀有一段話流傳甚廣:“健康好比數字“1”,事業、家庭、地位、錢財是0;有了“1”,后面的“0”越多,就越富有。反之,沒有“1”,則一切皆無。”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健康的訴求,令大健康理念有了發生發展的土壤。從透支健康、對抗疾病到呵護健康、預防疾病,一種更為科學、合理的新型健康和醫療模式正在逐漸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觀之中。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精神下,2016年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確立了“以促進健康為中心”的“大健康觀”“大衛生觀”,提出將這一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實施的全過程,統籌應對廣泛的健康影響因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維護人民群眾健康,明確將“全民健康”作為“建設健康中國的根本目的”。
既然傳統的以疾病為中心難以更好地解決人的健康問題,單因單病的生物醫學傳統模式逐漸力不從心,在“生物—社會—心理—環境”的大健康模式轉型過程中,醫學模式該如何科學地排除或減少健康危險因素?如何實現個人的健康管理?歸根結底,又如何跳出傳統生物醫學的局限,建立起明確的“大醫學”觀?
面對一系列問題,深圳大學醫學院教授、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醫學博士張健一直推崇和探索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社會群體的協調與融合,他認為應該建立起以“生物—醫學—社會—心理”相結合的整體醫學觀念,系統、全面、有機地來認識、辨別、處理、診斷、治療和康復疾病。
康德曾說,有兩樣東西,愈是經常和持久地思考它們,對它們日久彌新和不斷增長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實著心靈:我頭頂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于張健而言,“生物—醫學—社會—心理”大整體醫學就是他“頭頂的星空”。
“大醫學”是大勢所趨
生長與變化是一切生命的法則。“大醫學”觀就是隨著變化循序漸進地出現的。而這種變化,也表現在多種角度上。
進入20世紀之后,世界各國先后出現了以心臟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占據疾病譜和死因譜主要位置的變化趨勢。早年間由天花等傳染性疾病造成大幅度死亡率的現象已經成為歷史,與之相對的,是世界各國對癌癥等慢性病的高度重視。1971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提出,應該集中像研究核裂變以及登陸月球所付出的力量來向癌癥宣戰。2017年,中國也在《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中承諾,到2020年將總體癌癥的5年生存率提高5%,到2025年提高10%。這種嚴陣以待,正是由于人類的疾病與死因結構發生改變而造成的。
當人們在保護健康和防治疾病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值,認識自然也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心理與社會因素越來越被凸顯出來,健康思維也日趨全方位、多層次。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很多人已經意識到,疾病預防是促進健康的有效手段,而疾病的預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而不是單個人的活動行為。只有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通過廣泛的健康教育、公平合理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以及社會多部門的合作等社會措施,才能達到減少疾病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保障人人健康的目的。當然,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的增加,人們也有能力對衛生保健提出更高的要求,更期望從身體狀態到心理狀態和社會活動能力都得到質的飛躍。這一點,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無法使之得到滿足。
“生物—醫學—社會—心理”大醫學模式試圖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但這個被張健寄予厚望的大醫學模式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拋開單病單因的局限,醫學的發展必須要抓住多病多因的現實情況,而多病多因就要考慮環境健康。1974年,布魯姆提出環境、生物、行為生活方式、衛生服務這4大因素都影響著人類健康,其中環境因素包括自然和社會環境,特別是社會環境更是對健康有重要影響。隨后,拉隆達和德威爾對此進行了修正和補充,認為4大因素可以分別細化出3個因素,而且各類因素對不同的疾病影響是不同的,如心腦血管病以行為生活方式、生物因素為主,意外死亡以環境因素為主,傳染病以衛生服務因素為主。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教授恩格爾就直接多了,他直截了當地點出應該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取代生物醫學模式。在《科學》雜志發表的文章中,他指出,生物醫學模式關注導致疾病的生物化學因素,而忽視社會、心理的維度,是一個簡化的、近似的觀點。這個模式已經獲得教條的地位,不能解釋并解決所有的醫學問題,為理解疾病的決定因素,以及達到合理的治療和衛生保健模式,醫學模式必須考慮到病人、病人生活在其中的環境以及由社會設計來對付疾病的破壞作用的補充系統,即醫生的作用和衛生保健制度。
大醫學的發展已成必然之勢。在國內,張健則希望這一模式能夠符合本土化要求,以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多學科交叉,結合他所擅長的專業角度出發,走出一條更加接地氣的路。
為大整體醫學添磚加瓦
對張健來說,他不僅是一位醫學科學研究者,還是一位具有20多年豐富診療經驗的資深臨床專家。這決定了他在對研究方向進行定位的時候會從臨床整體思路出發。
“一般來說,臨床診治有3個不同的思考和處理環節”,張健說。第一步,當疾病嚴重危及到患者生命時,醫生首要考慮的是竭盡所能地去挽救病人生命;當病人不存在生命危險,或已度過生命危險期時,就要進入到第二步,此時醫生首要考慮的是如何去保障病人的有效生命質量,并以此作為制定治療方案和藥物選擇的原則和評判依據;當“有效生命質量”也不再是主要問題時,那么要考慮的就更加深入了。“疾病以及對疾病的診治多多少少都會對人造成傷害,此時,我們除了考慮和保障患者軀體的康復,還需要考慮病人心理狀態的康復,如自我情緒的平穩,以及與社會的正常交往情況,以達到良好的軀體康復與心理康復的有機協調整合治療。這也是整體醫學觀的表現之一。”

閑庭信步
談到整體醫學觀,就不得不提及長期以來占據主流的生物醫學模式中存在的局限。生物醫學模式中的“單病單因”,事實上是習慣將系統分成部分。舉個例子,當不得不面對一臺復雜的機器時,生物醫學模式下可能會將機器拆散成幾千、幾萬個零部件,分別進行考察,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但耗時費力,效果還未必理想。而在整體醫學觀的指導下,則會把機器運行起來,觀察運行中機器的各種反應,從而建立起各種反應之間的聯系,以全面了解整臺機器的功能。
人體這臺“機器”顯然更為復雜,張健之所以強調要注重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社會群體協調融合起來,恰恰是因為人生天地間,就會受到自然、社會等各方面環境的影響,這些影響往往是無法拆分、難以量化的。因此,疾病的病因機制、發生發展等,也要放在整個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層面,去觀察其整體的群體分布,尤其是各因素的權重和眾數偏向情況,從而找出其權重比值。在此基礎上,來分析各因素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平行關系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等。“不要孤立地看待一個病因和疾病發生發展的因素,要從大生態和整體生態平衡、大社會心理和個體心理等主體因素,從統計的、系統的層面進行權衡比較,并指導一系列的臨床思維、科研思維和研究工作。”張健補充道,“也就是現在所提出的多中心雙盲法。”
在對整體醫學觀有了清晰的認識后,張健近幾年在臨床上的診療工作主要定位在抑郁、失眠、眩暈癥等問題上。從研究手段上具體來說,他主要是采取免疫組化技術、膜片鉗離子通道分析技術,開展癲癇、老年癡呆等相關疾病的發生發展機制和臨床應用基礎研究;采用現代腦電技術,包括腦電圖、事件相關電位以及功能性影像識別技術等,從整體上開展焦慮抑郁,情緒與焦慮,情緒與失眠,長期慢性失眠與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相關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神經損傷康復訓練研究,并采用間充質干細胞技術開展神經損傷后再生的基礎和臨床應用研究。
而圍繞這些問題,張健的另一個工作重心就是開展天然藥物抗癲癇、抗焦慮抑郁、睡眠障礙與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平衡調節以及神經損傷修復與康復等方面的有效活性物質的提取、藥理機制以及臨床應用推廣研究工作。在他看來,既要解決純科學問題,也要解決更好的臨床使用藥物問題。為此,他和深圳大學醫學院一群志同道合者組成研究團隊,成立了小分子天然藥物研究平臺,并與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聯合開展研究,在平臺上構建了針對上述疾病的天然小分子有效活性成分分子庫。這也是目前國內外唯一的天然小分子有效活性成分分子庫。
到底為了什么而研究?張健心底一直都有桿秤,他希望他和團隊的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大整體醫學理念,為了更好地促進“生物—醫學—社會—心理”臨床診療而進行的有針對性的選擇,真正令其在現在和未來得到科學的、規范化的、系統的提升。
“教育之目的在于使人成為人”
“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為人。”在談到如何將大整體醫學觀潛移默化到教育里時,張健引用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觀點。
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的目的也是人,教育的一切理念和行為都會圍繞著人來展開。教育的本質就是挖掘任性中的自然稟賦,使自然人成為社會人,使人成為有價值的人。在這樣一個核心價值觀的指導下,張健認為,不僅要培養學生的學問,更要注重基礎研究和臨床診療思維的培養,同時對于一個未來的臨床醫生,還要從多方面入手進行醫學生的人格、品性培養。教育即生長。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要灌輸以意志力、愛心的培養,以及對社會的奉獻和服務意識的培養,并使這些品質成為學生的天然養分,融會貫通到他們的氣質當中。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關懷”,張健認為,醫護人員的自身修養一定要過硬。用他的話說,醫學院教育出來的學生大多都是要走向臨床的,作為一位醫護人員,這些品質是他們必須要具備的。從教育時期就抓住這一點,既是為了將他們培養成真正的白衣天使奠定前期的基礎,也是為緩解醫患矛盾采取的一個早期措施。
而正因為要走向臨床,在早期的專業培養理念中,更要采用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現代醫學教育模式。深圳大學醫學院自2008年籌建起,就明確了辦學定位——高端、精英、超前、精湛,明確了早期接觸臨床、早期接觸社會、早期接觸科研、雙導師制的辦學模式。
“高端”即建立高端的教學科研平臺,不走一般化路子;“精英”即實行小規模的優質生源,實行導師制培養模式,使學生具有個性化的發展空間,以培養醫學精英為目標;“超前”即教學研究注重超前性,圍繞國際尖端課題攻關;“精湛”即附屬醫院要有精湛的醫療水平,成為深圳最好的醫院,促進深圳醫療科研水平和服務質量的全面提升。
張健介紹,在這種小規模、研究型、精英化的辦學原則基礎上,醫學院實行“1(理工科基礎)+5(醫學本科)+4(碩博連讀)”十年制精英式臨床醫學高端人才培養模式。他們對生源質量和數量進行嚴格控制,每年從大一、大二的學生中擇優錄取30名學生,并為其提供全額獎學金。在醫學院,學生們可以接觸到大量的高端設備,以及超前尖端的科研課題。同時,深圳大學還與美國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等國外著名高校的醫學院合作,醫學院學生在十年制學業中將有機會前往這些學校進修。而且學生一入學,就開始實施雙導師制,每個學生都有一名科研導師與一名臨床導師,讓學生早期就參與科學研究,早期接觸臨床。
作為深圳大學醫學院的早期建設者之一,張健更是將這一理念貫徹到底。“如果學生們能夠從早期就接觸到臨床和社會,就能夠更多地帶著社會和臨床問題來學習、把握、消化、理解醫學基礎課程,如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病理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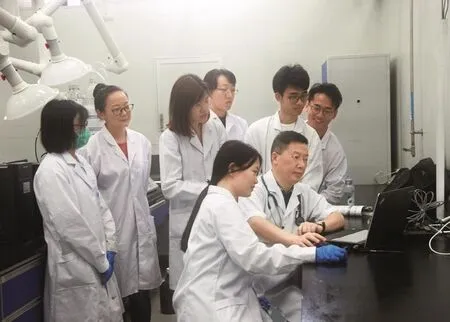
指導學生實驗
要給學生一杯水,教師就要有一桶水。張健所堅持的臨床思維教育當然也源自他本身的實踐。多年來,他領導成立了臨床診療團隊、小分子天然藥物團隊等,圍繞情緒與焦慮抑郁、癲癇、失眠,失眠與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發生發展的相互關系,開展了國家、省市等多項基礎和學術應用研究工作,在國際知名雜志發表了多篇相關高水平研究論文。
身為過來人,張健能夠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理念,對在前期開始醫學基礎課程學習的學生來說,通過早期接觸臨床、早期接觸社會,他們一開始就能帶著社會倫理與心理問題,帶著觸及和感受到的臨床疾病相關問題來學習解剖、生理、藥理、病理等醫學基礎課程,從而能更好地理解、消化、領悟和把握基礎醫學知識點,使醫學基礎課程的學習更加有的放矢,擺脫了大部分醫學生學習的枯燥、乏味、盲目感;同樣,在后期的內、外科等臨床課程學習中,采用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模式,學生反過來又可以用已經學習和掌握了的解剖、生理、藥理、病理等醫學基礎課程的概念及原理,來理解、分析和回答臨床癥狀、體征、疾病發生發展過程與機制,以及相應的診療措施的制定等一系列臨床問題,使其既能更好地有效領悟和掌握相關知識要點,又能使醫學基礎課程和臨床課程的學習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如此,學生們就可以從一開始就進行科學化、系統化的醫學課程學習,從而有利于系統地開展以問題為導向、以臨床實踐為核心的臨床思維、臨床技能和臨床科學研究訓練。
“醫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張健再次強調道。隨著傳統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醫學—社會—心理”大整體醫學模式轉變,醫學人才的培養也要邁向思考型、創新型、實踐型。他也希望能夠培養出更多這樣德才兼備且符合大醫學發展趨勢的醫學人才。

專家簡介:
張健,深圳大學醫學院教授、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醫學博士。長期從事神經病學臨床診療、教學及科研工作。在腦卒中、失眠、焦慮抑郁以及老年癡呆、認知障礙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診療與研究經驗和基礎。采用免疫組化和電生理學技術,在腦缺血、癲癇、焦慮抑郁、亨廷頓病、神經肌肉疾病、疼痛信號傳導與調制等的細胞與分子機制及診療方面開展了系統、深入的研究。近年來的研究興趣擴展至采用電生理及fMRI影像技術開展情緒及認知障礙相關機制研究。發表高水平SCI論文10多篇,主編或參編專著兩部,主持和參與了10多項國家、省、市自然科學基金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