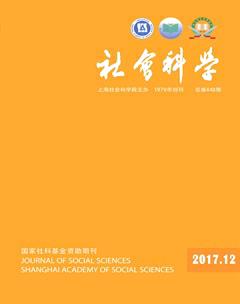當代中國政府回應性的邏輯:基于歷史與現實的分析
王軍洋+胡潔人
摘 要:西方政治理論認為,政府的回應性源自于普選式的民主,贏得選票的壓力促使政府致力于回應至少是平衡不同群體間的各種訴求,循此邏輯,選舉效能不足的體制并不具有回應公民意見的充足動力。然而,來自中國的政治經驗表明,在非西方的體制下,政府在發展經濟和回應民眾訴求方面也可以有很強的動力,甚至回應的效率并不遜色于西方政治體制。此種看似吊詭的政治現象客觀上存在著深刻的政治與社會根源,分析發現,改革開放后四個方面的政治變化促成了非西方體制下的政府回應性,即意識形態的世俗化轉向、執政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地方官員績效考核體制的變化以及層級制帶來的圈層治理結構。雖然上述政治性變化促成了政府的回應性,保證了中國特色政治體制的彈性與活力,但也存在明顯的效用邊界。
關鍵詞:回應性;合法性;執政基礎;績效考核;圈層治理結構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7)12-0030-10
作者簡介:王軍洋,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胡潔人,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山東 濟南 250100)
西方政治理論認為,政府由公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選出的政府在選票的壓力下反過來回應公民需要,這是西方政府回應的理論前提。按此邏輯推演,非西方體制下的政府在理論上并沒有回應公民的動力,但這一廣受認可的觀點并沒有在中國政治運行中得到體現。一方面,黨政部門有強大意愿了解社會的真實狀況和公民的實際需求,為此特意建立了大量的政府領導的新聞與決策咨詢等內參系統主動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搜集民意①,這些機構利用自身的信息實效優勢,通過遍布全國的記者來了解實際狀況,匯編信息送達各級黨政決策部門參閱;同時,全國的各種研究機構也利用自身的人才與知識優勢,在各個領域撰寫專業研究報告,向黨政部門提供咨詢。另一方面,政府不僅有意愿搜集民意,同時也有著強大動力回應公民的各種需求。在當下中國,每年因為各種原因發生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政府部門在對超過90%的此類事件中都采取了容忍態度或者做出了讓步Yanqi Tong and Shaohua Lei, Soci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3-2010: Transitional Pains and Regime Legitimacy, Routledge, 2013.。不僅如此,政府部門在處置事件的過程中,往往會對失職官員進行懲罰,輕則黨紀或政紀處分,重則開除黨籍和公職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從1995年至2004年發布的八份《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通報》。。從2005年的定州征地事件到2013年的啟東環境事件,無不是在事件發生后政府部門第一時間介入處置,不僅按照抗議者訴求停建了涉事項目,還對其中涉嫌失職的官員做出了包括免職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嚴肅處分,其對民意的重視程度和回應的效率甚至超過西方政府唐文方:《政府為何會在民意面前讓步》,IPP評論,2016年7月8日。。那么,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下,究竟是何種原因讓中國政治體制對回應民意更為積極?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民意的回應是否存在差異,又存在哪些差異?本文通過回顧中國自建國后政權合法性的變遷,和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回應動力上差異的分析,嘗試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從意識形態到經濟績效:建國后合法性來源的變遷
在每一個國家,執政者都需要說明為什么是這個組織或個人而不是其他組織或個人掌握國家權力,以此證明執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每一個政權有效統治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只有當執政團體獲得人民的自愿擁護時,其統治才會具有效力,社會也才能保持穩定,而“缺乏合法性,任何系統都不能延續,至少不能延續很久”[美] 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合法性固然重要,但不同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卻有很大區別,傳統、宗教、意識形態或者民族主義以及韋伯式的“法理型權威”都可以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一個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變遷和政權改革等都會出現很大變化,或者在某一個特定時期,合法性的來源結構是多元的,相互之間相互補充。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之后,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方針,經濟上消滅私有制大力推動公有化,并將整個國民經濟納入國家統籌;政治上推動黨政組織全方位下沉,編織密集的單位組織網絡,將整個社會納入到國家范疇之中;思想上通過反復的群眾運動強化對共產主義的絕對信仰,結合以消滅剝削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義內容,使公民徹底內化為國家的一部分[美] 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下)》,金光耀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5頁。,在此基礎上,執政黨全方位建構了意識形態式的合法性。區別于法理合法性,意識形態合法性并非通過滿足公民需要并通過法定程序而實現,而是通過根據某種理想的政治圖景來塑造公民需求以使之適應現實政治需要而實現的王軍洋:《穩定的邏輯:社會狀態的政治區隔及其類型演化》,《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3期。。
但是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結構,將政權對公民的回應方式從理論回歸到了現實。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重新確立了自主經營的小農經營體系,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迅速解放;城市民營經濟的合法化推動了大規模的公民經商,全體民眾沉浸在發財致富的沖動之中。城鄉改革顛覆了既有的國家社會關系,國家開始從私人領域和市場領域撤退,社會空間得到重建,市場力量開始取代之前的國家組織體系來引導社會和公民行為。與此同時,隨著嚴格的社會組織體系的解體,附著其上的意識形態也陷入困境,社會上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信任度越來越低,一度出現“三信危機”徐非光:《就“毛澤東熱”對鄧力群同志的采訪和對話》,《中流》1991年第12期。,意識形態也越來越難以整合社會以生產合法性,國家亟需開拓新的合法性來源Feng Chen, “The Dilemma of Eudaemonic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Polity, Vol. 29, No. 3, 1997, pp. 421-439.。endprint
鑒于改革開放后公民需求從意識形態逐步轉向市場行為的現實,傳統的意識形態供給已難以滿足公民需要,執政黨不得不通過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有效供給市場性公共物品的方式來贏得公民的支持,以此開拓新的合法性來源。在此過程中,公民在合法性生產中的中心地位逐步顯現,這一點正是績效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合法性之間的基本區別。依據中央領導人的經典表述,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該表述再次強調了鄧小平的執政評價標準——一切以人民為準,也說明民心在合法性生成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王岐山在“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也直接談及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指出“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則需從實際情況(而非意識形態藍圖)出發,不斷滿足公民多元的、日益增長的利益需要,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構建新時期穩固的政權合法性。
二、擴大執政基礎與增強政府回應能力
改革開放后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變遷回答了執政黨為什么需要回應公民意見的問題,但是“公民”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群體,執政黨究竟需要對其中的哪一部分進行回應,以及在不同的時間段會有何變化也是一個需要關注的話題。中國共產黨在立黨之初曾明確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故而此時工人階級是主要的發展對象。之后鑒于工人階級規模偏小,農民階級數量龐大的現實,革命斗爭逐漸放棄城市路線轉入農村,此后農民群體漸成為革命主力。建國之后,中共主導制定的1954年憲法文本將國家性質定義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從該表述可見,雖然工人階級仍舊是國家的領導群體,但中共的執政基礎也正式涵蓋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而工商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都被排除在外。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在對“文革”撥亂反正的同時也啟動了執政基礎的調整過程,首先被“摘帽”的是知識分子。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作了新的概括,“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與歷史上的剝削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不同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在恢復名譽的同時,正式對知識分子開放入黨,這些做法極大地調動了知識分子投身建設事業的積極性,對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乃至政權穩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主要是解決了為改革開放貢獻智力的問題,但是發展生產力仍需要民營經濟的發展。
在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率先沖破農村民營經濟的禁錮,指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個體經濟開始得到認可。在隨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一定范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被認為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此后,隨著民營經濟的合法化,企業家的政治地位問題逐步進入政治討論的視野。2000年2月江澤民視察廣東時,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次年在建黨八十周年講話中,江澤民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社會階層,而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我們應該把……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該講話正式在入黨群體方面相應增加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由此,在意識形態中被定義為“剝削階級”的私營企業家,也可以“先進分子”身份入黨。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黨章做了修改,執政黨的性質也從“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過渡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相當程度上標志著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其主要任務也不再是帶領工人階級實現共產主義,而是協調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分化之后的階層、區域以及行業利益矛盾的問題。自此共產黨在理論上拉平了與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政治距離,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理論障礙被清除。此外,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催生了一大批新興階層的出現,如白領、高級職員、職業經理人等中產群體,對該群體的吸納也是中共調適合法性結構的一部分。
執政黨黨員結構的變化集中體現了執政基礎調整的歷史過程。建國之前由于政治軍事斗爭的需要,工人黨員始終處于較低比例,始終處于10.9%(1928年)以下,而此時的農民比例高達76.6%盧先福、趙云獻:《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史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這一情況在建國后得到迅速改觀。截止1953年,636.9萬名黨員中工礦企業工人從1950年的32萬余人增加到66.6萬余人,增幅達108%張天榮等:《黨的建設七十年(1921-1991)》,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改革開放之后,知識分子入黨數量穩步增加,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專業技術人員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到1981年10月止,全國835萬各類專業技術干部中,已有黨員185萬,占22.2%”《關于加強在中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工作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706/4495755.html,1982-09-26。。但私營企業主的入黨卻經歷了一個較長過程,九十年代雖然有私企人員入黨,但增長緩慢,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1997年為16.6%,新世紀后才獲得較大提升,2003年達到29.9%《調查顯示:中國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人數逐步增多》,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2-18/26/273940.html,2003-02-19。。隨著執政黨構成的變化,全國人大的構成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五屆人大中,工農代表占據47.33%,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分別占據14.96%、13.38%和14.38%史衛民、郭巍青、劉智:《中國選舉進展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422頁。。而在九屆、十屆人大代表中,知識界、企業界和其他社會精英獲得了很大的代表份額,而純粹意義上的工人農民比例則下降明顯,社會代表性更加多元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endprint
黨政代表結構的多元化吸納了更多的群體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來,當然也有助于吸收來自不同群體更為多元的意見,進而在多元意見的基礎上做出更為代表性的決策以回應更可能多的社會群體。在此過程中,執政黨本身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原先的“三個革命階級”過渡到了“兩個先鋒隊”,執政角色也逐步向利益協調者過渡,致力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民網,2017年10月18日。。
三、官員績效考核與地方政府行為
合法性與執政基礎的調整解釋了抽象意義上的政府回應性,但作為一個具體機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面對社會并處理各種具體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應對來自上級政府的監督壓力,工作內容要復雜許多,故而對地方政府回應性的解釋需要具體到機制層面。
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結構也發生著深刻變化,階層分化愈來愈深入,新社會階層愈來愈多,曾經被消滅了的貧富差距重新出現,各個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越來越明顯,改革逐步從沒有受損群體過渡到了分利競爭階段,道德失范、國有資產流失、犯罪和貧富差距等問題不斷涌現,各類群體性事件開始蔓延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愈演愈烈的群體性事件態勢促使黨政系統不斷完善維穩體系,為了避免形成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維穩工作的重點被放置在了基層。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認為,“大量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發生在基層”羅干:《政法機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擔負重大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求是》2007年第3期。,所以如何調動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就成為了政府回應的題中之義為此,中央政府甚至于2008年11月在中央黨校輪訓500余名縣委書記,主題是如何應對近年來在全國縣城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以維護基層社會穩定。參見《中央黨校縣委書記輪訓開始,維護穩定成培訓重點》,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8345885.html。。
然而在新世紀初期,中央政府也曾試圖以直接介入的方式來回應紛繁復雜的信訪及群體性事件。2003年,中央曾專門成立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牽頭的“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以此督辦交由中央與地方黨政相關部門來處理的案件。胡錦濤、溫家寶和曾慶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對做好信訪工作、減少重復來訪和集體來訪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批示,之后中央各個部門召開了各種專門會議應對此問題胡奎、姜抒:《2003年中國遭遇信訪洪峰 新領導人面臨非常考驗》,《瞭望東方周刊》2003年12月8日;《全國公安機關集中處理群眾信訪問題》,http://www.mps.gov.cn/n16/n8357/n1525334/n1525930/1527826.html。。一連串的政策在短時間內刺激了赴京上訪規模的迅速擴大Lianjiang Li, Mingxing Liu and Kevin J. OBrien, “Petitioning Beijing: The High Tide of 2003-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2012, pp. 313–334.,2003年下半年到國家信訪局上訪的群體比之于前一年同期增加了58%,2004年第一季度比前一年同期的赴京上訪人數增加了95%王永前:《破解群眾信訪八大熱點——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答本刊記者問》,《半月談(內部版)》2003年第11期。。但在此期間,赴省市政府上訪規模的年度增速僅僅是10%左右 于建嶸:《信訪制度動搖國家治理根基》,《改革內參》2004年第31期。。如此迅猛的信訪洪峰很快便超越了中央政府的回應能力,中央政府迅速調整策略,將回應各種類型群體性事件的職責下移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而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正是改革對地方政府的考核體系。
2005年國務院頒布《信訪條例》,第四條規定信訪工作應當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與疏導教育相結合的原則。為了推動地方政府主動化解基層矛盾,信訪條例要求各級政府建立健全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嚴格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本條例的規定,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并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同時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信訪工作績效納入公務員考核體系。此后,國家信訪部門開始每月一次的對各省(市、區)“非正常上訪”人次數進行排名,各省市信訪部門也會對各地市排名,直至縣市及鄉鎮政府。由于信訪案件多發于基層,縣市級及鄉鎮政府的信訪工作,隨即成為當地黨政干部政績考核的基本指標之一,隨后,各級黨政領導成為信訪責任人,其轄區內訪民進京上訪次數與黨政領導的升遷直接掛鉤。鑒于對政治晉升的重大影響,地方政府迅速轉變了過去對信訪的一定程度的消極態度,開始嚴肅對待信訪事務。
與信訪排名制度密切相關的是對地方穩定考核的“一票否決”制度,早在1992年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就發布了《關于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的規定(試行)》(綜治委[1992]1號),要求“對不安定因素或內部矛盾不及時化解,處置不力,以致發生集體上訪、非法游行、聚眾鬧事、停工、停產、停課等問題或造成嚴重后果,危害社會穩定的”情況所在的地方政府實行“一票否決”。為進一步操作“一票否決”制度,1993年底,中央綜治委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的若干規定》,明確要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同黨政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晉職晉級和獎懲直接掛鉤,將責任落實到人。對發生重大群體性事件的地方、單位及部門,由中央綜治委向重大問題發生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綜治委下達《重大問題領導責任查究通知書》,對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進行領導責任查究,收到《查究通知書》的單位在一定時間內取消評優資格,其主要領導也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中央綜治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組部、監察部、人事部:《關于對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穩定重大問題的地方實施領導責任查究的通知》(綜治委[2000]17號)。。為了推動領導干部積極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央組織部在2009年下發文件,將發生群體性事件列為對所在領導問責的情形之一,就此主要領導干部的政治前途與轄區社會穩定緊密聯系起來。至此,維穩工作日漸成為“一票否決”考核的主要領域“一票否決”目前主要集中在三個有限領域,排名第一的就是“社會穩定”,不僅使用頻率遠遠超過另外兩項(計劃生育與黨風紀律),且使用者的行政層級也更高,參見Freedom House, “The Politburos Predicament: Confronting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sion”, A Freedom House Special Report, January 2015。,但這一進程并未到此為止,2016年2月,中央頒布《健全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規定》,要求對沒有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安重點地區和突出公共安全、治安問題等”做出回應,或者已經(連續)發生重大群體性事件的地區的黨政領導“進行責任督導和追究”。九十年代以來,類似的強調維穩考核的中央專門文件至少已有8份之多,對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考核壓力其他的諸如1990年5月公安部《關于轉發黑龍江省委省府辦公廳關于在整治社會治安中貫徹“誰主管,誰負責”原則的意見的通知》;1992年1月中央綜治委《關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實行“屬地管理”原則的規定》(試行);2004年12月中組部《關于注意在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中考察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有關事項的通知》;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endprint
在中央政府嚴厲的責任考核下,地方政府開發和創新各種手段化解社會矛盾,預防群體性事件《新華社:用全民健身化解農村矛盾 效果超乎想象》,《聯合早報》2017年6月29日。。在每年發生大量群體性事件的情況下,政府每年成功化解的社會矛盾與糾紛也以百萬計,雖然這些方法未必都在法律框架之內,甚至還存在過度回應的問題,比如廣泛應用于基層工作的“花錢買穩定”(Buying Stability)做法《李靜君:中國政府“花錢買穩定”的邏輯》,http://cnpolitics.org/2014/10/chinas-rustbelt-and-sunbelt/;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2013, pp. 1475-1508。,動用公共資源為企業等社會主體制造的社會矛盾買單。在此過程中,若沒有及時發現問題,最終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直接責任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見表1),而在群體性事件的處理過程中能夠有效緩和平息事件的官員則能夠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多位重大事件“救火”官員獲晉升 官員維穩經歷被看重》,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13/18224931_0.shtml,2012-10-13。。從這些事件的對比中就可以看出維穩在對地方政府的考核中所占有的地位,也可以預見到地方官員對社會民眾的回應意愿。
四、維穩的制度依托:公共治理的圈層責任體系
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固然推動了地方政府的回應性,但地方政府本身也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體系,不同的層級在回應權限和責任承擔方面也存在差異。作為中央集權制國家,在中國,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各層級之間并沒有嚴格的權力分界。面對社會需求,首當其沖的是基層政府,尤其是權力單位比較完整的縣級政府徐勇:《接點政治:農村群體性事件的縣域分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之后根據事件的演進,主管政府層級會相應變化。簡單而言,規模越大,越有可能引起更高級別政府介入,甚至中央政府也會視情況作出批示(見表2)。有學者將這一層級化的政治結構稱之為“上下分治體系”,其核心要義在于治官權與治民權的分離曹正漢:《中國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及其穩定機制》,《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1期。。基層政府在具體“治民”措施上享有充分自主權,中央政府會通過“治官權”倒逼地方政府謹慎應對事件,較為常用的手段即是對應對失當的官員問責。2009年中央發布《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官員實施問責,這一點體現了中央對治官權的掌握。但實際上,地方政府責任體系并非二元的“上下分治”體系,而是上至中央下至鄉鎮的五級行政體系,不同層級之間“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三條,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18/c64387-28561177.html,2016-07-18。。不同行政級別擔負不同的責任,在具體操作中,依據事件規模和影響大小來確定追責的行政主體及邊界。如果事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追責主體就可能超越地方的范疇,直接由中央政府執行,而處置的對象則可能是地方的高層領導如2005年汕尾東洲事件中,由于警方開槍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傷,廣東省委也曾被責令向中央檢查,參見新華網《廣東省汕尾市紅海灣開發區發生嚴重違法事件》,2005年12月11日;《汕尾局勢有變 廣東向中央作檢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nwei-20060112.html, 2006-01-12。。其中除了處理某些地方官員以外,相伴隨的還有省市乃至中央與抗議群體的直接接觸,比如2004年的漢源事件中中央就曾派出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洋領隊的工作組介入《中央就漢源移民聚集事件四點指示》,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11/200411101705.shtml,2004-11-10。,烏坎事件、隴南事件與較早的仁壽事件中省級都曾派出大員領銜的工作組前赴事發地。但如果事件規模和影響較小的話,省級、市級甚至縣級都有可能成為追責的主體,而比他們更低級的政府成為追責對象。
既然治官權是對下級追責的基本手段,那就意味著每一個能夠成為追責主體的政府層級都擁有對下的治官權,而省級乃至中央派出工作組直接面對公民的做法說明上級事實上也掌握有直接針對社會的“治民權”孔飛力先生在對清代“叫魂案”研究中,曾將政府權力劃分為“常規性權力”和“專斷性權力”,前者主要是指依賴于政府科層結構的正式的與制度化的處置權力,而后者主要是清朝皇帝所具有的(時常使用的)繞過正常科層程序,直接向所關注的事務發布命令的權力。參見[美]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等譯,三聯書店2012年版。筆者以為這種分法對理解當下上下關系仍具有啟發意義。。所以,治官權與治民權并沒有分離,理論上講,五個層級都同時擁有對下級的治官權和對社會的治民權,只是在權力能量、使用頻率和使用場合上有所區別。所以,五級行政體系并非是一個簡單的上下分治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從上到下權能不斷遞減的“圈層治理結構”,不同的圈層根據在政治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在事件處置中發揮著不同的角色。
一方面,五級行政體系之間在治官權和治民權權能上存在差異。以警力動員為例,時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長的孟建柱曾指出,為防因用警不當、定位不準、處置不妥的情況,“要嚴格請示報告制度,凡調用警力參與重大非警務活動的,必須逐級上報、嚴格審批;情況特別緊急,不及時果斷采取措施難以有效控制事態時,要邊出警、邊處置、邊報告”孟建柱:《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 做黨的忠誠衛士和人民群眾的貼心人》,《求是》2008年第21期。。2008年孟連事件發生前,在孟連縣委縣政府請求下,3月普洱市政法委書記謝丕坤專程向省政法委匯報要求調動武警打擊孟連“農村黑惡勢力”,但沒有征得省政法委書記孟蘇鐵的同意。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再向省公安廳書面請示跨縣調動400警力到孟連,省政法委、公安廳再次否定該請求。然而,7月2日召開的普洱市委常委會依然決定跨縣調警打擊孟連“農村黑惡勢力”白靜潔、林霞、楊海冬:《云南孟連縣一起群體性突發事件后的“融冰模式”》,http://roll.sohu.com/20111020/n322848307.shtml。。2014年查處時任普洱市委副書記、市長,后升任云南副省長的沈培平時,此事被指“瞞著省里調動警力”王瑞鋒:《云南副省長沈培平被查 孟連事件瞞著省里調動警力》,人民網,2014年3月10日。根據2008年發布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調動警力100人以下的,由縣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調動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須報經地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調動300人以上的,須報經省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并報公安部備案;跨區域調動的,應當由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批準。武警的調動,則依從2008年中央辦公廳發布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部署和兵力調動使用批準權限規定》(中辦發[2008]21號),此未公布。。這說明,不同層級對警力尤其是武警的指揮權限差距非常大,自然在現場處置中擔負的責任也有很大差異。endprint
另一方面,五級行政體系在事件處置中的政治態度存在差異。一般而言,往往越是高層就越“親民”,越是基層則越傾向于強力解決問題,而在事后處理中,越是基層被處理的越為嚴肅,這一現象在孟連事件和漢源事件中都得到了集中體現。在兩起事件中,都出現了大規模警民沖突,并伴有平民傷亡,因此也都有多層級政府介入,但不同層級的介入方式和態度差異巨大,這一差異會深刻影響事件處置結果。根據相關研究數據,在有中央介入的事件中,成功率可達76.6%以上;反之,成功率只有23.8%左右Yongshun Cai,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10.。
在以權能和態度差異為主要特征的圈層責任體系中,責任轉移機制和利益讓渡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責任轉移機制要旨在于通過保持高層乃至中央政府的公眾形象來保持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其具體內容在于一方面高層秉承宏觀指導、親民導向和結果控制的原則,對地方應對抗議事件提出較為原則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斷強化對地方維穩的考核,要求地方從速平息事件。在高層的結果導向下,地方政府被賦予事件處置的充分自由裁量權,只要能夠從速平息事件,中央對于平息的手段并不會特別關注。但若處置無效導致事件擴大化,高層則會以失職或瀆職為由問責地方,而首先被問責的則是基層政府,尤其是縣鄉政府;如果事件影響超出一定的地域界限,問責對象的層級也會攀升。考慮到五級行政體系之間沒有明晰的權責劃分標準,致使掌握問責主動權的上級始終占據對事件性質與影響大小的鑒定權,出于自我保護的原因,必然傾向于將責任推向下級,進而促使下級尤其是基層政府對公民訴求更敏感。
其二是利益讓渡機制,該機制與責任轉移密切相關,當基層干部被處理后,上級乃至中央仍然需要面對如何處理事件的問題。因為高層更具有親民的意愿,所以在高層介入事件后,向抗議群體讓渡的利益一般也會增加。仍以漢源事件為例,在中央派出工作組后,地方政府迅速改進工作做法,除大幅提高補償金外,還保證把所有移民都安置到成都平原上的富裕地區,保證移民的新生活比現在好。在孟連事件發生后,省政府成立孟連縣橡膠產業利益調整工作指導小組,普洱市成立孟連縣橡膠產業利益調整工作領導小組,擬定橡膠產業利益調整方案,充分聽取廣大群眾的合理訴求,并切實維護好群眾的合法利益。類似的做法在滿足涉事公民利益需求的同時,以犧牲涉事政府威信為代價,維護和增進了公民對高層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支持程度,這實際上進一步拉大了央地之間的信任差,固化既有的“圈層治理體系”。在此基礎上,不同層級就更有(基于不同考量的)回應意愿與動力。
五、結語與討論
在政府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上,中央與地方具有不同的動機。過去三十余年中,隨著黨持續性地通過發展經濟來“滿足公民物質文化需要”以爭取公民信任,執政黨本身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為了穩固自身的執政地位,執政黨不斷地向知識分子、資本家階層開放入黨,將各個階層和群體中的精英人士吸納到體制中來,黨員結構越來越多元,涵蓋的階層與群體類型越來越多,代表性也越來越廣泛。這一點是中國特色政治體制同樣有強大動力回應社會需要的基本政治前提。與中央政府源自于合法性考量的回應性不同,地方的回應意愿更多地來自于上級的晉升和考核壓力。90年代后,地方考核指標日益多元化,社會穩定考核逐步獲得了“一票否決”的權能,其他民生、環境的指標,甚至民意調查也開始納入官員考量的范圍David Lampton, “How China is Ruled: Why its Getting Harder for Beijing to Gover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1, 2014, pp. 74-84.。在考核指揮棒的驅動下,地方也不得不努力按照中央要求的內容回應公民需要,尤其在化解社會矛盾預防群體性事件方面。公共治理所依賴的逐級加壓的圈層責任體系促使每一級政府都有解決問題和回應訴求的動力,同時,回應主體的層級分化為高層乃至中央在應對不同規模抗議事件中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緩沖,避免單一事件引發結構性的震動。責任轉移機制和利益讓渡機制比較有效地幫助中央能夠將抗議事件控制在一個有限的范圍之內,而不致引發區域性、行業性和群體性擴散,進而確保中國社會政治的穩定Yongshun Cai,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3, 2008, pp. 411-432;謝岳:《集體抗議與政治韌性的延展》,《當代中國研究》2014年第2期。。
但客觀上,并不應該高估基于合法性和績效考核而帶來的政府回應性的效力,尤其是該回應性之于社會政治穩定的意義畢竟在中國古代,具有層級差異的回應性也是存在的,參見韓承賢《文治之下的抗議:嘉慶四年蘇州士人的集體抗議與皇帝的反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3月;Jonathan K. Ocko, “Ill Take It All the Way to Beijing: Capital Appeals in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2, 1988, pp. 291-315。。核心的問題在于回應的原初內容并非是“客觀”的“民意”,而是政府對民意的感知,雖然兩者并不存在根本意義上的沖突,但在具體政策層面仍然存在不一致。基于此種意愿上的回應,最大的問題是可能存在選擇性回應問題,其一是在某些議題或者某些情況下的回應不足;其二則在另一些議題或者情況下的回應過度。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矛盾情況,是因為回應的議題設置權始終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讓政府感知到“民意”以后,才會觸發回應機制,否則即使是真正的、非常緊迫的問題也未必可以得到回應。如此一來,關鍵的問題就轉移到了如何制造可被政府感知的民意上,較為和緩的方法(如信訪)因為不能為政府感知到其緊迫性,觸發政府回應的效率并不高,而只有更為直接的如引發(尤其是國際)媒體的關注或游行示威等各類群體性事件等方式可以令政府更快更好地作出回應。但吊詭的是,正是這些制造民意的方法反過來又會被政府視為破壞穩定,進而需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平息。要平衡這一矛盾,合適的做法莫過于縮短原始民意與政府回應性之間的張力,比如在政策與政治活動中更多吸納公民參與,推動民眾自主和制度化地表達民意,而不僅僅是由科層組織來代理民意的征集。endprint
(責任編輯:瀟湘子)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order to win the election, government has to respond to, or at least balance peoples diversified demands. Although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dont have the 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lease their citizen, the Chinas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without essential election can also have strong motivation to respond to peoples demands efficiently, even at the cost of harsh punishment over its own officia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urces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context and attributes the reason of responsiveness to four changes of the system: secularization of party-states ideology,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foundation, local officials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nd the hierarchy system. These four changes have been contributed to the party responsiveness as well as its resilience, but they still have some obvious limitations in the efficient responsiveness.
Keywords: Responsiveness; Legitimacy; Ruling Partys Foundati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Hierarchical Responsibility Syste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