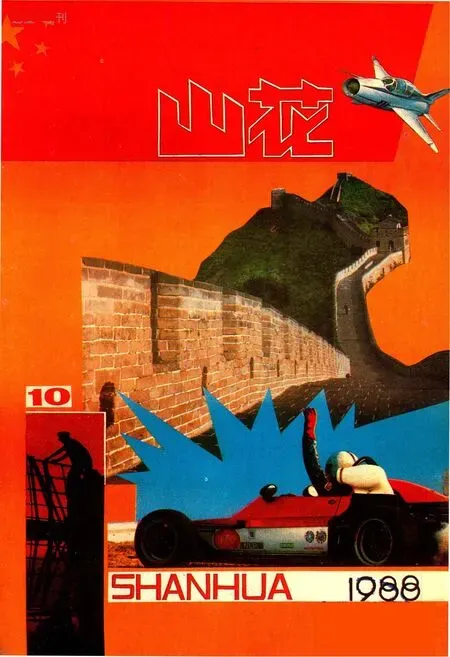流星 ???? ????
哥舒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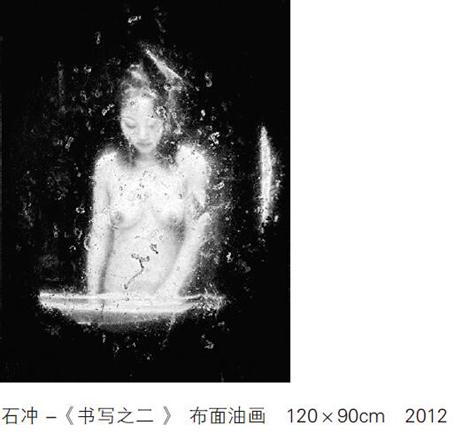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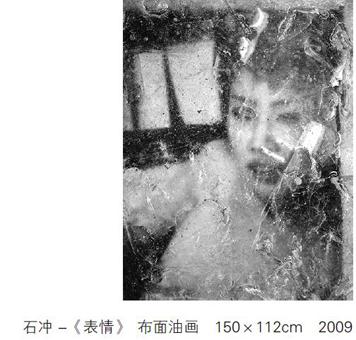
我背著行李走在淚街上,在車站看見了一位姑娘,好像在等去向別處的公共汽車。她不知道這個公交車站早已經廢棄了,再沒有任何公交線路通過這里。這個姑娘穿著裙子坐在欄桿上晃啊晃的,露出了苗條的腿,過了會兒她瞄向長街的另一端,瞧見了我,明顯猶豫了一下,然后問。
“你好,請問這里是哪里?”
“這里是淚街,以前這個站是淚街車站。”我說。
她轉過臉去看站牌,秀氣的脖子戴著一根銀色的項鏈,吊墜是一顆透明的星星。
“以前?”
“站牌早就沒有了。因為這個車站已經不存在了。”我說,“整條公交線路都取消了。你是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是不小心掉到這里來的。”她偏頭想了想,“你剛才說這里是淚街?哪個淚?”
“淚街。”我說,“眼淚的淚。”
“為什么叫這個名字?”
“因為整條街就像一條淚痕。大家都說淚街就好像是石城流下了眼淚。”
“石城?”
“這個地方叫石城,開采礦石的城市。”我耐心解釋。
她又眺望了一下街道,點了點頭,貌似理解了我的話。
“石城是嗎?”她頓了頓,小聲問,“那么,這里是地球嗎?”
我看了看她,她也在看我。對視了一會兒后,她臉紅了起來。我背起背包,往石城的城區走去。她跳下欄桿,跟在了我的后面。
“你是本地人嗎?”
“算是吧,我小時候住在這個城市。”我說。
“那你可以帶我看看這里嗎?”她說,“我剛來這邊,還不太熟悉……”
我覺得沒什么不可以,她大概只是個旅行者,故意來偏僻的已經荒廢的地方旅行。她的樣子挺好看的,好看得有點不合時宜,仿佛是臟亂背景里出現的花朵。我很擔心她會被這個城市吞沒,盡管石城已經廢棄了很久,我也剛回到這里。
我們沿著淚街往東走,走出街口基本就是石城的城中區了。不過就算站在城中區的中心街道往四面看,也看不到什么人影,這里盡管是石城的中心地帶,可是仍然看不出繁華的景象,一副城鄉接合部的樣子。灰撲撲的街道,到處是灰塵的地面,不超過五層樓的建筑,水泥墻都裂開了,露出了里面紅色的磚頭。貼了瓷磚的樓面,馬賽克都掉了,像被機槍掃過的槍眼。
“這里好像那些生命絕跡的行星。”旅行者姑娘說,“我在來的路上經過那些地方,我還以為這是座大城市呢,石城是吧?以前這地方也是這樣?”
“以前這里不是這樣,起碼我小時候不是這樣。”我說,“二十多年前,石城是北方一座還算熱鬧的小城市,荒廢是后來的事。你看見那個操場了嗎?這就是石城的中心廣場。”
我和她正好走到了中心廣場,操場現在也沒了當初的氣派模樣,只余留了空曠的形式。煤渣鋪就的環形跑道上雜草叢生,中間方形的足球場徹底變成了狗尾巴草的海洋,只有主席臺還保留了一絲威嚴。外圍的鐵欄桿已經拆得差不多了,我和姑娘隨便找了個缺口,走到了跑道上。她低頭,無聊地用鞋尖踢一塊大煤渣。她這樣讓我感覺怪親切的。小時候我也這么干,把白球鞋前面都踢臟了,家里人罵我費鞋,跟小混混沒兩樣。
“這里的跑道讓我想起了土星的光環。”她說,“不過這個操場是干什么的呢?做廣播體操用的?”
她居然也知道廣播體操。
“開運動會就用這里,不過用處最大的還是公審大會。一旦開公審大會,不但操場上,連圍欄外面都站滿了人,有的孩子還爬到樹上。看見那個主席臺了嗎,有點像天安門城樓吧?”
“沒見過天安門。”她搖了搖頭,“外太空最多能看見長城。”
“城樓下站著一排犯人,法官就站在主席臺,用高音喇叭宣讀犯人的罪行和審判結果。當然通常是死刑,槍決,立即執行。犯人們脖子上掛著涂了大紅叉的牌子,低垂著腦袋,從卡車上被武警押下來,然后又押上去。卡車開上人民東路,再開上人民西路,然后是人民南路和人民北路,繞市中心一圈以后,從淚街開出石城,在城外的礦場執行槍決。”
“判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年輕人,有的是小混混,有的是大混混,也有貪污犯和殺人犯什么的。有一個年輕的小混混,因為羨慕別人有自行車,就去學校里偷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結果當場被抓住了,很快被判了死刑。槍斃的子彈是需要花錢買的,五分錢一發,我記得好像是這個價格。”
她打了個寒顫。
“我不想聽這些。我感覺很不好。”
我還以為她想聽這些,旅游的人不都是想聽這些嗎?當地的風俗人情和歷史典故。不過我說的只是我的記憶。那個記憶中的石城,有很多人的,很多年輕人的,很多年輕小混混的地方。
“接下去,你想去哪里?”
“我有點走累了,”她說,“能找個地方坐一下么?”
但我也不知道哪里能休息一下,我好久沒回來了,這里現在都沒人了。中心廣場對面本來是石城中學,是這里最大的學校了,可是年輕人都離開了這個城市,所以學校里早就空無一人,校門向兩邊敞開著。門左邊是原來的文化宮。文化宮現在也不在了,只有底層開著小門面,上面寫著“超市”兩個字。走到跟前,發現這家店雖然號稱是超市,實際上也就是個雜貨鋪,什么都賣一點,從五金小件到火腿腸方便面,從洗發水到飲料酒水。店主也在,一個腦袋形狀怪異的老頭,在柜臺上擺弄一臺雜牌收音機,不時調一下頻道,電臺發出語焉不詳的人聲,忽然有個聲音亮了起來,玻璃柜面都震得嗡嗡作響。“第八套廣播體操現在開始,第一節,伸展運動……”
玻璃桌面上一層浮灰。我敲了敲桌子。
店主抬起頭,目光在老花鏡的鏡片后閃爍。他腦袋的右半邊癟了進去,像是一個摔變形的雞蛋。癟掉的半邊腦袋上沒有毛發,可能是因為這一點,他看起來又怪又老。姑娘往我身后躲了躲。
我和他的視線在空中某點對峙了一會兒。
“你要買啥?”他問。
“我要個打火機。”店主拿出一個紙盒子,從一堆五顏六色的廉價打火機里揀出來一個綠色的。我打了一下火,沒有質量問題,把一塊硬幣放在桌上。硬幣像煎餅一樣陷進一堆灰里。
“附近有沒有喝茶或者喝咖啡的地方?”我問。
癟腦袋店主用手掌把一塊錢和一堆灰都掃進了零錢盒,然后用手指了指街道斜對面。我和姑娘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看見了五個霓虹燈大字。
星吧客咖啡。
“那里以前不是個舞廳嗎?”我問,“現在是咖啡館了?”
店主再次抬起腦袋打量我,一邊晃動著收音機的天線。
“哦?你以前來過這里?”
我點點頭。這時收音機傳出了另一個頻道的聲音。
“昨天……獅子座流星雨掠過地球,有流星墜入大氣層……”
接著收音機里的聲音又變成了廣播體操。癟腦袋店主拍了拍收音機,舉起來貼在耳朵邊上搖晃。
我和姑娘走到咖啡館的霓虹燈下面,然后“星吧客咖啡”的“客”字閃了兩下,啪地冒出一股青煙,大概是報廢了。進到里面,我們才發現整個咖啡館也差不多到了報廢邊緣,所有的桌椅都搖搖欲墜,咖啡的看板很像是山村小學的破黑板。環顧四周凄慘的景象,就跟剛剛有兩幫小混混在這里打過架一樣。整個咖啡館唯一的優點是地方夠大,也就是說足夠容下更多的混混在這里打架。畢竟以前是舞廳。以前舞廳里真的經常有兩幫混混打架,為了姑娘或者為了面子,或許兩者都是一回事,跟公狗撒尿標識地盤差不多是一個道理。
我們在靠街的窗邊找到了還能坐的桌椅。過了兩分鐘,服務生終于意識到我們的存在,貓著腰踱到我們桌前。
“抱歉沒看見你們,今天沒什么客人,所以剛才一直在開小差,玩手機呢。”服務生是個發育不良的女孩,看起來只有十五歲,手里拿著一臺白色的愛瘋四,她麻利地套上帶著咖啡館標志的圍裙,“說吧,你們想喝啥,我們這里只有速溶咖啡。”
“……那還點什么?隨便上吧。”
“雀巢還是麥斯威爾?”她好心地問,“麥斯威爾口感更柔和,而且雀巢的快過保質期了……”
我和姑娘都紛紛點了麥斯威爾。服務生女孩又貓著腰回去了吧臺那里。
“我不是很愛喝咖啡,容易在飛行時睡不著覺。”姑娘說,“咖啡有股隕石坑的煙塵味。”
“小時候沒喝過,倒是經常喝中藥,”我說,“我是長大以后才習慣喝咖啡的,咖啡的苦感有點像是中藥,或者也可以說是回憶的一種。”
“你在這里長大的?”
“我出生在這里。”我說,“你呢?你從哪里來?”
她想了想,指了指天上,大概是說坐飛機來的。這時服務生女孩在吧臺那里用力敲桌子。
“咖啡好了,自己來端一下。”
我站起來走到吧臺那里,只有兩杯咖啡,也用不著托盤了。
“哦,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愿意端過去。”服務生女孩小聲說,“我端不動……我的腰壞了。”
“你的腰怎么了?”我問。
“很多年前砸斷的。……不然早就和大家一樣離開石城,去南方的大城市打工了。”
我看了一會兒她的臉,忽然想起來很多年前的事。
“平時生意怎么樣?”
“沒有什么生意,”她說,“這個城市沒幾個人留下來了,年紀輕的都出去了。我一天都賣不掉十杯咖啡。”
“那怎么辦?”
“晚上老年人會來這里包場跳交誼舞。白天做咖啡不為賺錢,就為了打發時間。可以認識陌生人,聊天什么的。”她說,“你女朋友挺漂亮的,一看就是大城市來的姑娘。”
“不是我女朋友,剛認識的。”我說,“我來端咖啡。”
我端著兩杯咖啡回了靠窗的座位。姑娘雙手托腮看著外面的大街。秋天,葉子落在水泥路面上,我想起打工后認識的一位姑娘的話,北方的秋天,就是竹掃帚掃去落葉的聲音。我是石城長大的,石城是北方的城市,所以我理解她的意思。
現在又是秋天了。
“葉子從樹梢上飄下來的樣子很好看。”姑娘說,“它們好像慢吞吞的老太太。”
我開始喝咖啡,捧著杯子看著外面的街道。她也學我的樣子。
“知道嗎,”我說,“這里以前是個舞廳。”
“跳舞的地方?”
“舞廳當然是跳舞的地方,不是游泳的地方。”我說,“白天基本上都關著,到了晚上七點才開門,然后全城的小年輕都匯聚到這個舞廳來了,大多數都是混混,也有我這樣的還在讀書的中學生,我記得門票很便宜,兩塊錢。”
“舞廳里有很多漂亮女孩?”
“沒注意,可能有一兩個。但我那時有個喜歡的女孩,是我的同學,她是個好女孩,從來不去這種地方。”
“你喜歡跳舞嗎?”
“我不喜歡跳舞。”我想了想,“而且也跳得很爛,那時大家都跳二步三步四步什么的,我一直沒學會,所以沒什么舞伴。就跟癟腦袋一樣。”
“癟腦袋?”
“一個經常被大家笑話的小混混,因為太笨了,可能智力上有點問題,大家叫他癟腦袋,個子又矮小,整個發育不良。所有人都拿他取樂。沒有女孩愿意當他舞伴。也沒有女孩和我跳舞。那些喜歡跳舞的女孩像逃避苦難一樣避開我。再說我也不是去跳舞的。”
“那你為什么要去舞廳?”
“可能是逃避孤獨吧。我在學校里讀書的時候,感覺很孤獨。”我說,“可是實際上在這種地方待著對減緩孤獨感沒有任何幫助。到了高三以后,我就不再來這里了。因為要準備復習高考了。”
“在孤獨這一點上我挺有發言權的,我好像孤獨地在宇宙呆了二十年。”她喝了口咖啡說,“偶爾會遇到超新星爆發,我遠遠地看著那煙花一樣的絢爛,然后繼續我的旅行。”
她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姑娘。我笑了笑。
“你為什么來到石城?”我說。
“我也不知道,這是我的旅行線路,可能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吧。是引力讓我掉到這里。”她蠻隨遇而安地莞爾一笑。
“這個地方早幾年就破落了。礦場也關掉了,以前倒是可以來碰運氣找找石頭什么的。”
“石頭,什么石頭?”
“鉆石。非常特別的鉆石。”我說,“很多年前這里的名字不叫石城,人們叫這里鉆石城。”
姑娘手捧著咖啡杯,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服務生女孩在吧臺里鼓搗了一陣,打開了音響。音箱里響起了模糊的歌聲。
“我有點明白自己為什么會來這里了。”姑娘說,“城外的礦場,就是以前的鉆石礦是嗎?”
“那是一個天然的大坑。誰也記不得這個大坑是什么時候出現的,直到人們在那里發現了鉆石。”我說,“他們說,那是一個隕石坑,很久前有一顆流星墜落到這里,因為高熱和高壓,流星就變成了鉆石。有個美國作家叫菲茨杰拉德的,就此寫過一篇小說。我讀書以后特意去找來看了,小說名字叫《像里茨飯店那樣大的鉆石》。真的就像一個酒店大廈那么巨大的鉆石,鉆石就在那個隕石坑里。據說這些鉆石非常罕見,打磨以后,里面好像可以看見星光。”
“可能是因為,它本來就是一顆星星。”姑娘輕輕說。
“但在我小時候,鉆石礦已經采光了。整個礦場都找不到幾粒鉆石了。那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鉆石枯竭了,礦場關掉了,整個城市也跟著破落下來,人們陸續下崗,年輕人沒有出路,混跡在游戲廳,錄像廳,桌球室和舞廳,城市治安一片混亂,每個人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但我那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我正在讀高中,心里有個喜歡的女孩。我用功讀書,每天來到學校,只是為了能看見她。那時我們就在對面的那個中學讀書。這是石城唯一的中學。”
服務生女孩在吧臺后大聲問我們要不要續杯。我端著兩個空掉的馬克杯過去。她倒熱水沖速溶咖啡,把包裝袋丟到吧臺下的垃圾桶里。
“我覺著那個姑娘有點喜歡你,”女孩貓腰低聲說,“只有喜歡一個人,你才會愿意聽他說故事。”
我謝過服務生女孩,接過兩杯咖啡,端了回去。
“繼續說你喜歡的女孩,”姑娘說,“她是你的初戀嗎?”
“是的,但僅限于暗戀。”我低頭喝了口咖啡,“表白信或許寫過,但沒有勇氣寄出去。這是個封閉的小城市,這種事情很難去想象后果,會把一切都搞糟的。我不知道她會怎么看待我,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對我有一點好感。對我來說,就算整座城市都變成鉆石,都不如她。”
“平時你們接觸得多嗎?”她喝了口咖啡,小聲問。
“我們隔得很遠,差不多是教室的兩端。她的座位在窗邊,我常常借看風景的機會看著她。她的學習成績很好,年級數一數二。家庭條件也比一般人好得多,她的父親是石城礦務局的局長。可是在班里她沒什么朋友,上學放學都是一個人。我們兩個人住在同一個方向,都會經過淚街。有時候會在路上遇到,然后默默地同行一段。每天她都在你剛才待著的那個車站等車。”
“她長的什么樣?”她問,“和我像嗎?”
“應該很好看吧,可是我有點記不得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要是沒有回到這里,我幾乎不再想起她來。”我說,“我覺得你們的樣子不太一樣。可是不知道為什么,見到你的時候,我還以為看見的是她。”
姑娘好脾氣地笑了一下,她笑起來像夜空的星星發出柔和明亮的光。我凝神聽了一會兒咖啡店里模糊的背景樂,是一首搖滾樂。
“我們的交集可能還有音樂。”我說,“后來我才知道,我們都喜歡搖滾樂。你喜歡音樂嗎?”
“我大部分的旅行是在寂靜里度過的。”她有些難過地說。“音樂方面我幾乎什么都不懂,但在一個人的時候,我經常哼唱給自己聽。”
“你能聽出這是哪首歌嗎?”
她聽了一會兒,搖了搖頭。
“后來呢?你和她怎么樣了?”
我聽了一會兒歌。
“死了。她很早就死了。在高考之前就死了。”我說,“我說過那是個混亂的年代。小混混們很容易就死掉了,有的是死在了別的小混混手里,有的是被捉起來,槍斃在廢棄的礦場。但我沒有想到像她這樣的女孩會死掉。我以為她會離開石城,那時她已經確定被保送到南方的大學了。”
“發生了什么?她怎么了?”
“那時整個石城都很混亂。在我們讀中學最后一年的時候,這種混亂到了頂點,出現了連環殺人案。被害者幾乎都是年輕的女孩,晚上一個人走在街上,被人從后面敲碎了腦袋。這就是惡名遠播的石城敲頭案。”
“為什么會有這種事?被害的女孩多嗎?”
“受害者一共是十三個女孩。”我說,“死了七個,有六個人重傷,變成植物人,或者癡呆,或者殘廢了。你看見咖啡館這個女孩嗎?我現在才想起來,她是其中一個,不過她很幸運,兇手失手砸斷了她的腰。從那以后她再也直不起腰了。”
姑娘轉頭望了望服務生女孩,女孩在吧臺里抬起腦袋。
“還需要什么嗎?續杯還是餅干?”
“不用了,謝謝你。”我說。
姑娘收回目光,低頭望著杯子。
“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凄慘的事發生的。”她說。
“是的,但是世界上偏偏就會發生這種凄慘的事。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好像更喜歡悲劇。”我說,“第一次謀殺就發生在舞廳門口,當時已經散場了,那個女孩從現在角度來說就是個不良少女吧,兇手敲碎了她的腦袋,把她拖進了一條死巷。第二天早上,上學的學生發現了尸體。去舞廳跳舞的大多認識這個女孩,因為幾乎都和她跳過舞。舞廳就此關門,再也沒有開張過。她是第一個受害者。”
“兇手為什么要殺她?”
“不知道,兇手也和她跳過舞吧,可能因此才會選擇她做第一個目標。”我說,“受害者都是女的,所以這些謀殺里很大程度上含有性的意味。那個罪犯是個很變態的家伙,下手很重,幾乎都是一擊必殺,敲碎頭骨。把受害人身上的錢和手表都拿走,但那些錢實在是微不足道,所以我覺得他根本不是為了錢。”
“為了什么?”
“只是心理扭曲了,想殺人而已。就像在一個又黑又深,又爬不出去的井里,他因為無聊,空虛,絕望,將井里的一切都毀壞掉,來獲得一絲滿足感。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測,也許根本就是有另外的原因,但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了。”
“他傷害了十三個女孩……”姑娘猶豫了一下,小聲問,“那你暗戀的那個女孩……”
“她是第十三個。有一天下晚自習,她一個人在淚街車站等車。兇手敲碎了她的后腦。她當時沒有死掉,在醫院昏迷了一個星期后才死的。”我說,“那天晚上我本來是想跟著她到車站。那段時間我一直都跟在她后面試圖保護她。但是我被留下來打掃衛生。只耽擱了幾分鐘,但一切都來不及了。這也是最后一起敲頭案,因為那天晚上兇手就被捉到了。”
“兇手是誰?”
“一個智力有點問題,看起來發育不良的小孩。所有人都拿他取樂,叫他癟腦袋。”我說,“被抓到的時候,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害怕,拿著一把鐵錘,對著周圍人齜著牙笑。”
“你認識他?”
我點點頭。
“這是個小城,大家在某種程度上幾乎都相互認識。算起來他和我念同一個小學的,算是小學同學吧。實際上他只有十五歲,還不到量刑年齡,但是他做的事太惡劣了,又可怕又惡心。據說他不但敲碎了那些女孩的腦袋,還對尸體做了過分的事。他被抓后,沒有一個人去看過他,連他父母都不認他了。審案的直接把他戶口上的年齡改成了十八歲,直接槍斃了事。于是一切就都結束了。”
“那個女孩, 你喜歡的那個女孩,真是很不幸。”她說。
“我覺得她的死亡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既是我青春期的結束,也是石城一個時代的結束。”我說,“很快我就去了南方的大學讀書,后來就沒有回來過。而石城的年輕人,也從那時開始,逃離了這個地方,尤其是年輕女孩。沒有了女孩,就沒有了希望。這個曾經出產鉆石的城市,已經死了。留下來的只有貧窮和絕望,沒有未來。我讀完了大學后,就留在了南方的城市。已經有十幾年時間,時間久得連我都忘了自己是哪里人了。”
“那你為什么現在又回來了?”
“我不知道,這十多年,我好像一直都在做夢一樣,在長久到無法醒來的夢境里,我一直想起過去,想起這座我早就離開的城市。我沒有覺得這里是我的故鄉,哪里都不是我故鄉。我只是在做夢時想起它,想起那個過去的時代,想起那個悄悄死掉的女孩。我休了個長假,不知不覺買了開往這里的火車票。也許我是想再到這里來看看,看看北方的秋天,看落葉飄滿街道,看看我曾經喜歡的女孩消失的地方。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脆弱,那么可憐,就像流星一樣一閃而逝。”
我低下頭,停了一會兒。
“人的生命就跟流星一樣,一閃而逝。不管你怎么追尋它的光芒,它最后都會消失在黑暗的星空。”
她“嗯”了一聲。
“流星的生命就跟人一樣,始終是孤獨的。我們跟隨著命運的腳步,來到不可知之地,迎接不可測的命運。”
我們沉默下來,聽咖啡館里不可靠的音響里播放的不可靠的歌曲。直到此刻我才聽出來這是什么歌。
我想知道流星能飛多久,它的美麗是否值得去尋求。
“流星……”我說。
“你叫我?”
“我是說這首歌的名字,你聽過這首歌嗎,原來是Coldplay的Yellow,但我更喜歡鄭鈞的這首,他把這首歌起名為《流星》。”
姑娘聽了一會兒,輕輕哼了起來。
“我很喜歡這首歌呢,就好像是為我寫的一樣,”她說,“我完全能夠理解這首歌,因為啊,我就是一顆流星。”
“你說什么?”
“我說,我就是一顆流星。”
我沉默了一會兒。
“你是在開玩笑嗎?”
“這是真的。我飛了很遠的距離才來到這里。在你和我說這些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來這里。直到聽完所有的故事,我才明白是為什么。”
“為什么?”
“這是我的命運。我會在這里遇見你。”她說,“世界上有很多的女孩,就和宇宙里有很多的流星一樣。”
我記得自己是在車站碰到她的。她的樣子有些迷茫,就好像一頭迷路的小鹿。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她都和這個小城市格格不入,石城無法容納這樣一個姑娘。這樣的姑娘只會待在一個小城男孩永遠的夢幻里。可是我已經不是什么容易做夢的孩子了。我早就離開了黑乎乎的街道,用外面世界的自來水洗干凈了臉和手。
“當然,這里沒有人知道我是一顆流星。從星光的等級上來說,我是中等亮度的,現在我剛成年,所以這次是我的成年旅行。”
“你多大了?”我問。
“換算成你們的時間,大概是二十歲吧,”她說,“你覺得我太小了嗎?”
“不,我覺得你正好。”我說,“你看起來就是二十歲。”
她笑了起來。
“可是……可是為什么大多數流星都成為了隕石,而你卻是個女孩?”
“因為她們都墜落了。就像城外那個隕石坑,也就是你們說的鉆石礦,那應該是我的同類,可是她消逝了。”她低聲說,“只有活著的星星才會是女孩。”
姑娘舉起胸前的吊墜給我看。
“你看,這是我的星光。”
她的星光比所有的鉆石加起來都要明亮。我看著她,她身上散發出璀璨的微光,猶如彩色的標本一樣浮現在黑白的背景里。咖啡館破舊得好像是百年前的建筑,說不定真有這么舊。很多年前我還是個男孩時,一個人站在舞廳里,激光燈在頭頂轉個不停,一束束光點像刀子一樣落在人們的身上。現在沒有激光燈了,可是我仍然感覺有點眩暈,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氣,閉了一會眼睛,好讓她的光芒在我腦海里褪去。她是那樣醒目,仿佛一顆星星墜入了藍色的大氣層那樣周身明亮。
“可以抽煙嗎?”
“當然可以,我不反感煙味的,因為聞起來很像是在大氣層燃燒的味道。”
我在身上摸索了一會兒,只找到了打火機。
“我要去對面買包煙,你能在這里等我一會兒?”
“好啊,等你回來,我要告訴你關于星星的一切。”
她垂下眼睛,低聲說了一句話。
“你在說什么?”
“在星星的語言里,這是一句祝福的話,”她說,“希望宇宙里所有墜落的星星,都能找到夜空的歸宿。”
我起身離開咖啡館,走到剛才買打火機的小賣部。小賣部的店主還在那里聽收音機。我要了包中南海,他彎腰從柜子里給我找煙。我一邊等著,一邊看著貨架上的小商品,看起來確實沒什么人買。貨架上一層灰。
“那個拿給我看看。”我指了指右邊的位置。
店主瞥了一眼,和煙一起拿了過來。
“這是工藝品,鍍銀的手工錘。”他說,“以前采鉆石用的,現在賣給游客做紀念品。”
我拿在手里掂了掂,錘子很小,銀光閃閃的,看起來挺精致的,不過也只能做紀念品,派不上什么用處。真的礦工錘比這個要大很多,也重很多。
“這個我也要了,”我說,“一共多少錢?”
“你為什么要買這個?”店主問。
“紀念品,買來送人。”
店主斜著眼看我,看了一分鐘。
“我想起來你是誰了。你是那個男孩。”他忽然說。
“什么那個男孩?”我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什么。”
“敲頭案,十幾年前石城有名的連環敲頭案。你是敲頭案最后那個受害者的同學,后來頂替她保送去了南方的大學。你就是那個男孩。我記得你。”
我抬起頭,靜靜地望著他形狀怪異的光腦袋。
“就算我是那個男孩,又怎么樣?”
“他們說,保送名額只有一個。你是全年級學習最好的人,但是那個女孩的爸爸是局長,如果沒有出事,她會被保送進大學。”
“你到底想說什么?”
“雖然那個變態槍斃以后,再也沒有人被敲頭了。可是大家都覺得,兇手仍然游蕩在石城的街道上。”
我繼續注視著店主的光腦袋。它奇怪的形狀讓我想起那個癟腦袋的小混混。我一直在想,究竟那個罪犯是因為腦袋是癟的才這么變態,還是因為是遺傳了癟腦袋和變態才變成了罪犯。不過歸根到底,他也是石城的孩子,就和我一樣。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我告訴你,我就是那個男孩。”
“我就知道。”店主嘀咕說。
“而且我確實保送去了南方的大學,這是當時能夠離開這個該死的地方的唯一的辦法。”我說,“我去了南方的大城市,先是讀書,然后留下來工作。這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回來過,一次都沒有想過。如果你想知道為什么,我告訴你。因為我一直很害怕。每一個晚上都很害怕。我害怕回到這個該死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覺得有人在跟著我,有把榔頭隨時會敲在我的腦袋上。我就和所有出生在石城的年輕人一樣絕望,最后我們都離開了這個噩夢般的故鄉,并且再也不愿回來。”
“但是現在你回來了。”他說,“也只有你回來了。”
“因為我不害怕了。我意識到這件事有多么荒謬。”我把那把工藝品小錘拿在手里,看著店主的眼睛。“我已經回來了。我已經不是個孩子了,我可以做任何我要做的事。如果有人要敲我的腦袋,如果有人想要敲碎我守護的東西,如果有人想從我這里奪走什么,我一定會用種種方式,反過來敲碎他的腦袋。不相信盡可以試試。”
癟腦袋店主和我對視了一會兒,垂下了眼睛。
“不管怎么樣,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們沒有必要為過去的事爭吵。”
他像垂死的老人那樣嘆了口氣。低下頭繼續給我找煙。
這時,玻璃柜臺上的收音機響了起來,信號不良的沙沙聲。
“俄羅斯……科學家在西伯利亞東……發現了剛墜落的……隕石……罕見的……價值數億美元……”
沉默。
“這是昨天夜里落下的幾顆流星里的一個。”店主說,把一包中南海擱在柜臺上。
“是么,那又怎么樣?”
“你知道她是一顆流星吧?”他的眼睛在鏡片后閃爍,“我是說那個和你一起的姑娘。”
“你在說什么?”
“世界上不可能有這么漂亮的女孩。我看見了她的吊墜。那塊吊墜里,有她的星光,和昨天夜里的流星一樣色彩的光芒。”店主說,“我就是靠這個認出來的。要知道,很多人都在找掉下來的流星,有很多想要改變命運的人,都想要找到昨天夜里那顆落下來的流星。也就是你身邊的這個姑娘。”
“你瘋了。”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們都瘋了。”
“所有石城人都是瘋子。只是原因不一樣。有的人是因為錢,有的人是因為變態,有的人是為了別的摸不著的東西。”他說,“你呢,你是哪種瘋子?”
我把錢扔在柜臺上,拿起那包中南海。店主收起錢,將一個核桃放在桌上,拿起另一把小錘。
“聽著,活著的流星是不值錢的,”店主壓低聲音,“只有隕石才值大價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甩起錘子。啪地敲碎了核桃,仿佛敲碎一個腦殼的聲音。
我把煙和工藝錘都放在口袋里,轉身往街對面走。
我向對面的咖啡館走去,秋天的落葉落在我的身邊,好像能夠聽見落葉被竹掃帚掃走的聲音。遠遠地就能看見坐在咖啡館窗邊的姑娘。我望著她,內心有一些憂傷。
越是走近咖啡館,那首歌就越是清晰。我想知道,流星能飛多久,幸福能有多久。我想起來許多個漆黑如噩夢般的夜晚,想起那些夜晚的流星。那些流星美得讓人心碎。在那些夜里,我像信仰神靈的古人一樣,對著星光許愿。我想起那些一去不復返的青春,那些一去不復返的小城男孩和那些一去不復返的夢。當夢醒的時候,我茫然地站在街道上,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這里,舞廳里已經沒有人在跳舞,只有音樂流淌在黑夜。我想起窗邊的身影,想起我跟隨在那個孤獨的女孩身后,她在車站上落寞地等待著仿佛永遠不回來的班車。她回過頭,仿佛看見我了,露出了微笑。
我看見了那個如同流星般的姑娘。她看見我回來,對我笑了起來。愿所有墜落的星星,都能找到夜空的歸宿。
我向她走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