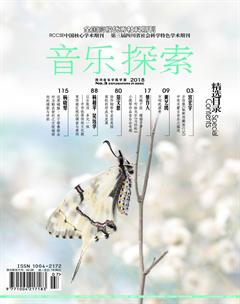古伯察《韃靼西藏旅行記》中有關蒙古音樂之描述
宮宏宇
摘 要: 法國遣使會士古伯察是“五口通商”后最早進入我國蒙古、西藏地區的西方人之一。其著述《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對當時清朝熱河、蒙古諸旗、鄂爾多斯、寧夏、甘肅、青海、西康地區的宗教信仰、歷史文化、民風習俗、自然狀況等記述在海外影響甚廣。以古伯察1850年首版的《韃靼西藏旅行記》為聚焦點,檢索古伯察對蒙古地區諸旗儀式及世俗音樂活動的描述。這些描述雖然不是民族音樂學意義上的有關蒙古音樂活動的專門研究,但卻提供了一個從世界看近代蒙古及其音樂文化的視角,不僅可彌補中文蒙古音樂研究史料之不足,亦可為學界了解域外對蒙古音樂文化的認知過程開啟一扇新的視窗。
關鍵詞: 古伯察;《韃靼西藏旅行記》;蒙古族音樂
中圖分類號: J609.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2172(2018)03 - 0003 - 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01
中國的蒙古地區,自元代時起就開始不斷有西人涉足,來此傳教、探險、調研的各類人員絡繹不絕,留下了大量的考察報告、游記、研究著述等文獻資料。這些早期進入蒙古地區的西人或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或通過道聽途說留下了大量有關蒙古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宗教禮儀、風土人情的通信、日記、考察報告及研究論著,西方社會也由此對蒙古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風土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
法國遣使會士古伯察(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及其1839年入華的上司約瑟夫·秦噶嗶(Joseph Gabet, 1808—1853)是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最早進入蒙古地區的西方人。與元代即涉足蒙古的其他西人不同,古伯察在進入蒙古地區之前已有過在中國內地和蒙古地區生活的經歷。1841年6月,他到達今河北省崇禮縣西灣子法國遣使會傳教區;1843年,到東北方向的蒙古地區黑水、別咧等傳教區傳教;1844年8月3日,與秦噶嗶在原青海三川縣的土族喇嘛桑達欽巴的陪同下從黑水川出發,沿途經過熱河、蒙古諸旗、鄂爾多斯、呼和浩特、寧夏、甘肅、青海等地,于1845年抵達青海西寧的塔爾寺;同年11月15日,他們從青海湖南經格爾木及玉樹州的曲麻萊和治多縣,再經唐古拉山口,經過18個月的旅行后,最終于1846年1月29日到達拉薩。 ① 在拉薩逗留近兩個月后,古伯察和秦噶嗶被清廷駐藏大臣琦善驅逐,于1846年6月初到達西康首府打箭爐(今四川康定)。后經現四川省、湖北省、江西省和廣東省,于1846年10月中旬結束了環繞中國多達14個省區的旅程回到澳門。古伯察在其后來出版的《韃靼西藏旅行記》 《中華帝國紀行》 《中國、韃靼和西藏的基督教》 {1} 等書中,對他沿途親歷的中國各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的土風民俗、宗教禮儀等記錄甚詳,其中包括該地區的游吟藝人及喇嘛驅魔治病時所用的音樂法器、喇嘛寺院的誦經儀式、新年上演的藏戲、兒童歌舞和他沿途聽到的各類少數民族音樂。
有關古伯察1843~1846年在蒙古地區諸旗、喀爾喀蒙古地區以及西藏腹地傳教旅行中對當時清王朝熱河、蒙古諸旗、鄂爾多斯、寧夏、甘肅、青海、西康地區的宗教信仰、歷史文化、民風習俗、山川地貌、開荒墾殖等的記述,國內史學界和民族學界已有學者專門論述 {2}。古伯察著述中有關“中國形象的塑造” “向西方介紹的中國” 以及漢藏關系的描述也有文化學者進行過專門研究 {3}。但國內外音樂學界對古伯察游記中有關蒙古族和藏族地區的游吟藝人及喇嘛驅魔治病時所用的音樂法器、喇嘛寺院的誦經儀式、新年上演的藏戲、兒童歌舞和他沿途聽到的各類少數民族音樂迄今為止卻鮮有提及。本文以1850年在巴黎首版的《韃靼西藏旅行記》(圖1)為聚焦點,檢索古伯察對1844~1846年親眼所見蒙古地區諸旗儀式及世俗音樂活動的描述。這些描述雖然不是民族音樂學意義上的有關蒙民音樂活動的專門研究,但卻提供了一個從歐洲看近代蒙古音樂文化的“他者”視角。不僅可彌補中文蒙古音樂研究文獻史料之不足,亦可為學界了解域外對蒙古音樂的認知過程開啟一扇窗戶。
蒙古包中慶祝中秋節盛宴后說唱藝人的演唱
1844年9月26日,古伯察和秦神父一行到達蒙古地區一個叫石板臺的地方,有幸目睹了蒙古人歡度中秋節晚宴后歡歌笑語的場景(雖然他也意識到漢人“八月十五殺韃子”背景故事,并表示了對蒙古人過這個節的不理解)。蒙古說唱藝人的表演技藝及蒙古民眾喜好說唱的傳統顯然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在書中生動地描述道:
……(晚餐后),一個男孩摘下掛在一只山羊角上的一個制作簡陋的三弦琴,并將它遞給了主人。后者又把它遞給一個面色靦腆、低著頭的年輕人,但一旦樂器在手時,年輕人的雙目霎時變得炯炯有神起來。主人對我說:“尊貴而神圣的遠游者,我請了一名說唱藝人(Toolholos),今晚讓他表演幾段為大家助興。”當老翁向我們講這番話時,演唱者已經開始調弄琴弦。接著,他很快就以宏亮和抑揚頓挫的嗓音演唱了起來。他有時也停下來并在唱奏間加入些充滿激情的活靈活現的道白。他演唱時,所有在場的韃靼人的臉都伸向這位游吟詩人,他們的面部表情隨著唱詞意義的轉變而不斷變化。說唱藝人選擇表演的節目與蒙古民族的傳統有關,聽眾聽興盎然。{1}
蒙古說唱藝人與韃靼英雄史詩《帖木兒頌》
《韃靼西藏旅行記》一書中也不乏對蒙古英雄史詩的記述。古伯察和秦神父由于“不太熟悉韃靼地區歷史……(因而)對于被蒙古藝人輪番推上舞臺的所有的這些陌生人物都不太感興趣”。 但他們因為已經有過在蒙古地區居住的經歷,所以對韃靼人喜歡唱誦的英雄史詩還是有所耳聞的,借蒙古人歡度中秋節晚宴的機會他們請求這位說唱藝人唱一首《帖木兒頌》給他們:“說唱家,你剛才演唱的歌好極了!但你還只字未提到不朽的瘸子帖木兒(Timour)。我們聽說《帖木兒頌》是一首著名的且深受蒙古人喜歡的歌。”“是的,是的!”許多人也異口同聲地回應到:“是的,請為我們唱一曲《帖木兒頌》吧!”說唱藝人沉默了一下后,從其記憶中思索了一下,以強健飽滿和富有征戰的口氣演唱了以下幾首頌歌 {2}:
當神一般的帖木兒住在我們帳篷中時,蒙古民族都是令人生畏和尚武之士。他的活動攪動了大地,一眼就可以使太陽照耀下的萬眾被驚呆。
啊!神一般的帖木兒,你偉大的靈魂是否很快就要轉生?
回來吧!回來吧!我們等待你。啊!帖木兒!
我們生活在自己遼闊的草原。這里平靜和美妙得如同羔羊。但我們的心在沸騰,它現在尚充滿著火一般的激情。對帖木兒榮耀時代的記憶一直縈繞我們。能成為我們的領路人并使我們成為武士的首領在哪里?
啊!神一般的帖木兒,你偉大的靈魂是否很快就要轉生?
回來吧!回來吧!我們等待你。啊!帖木兒!
青年蒙古人的臂膀如此有力,甚至能馴服野公種馬。他能在遙遠的地方的草上發現走失駱駝的蹤跡……啊!他再沒有力氣拉開先祖們的弓,其雙眼無法識破敵人的詭計。
啊!神一般的帖木兒,你偉大的靈魂是否很快就要轉生?
回來吧!回來吧!我們等待你。啊!帖木兒!
我們在神圣的山嶺上發現飄揚著喇嘛的紅袈裟,我們的希望已在自己的帳篷中開花。啊!喇嘛!請告訴我們這些事吧。當你要念經時,霍爾穆斯塔是否向你揭示來世的某種事?
啊!神一般的帖木兒,你偉大的靈魂是否很快就要轉生?
回來吧!回來吧!我們等待你。啊!帖木兒!
我們在神圣帖木兒腳下焚燒了香木,前額觸地,我們向他供奉綠色茶葉和我們畜群的奶制品……我們已準備就緒,蒙古人已站起來,啊!帖木兒!而你喇嘛,降福于我們的弓箭和長槍吧!
啊!神一般的帖木兒,你偉大的靈魂是否很快就要轉生?
回來吧!回來吧!我們等待你。啊!帖木兒! {1}
說唱藝人所唱的這首史詩中所歌頌的瘸子帖木兒(1336—1405)在14世紀時,曾征服了整個中亞,他建立的橫跨中亞帝國疆域從中國西北到高加索、土耳其東部、美索不達米亞等地,東南角遠至印度河流域。{2}
蒙古長調
蒙古說唱藝人演唱完史詩《帖木兒頌》之后,還有一個叫寧布(Nymbo)的蒙古人為古伯察和秦神父演唱蒙古長調,對此,古伯察也有以下細膩生動的描述:
韃靼說唱藝人(troubadour tartare)演唱完這首民族史詩(《帖木兒頌》)之后,起身向我們深鞠一躬,然后把他的樂器掛在一個木楔子上就出去了。老主人對我們解釋說:“我們的鄰居們也都在過節,他們也都等著聽他。不過,既然你們都很有興趣聽韃靼史詩,我們可以繼續聽一些其他的旋律。我們本家中有一兄弟,在他的腦子里也記有大量蒙古人喜歡的曲子。但他不會彈弦子,還說不上是一名說唱藝人。來啊,寧布兄弟!來給我們唱唱,并不是每天都有西方來的喇嘛聽你說唱。
一個蹲在角落的我們之前沒注意到的蒙古人立刻站了起來,占據了剛才那位說唱藝人的位置。此人的相貌實在是非同尋常,他的脖子完全龜縮在寬大的肩膀中,他那愚鈍和直視的大眼睛與其好像是被太陽曬黑的面龐形成了奇怪的對照,他披在腦后的頭發(更準確地說是沒有梳整的幾縷粗蓬鬃毛),顯現出他十足的粗獷不開化的野蠻人樣。 {3}
如果說古伯察對蒙古職業說唱藝人表演的史詩還存有敬意的話,他對寧布演唱的蒙古長調,正像他對寧布外貌的消極描述一樣,充滿了鄙視與不屑:“……寧布開始唱起來,但他的演唱是不折不扣的贗品,一種荒唐可笑的拙劣的模仿。”
古伯察雖然對寧布的演唱沒有好的印象,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寧布的表演技藝對蒙古牧民來說是很富有吸引力的:
寧布最大的本事是能夠長時間地憋一口氣,這使他有可能連續地唱出些復雜的華彩樂句(roulades),從而使任何有理性的聽眾聽得如癡如醉。我們很快就完全厭倦了他的大吵大叫,不耐心地期待小憩的時候借機回去休息。但這并非易事,這個鬼家伙可能已揣測到了我們的心思,故意不讓我們得逞。唱完一曲之后,緊接著唱另一曲,沒完沒了。沒辦法,我們只得一直忍受到深夜。最后,他終于停下來喝口茶。就在他一口氣將茶喝下去,清理了一下喉嚨準備重新開始時,我們趁機起身向主人獻上了一小塊鼻煙,向在座的人致意,之后便返回了自己的帳篷。{4}
古伯察對蒙古職業說唱藝人、他們在草原社會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在蒙古社會的位置似乎已有所了解。他提到:
在韃靼地區,你會經常遇到這樣的說唱藝人或四處流浪的游吟歌手,他們挨帳篷沿門行走,用歌聲唱誦其民族的人物和事件。他們一般都很窮,掛在腰帶上的一把三弦和一支笛子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產。但他們總是受到蒙古家庭的尊重和禮遇。他們往往在一個帳篷里一住就是幾天,當他們離開時,主人一定會送給他們一些旅行中的生活必須品,如奶酪、酒、茶葉等。這些說唱藝人使我們聯想到了希臘的吟游詩人和荷馬史詩的演唱藝人。他們在漢族地區的人數也不少,但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在藏區那么多。 {1}
蒙古牧民就醫時喇嘛的逐鬼驅邪儀式
除了娛樂的功能外,古伯察也注意到音樂在蒙古人生活中的實際功用,如他注意到就連“喇嘛們為治好病人而誦讀的經文有時也伴隨著凄涼和動人的儀軌”。在黑水川傳教時,古伯察就目睹過蒙古牧民就醫時,喇嘛為病人驅鬼的場景。他在 《韃靼西藏旅行記》 中提到喇嘛為病人驅鬼所舉辦的儀式時所用的樂器(法器)、唱念方式及整個驅魔程序:
驅鬼儀式于夜間11點鐘開始。喇嘛們圍繞著帳篷排成了一個半圓圈,手上拿著銅鑼、海螺、手鈴、鈴鼓及其它很吵鬧的韃靼樂器。其余的一半圓圈由病人的家人組成。他們都蹲著,一個緊挨一個。病人跪在(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墊著腳后跟蹲著)代表間歇熱鬼的草人的對面。主持的喇嘛醫生的面前放著一個盛滿小米和面團捏成的小塑像的面盆。燃燒著的牛糞冒著濃煙以一種神奇和搖曳的火光照耀著這一奇特的場面。
隨著發出的信號,喇嘛樂隊演奏了一首足以嚇退魔鬼撒旦本人的序曲。世俗人則拍著手有節奏地為嘈雜的樂器聲音和震耳欲聾的祈禱聲伴奏。這種兇神惡煞般的音樂結束后,大喇嘛打開了放在膝蓋上驅魔的經書。他一邊念經,一邊不時地從面盆中抓起一把小米,按照經書的規定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拋灑。大喇嘛念經的聲調有時悲傷壓抑,有時又高亢激揚。他有時會放棄那種韻律和節奏平穩的誦經方式,突然間大動肝火,對稻草人指手劃腳地大聲謾罵。驅魔儀式結束后,他將雙臂伸向左右二方發出信號,在場的喇嘛旋即以一種迅速而流利的語調誦讀經文,所有的樂器也都同時開奏。病人的家人也從帳篷中魚貫而出,像瘋子似的圍著帳篷瘋跑,一邊使勁用木棍敲打帳篷,一邊用能使普通人毛發聳然的嗓音高聲狂喊。在做完三次這種著魔似的儀式之后,這一行人迅速返回帳篷里,重新坐回到原來的位置。然后,所有在場的人都雙手掩面,大喇嘛則起身去點燃稻草人。火焰剛一升起,他便發出一聲巨吼,其余的喇嘛也隨即同聲重復。世俗人立刻起身奪走了被燒著的魔鬼,并將其攜往遠離帳篷的草原上。當間歇熱鬼在眾人的吶喊聲和詛咒聲中被焚毀時,仍跪在帳篷中的喇嘛們則以一種莊嚴和隆重的語調平靜地詠誦他們的祈禱經。
病人家庭成員從他們那英勇的狂奔中返回來了,祈禱的唱誦聲也由歡慶聲和歡呼聲取代。所有人很快就熙熙攘攘地跑到了蒙古包外面,每個人都手執一個點燃的火把,形成了一支游行隊伍,世俗人走在最前面,接著是由兩名家庭成員左右兩側攙扶著的那名患間歇熱的老人,最后是演奏著他們那讓夜間變得令人毛骨悚然音樂的九名喇嘛。 {2}
蒙古卓資喇嘛寺儀軌音樂
古伯察經過蒙古地區時,對當地喇嘛寺僧人的日常起居及祈禱儀式也有很細微的觀察。如在1844年9月,他經過當時“居住有2000名喇嘛”的卓資喇嘛寺(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卓資縣)時,就注意到:“每當誦經的時刻一到,一名負責把寺院的香客招到誦經處的喇嘛就會站在寺院的大門前,竭盡全力相繼朝四個主方向吹一個海螺號。這一法器的響聲可以傳得很遠,人在很遠的地方也可聽到。聽到海螺號后,每個喇嘛便會穿上法袍戴上法帽,前往寺院內的大院中集合。誦經時間一到,喇嘛會再吹一次海螺號,寺院大門也會打開,活佛進入佛堂……” {3}
與他對蒙古喇嘛為病人驅鬼的充滿鄙夷的描述不同,古伯察對蒙古喇嘛寺祈禱儀式上的喇嘛的唱誦似乎很有好感:“儀軌的主持搖動手鈴發出信號后,每個喇嘛都以低沉的聲調喃喃地先誦一段經,……。短時間的誦經之后,便是一陣深深的沉寂。接著再次搖鈴,莊嚴且富有旋律的二重合唱式誦經聲再次響起。藏文祈禱經文一般都采用詩節的形式,按格律韻律中規中矩地寫成,極其適合于和聲性誦讀。”但古伯察對喇嘛唱誦間歇時加入的器樂部分卻十分反感:“有時,在由經書確定的某些休止處,喇嘛樂師們會演奏一段與嚴肅端莊且富有旋律的誦經不大諧調的音樂。這段由鈴、鈸、鈴鼓、海螺、喇叭、嗩吶等樂器演奏的音樂,雜亂無章而且震耳欲聾,每名樂師都以一種癡狂的狀態演奏其樂器,相互間競爭,看誰發出的噪音最大。” {1}
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婚禮
古伯察對鄂爾多斯地區蒙古人的婚姻習俗及“韃靼人婚禮”儀式中的用樂情況也有記錄:
當新娘梳妝完畢時,便會被介紹給她的公爹,與此同時,聚集在場的喇嘛們也開始念誦由儀軌規定的祈禱經文。她首先向佛陀像行跪拜禮,接著拜灶神,最后拜新郎的父母和其他近親。而新郎則向齊聚在附近帳篷中的其妻娘家的人行同樣的禮。禮畢,便是婚宴,婚宴有時會持續七、八天。大量的肥肉,沒完沒了的煙和大壇大壇的酒使盛宴充滿了喜慶和榮華的氣氛。有時還要有音樂助興。婚宴上他們會請說唱藝人或韃靼吟游詩人,以使婚禮的節慶氣氛變得更加隆重。 {2}
結 語
法國遣使會士古伯察是目前所知最早在著述中詳細提到蒙古人音樂習俗的歐洲來華傳教士。作為史料,其著述中對1840年代清朝熱河、蒙古諸旗、鄂爾多斯、寧夏、甘肅、青海、西康地區宗教信仰、歷史文化、民風習俗、自然狀況等的記述尤為珍貴。盡管他有關蒙古音樂活動的描述不時透露出西方中心主義之偏見,但其考察之細微、敘述之詳盡,是在他之前,甚至之后其他西方各國來華西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即使是同時期國內漢族學者也無法相比。雖然他的這些描述絕非民族音樂學意義上的蒙古族人音樂活動的研究,但鑒于同時期漢文記載之稀少且欠缺實地調查,確實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民族志研究史料。在認知意義上,《韃靼西藏旅行記》亦可視為天主教士(“他者”)以蒙古為“田野”的民俗考察。它的出版為學界提供了一個從歐洲審視近代蒙古、西藏音樂文化的視角,不僅可彌補蒙文、中文相關文獻史料之不足,為學界了解域外對蒙古音樂的認知過程亦可有所啟示。
本篇責任編輯 錢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