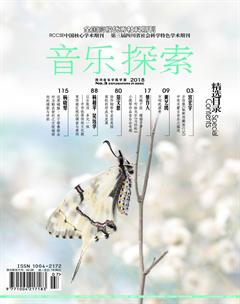非遺視野下鄂西原生民歌的傳承與呈現審思
任娟
摘 要: 鄂西地區擁有著文化底蘊深厚且風格獨特的民歌資源,千百年來,大量優秀的原生民歌作品在本地區保持著較好的傳承機制及呈現方式,并逐漸成為武陵山區地域文化與民眾集體精神的重要載體。從當下現實中來看,受到時代及大眾審美變化、商品經濟及業緣介入等因素影響的鄂西原生民歌在活態生存和流變發展的過程中,其傳承機制與呈現方式卻面臨一些問題,二者之間如何權衡好彼此關系、未來應當如何發展,還需要對此進行審視與反思。
關鍵詞: 鄂西原生民歌;非遺保護;傳承機制
中圖分類號: J6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2172(2018)03 - 0071 - 04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11
一、傳承機制與呈現方式
鄂西地區主要指圍繞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中心的武陵山區,匯集了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同時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交匯,形成了風格獨特、內容繁多、文化價值較高的原生民歌,并深刻地影響著地域文化與民眾集體精神。
鄂西原生民歌擁有著極為漫長的發展歷史,如《華陽國志·巴志》中有言,“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 {1} ,可見在商周時期本地的巴人(鄂西土家族的祖先)已經開始盛行歌舞活動。在《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關于“板楯蠻”(巴人的一支)的記載亦有言,“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俗喜歌舞”,從中可見在漢朝時這種歌舞文化已經在本地中延續了下來,又可由此窺見本地原生民歌的歷史傳承以及豐富的呈現方式。當然,這樣的傳承與呈現不只是為了實現其審美娛樂的基本價值,在諸多現實應用中,鄂西原生民歌還實現著許多社會功能,如《湖北通志·風俗篇》中也提到:“蠻俗好巫,喜淫祀,每淫祀必歌俚詞……板楯俗喜歌舞。夜幕澄寂,嘯歌群族,倫音俚態,幽怨委曲。” {2} 從中可見當地原生民歌在民俗祭祀等活動中仍多有活態應用與豐富呈現。清朝鄂西土家詩人彭施鐸有感于本地民眾日常的歌舞盛景,寫下《竹枝詞》“紅燈萬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亦歌亦舞、以歌引情;在恩施各地還流傳著“一天不唱歌,心里鬧豁豁” “幺哥一天唱不響,幺妹兒一年不開腔”等傳統民歌的樂句。這些都是對本地原生民歌在本時期盛行、活態傳承、多元呈現的最好表述。
鄂西地區原生民歌傳統的傳承機制和呈現方式雖來源繁雜、流變性較強,但相較之下,仍呈現出較為穩定的態勢。除了應用于宗教祭祀、歷史敘事等功能的部分原生民歌之外(如《擺手歌》 《卡切巴勞尺嘎》 《祈雨歌》 《坐喪子》等),大部分原生民歌并不完全囿于封閉的家傳、族傳式傳承機制,主要還是以“大眾參與式”的口傳心授、民間傳播為主。相對來講其傳承機制較為靈活多變,比如鄂西民間以傳承生產生活知識的諺語歌、以溝通親緣為目的的男女對歌、以承載重要歷史文化事件為主的敘事歌謠等等,相對保留了較為傳統的曲調和歌詞,也較好體現出地域審美的基本特征,其傳承機制相對來說維持較好。另一方面來說,鄂西地區原生民歌的藝術呈現方式也是形式多樣、異彩紛呈的。無論是來鳳縣和巴東縣集體狂歡、互動性強的“車車燈”,還是建始縣所流傳的、具有即興創作特征的“獅子贊詞”,從中均體現出了“表演中的創作”的活態傳承及多元呈現的基本特征 {1} 。相較之下,沒有承載過多社會功能限制的這些原生民歌反而基于活態的傳承與呈現,大量作品基本沒有脫離原生文化環境,且在當地民眾生活中得以活態應用。
質言之,鄂西原生民歌在活態與流變的態勢中,其傳承機制與呈現方式在傳統的文化環境里能夠保留相對較為穩定的狀態,難能可貴;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傳統的現實文化環境被改變的時候,傳承機制和呈現方式不可避免會受到沖擊,本身傳承機制就多元、脆弱的它們是否在將其活態性維持下去的同時能夠保持其原真性,不可否認的是,這其中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困難。
二、傳承困阻與呈現異變
事實上,從傳統社會結構到當下社會結構的改變中,鄂西地區的原生民歌的傳承機制與呈現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原生民歌逐漸開始脫離了其原有的文化環境,外來因素的介入所帶來的沖擊使得它們很難以傳統的方式維持其活態性和原真性的傳承、呈現,甚至對原生民歌造成了一些破壞,使之呈現出現了異變。
當下鄂西原生民歌所面臨的傳承困阻主要源于社會環境的變化,因為“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如伴隨社會變遷出現)會引起音樂口味、音樂類型的劃分以及音樂本身的改變” {2} ,這主要通過幾個現實方面體現:原生民歌所涵有的應用功能被弱化,逐漸上升為用于“娛人”的單純藝術作品,在宗教祭祀、民間信仰、生產勞作等日趨減少的相關活動中失去了用武之地;原有傳承機制本來就缺少親緣、地緣等相關的約束,源流繁雜的傳承實則使其顯得過于開放、脆弱,在整個傳承和呈顯中很容易產生過度流變的情況;傳承人很難將原生民歌作為謀生的方式,但如果一味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又很容易破壞到其原有品質,如此悖論最終只能使傳承行為后繼無人;傳統審美與時代審美之間產生了脫節,包括當地民眾在內的大眾可以通過新媒體接觸到西方音樂、流行音樂等更多的鑒賞選擇,傳統質樸的原生民歌并非他們首要選擇;研究、推廣和普及不夠,除了《龍船調》 《六口茶》 《黃四姐》等幾首較早挖掘并推廣的民歌之外,更多數優秀的原生民歌卻因為知名度不夠、傳承無序、無人問津等原因正面臨著消失散佚的危險;業緣的介入和沖擊使得鄂西民歌成為一種純粹的“藝術商品”,其中經濟價值侵蝕了原有的文化價值,使得很難維持這些民歌的活態傳承機制;缺少有效的資金用于扶持與保護,注重的是開發和“創新”;傳承人自身對于非遺保護知識及意識的缺乏等。多種原因造成了當下鄂西地區原生民歌傳承機制的諸多困阻。
在這個過程中,呈現方式的變化也會直接影響到原生民歌傳承機制的完整性,尤其是藝術呈現的異變直接影響到了傳承機制本身,對其造成較大困阻。傳統的呈現方式有很多,比如在宗教祭祀和白事中所唱的靈歌(“撒爾嗬”系列歌曲等)、田間勞作中所唱的勞動歌(薅草歌等)、男女之間的情歌對唱(《六口茶》等),可以說在鄂西地區的很多地方原生民歌可謂是“隨處可聞”“無歌不歡”,但目前來看,除了在深山和部分鄉村里還能聽到原汁原味的原生民歌外,可能也只有在電視和網絡上偶爾能夠對其有所了解了。另一方面來看,傳統原生民歌的呈現更多是為了實現一定社會功能、發揮實際作用,但目前這些民歌所發揮的作用更多是從“內向型娛己”轉為“外向型娛他”,逐漸呈現出舞臺化的傾向——為了適應舞臺需求,表演者會對傳統的演唱方式、歌詞、曲調、伴奏等進行一定改變,亦或是成為旅游市場里較為固化的程式化表演,原生性和活態性都得不到任何保證。《文化創意和非遺保護》書中提出了相應的憂思:“以原生態民歌為例,原生態藝術被藝術家們從大山從鄉村里發掘并搬上舞臺對原生態藝術有重要作用……當鄉民把自己的藝術傳播出去的同時,他們的藝術也得到了更多的保護勢力。” {1} 從現實情況可以窺見,有很多當地原生民歌的傳承者“他們更多的是會在傳媒中生活,尋找明星的感覺,同時在商業利潤的追逐下,他們也很難保證原生態不商業化,不因此受到其他利益的誘惑而改變過去的形式” {2} ,沒有對傳統技藝進行很好的傳承與鉆研,藝術呈現也失去了原有價值,令人扼腕。此外,院校派的演唱技法過多介入原生民歌的情況也多有出現,一方面這是對其研究與呈現的突破及探索,但若以此為標榜、過多介入,必然會影響到其原真性。
需要注意的是,鄂西地區原生民歌的傳承與呈現并非只是保護某個人或者某類歌曲,更重要的是保留與之相配的樂器、樂隊、舞蹈、歌俗等,盡管所涵面過廣、其難度非常,但面對著當前的困境,對于鄂西原生民歌日后的傳承與保護采取怎樣的措施去解決當下的困難才是當務之急。
三、活態傳承與呈現適度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中經常提及的兩個詞:“原汁原味”和“活態”。這兩個詞在鄂西原生民歌在日后傳承保護與呈現過程中可以作為其重要指引,亦是其重要的參考及審思準則。其中,要尤為注重權衡好“活態傳承”與“適度呈現”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需要以傳承和保護為主,但也要及時發現、利用、發揮其中的潛在價值,在對其進行合理經營或藝術提煉等行為時要盡量運用較為適宜的方式,大致可參考“異人、異地、異品”三原則 {3} ,即非遺的傳承、保護和開發需要由不同的人、群體來承擔,分而治之、齊頭并進、互不干涉,在保證這些原生民歌的原生性之同時,還可為其作更多研究、創作、推廣、開發,共同在當地營造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活態、整體文化環境,使非遺的傳承與呈現之間的關系得以平衡、減少矛盾、共同發展。
具體而言,關于鄂西地區原生民歌活態傳承和適度呈現應當主要關注其中的傳承人、政策及資金、文化環境等多個方面,而非只是關注到其中一個部分。在這其中,鄂西地區當地政府部門需要為這些原生民歌提供較好的扶持和資助,同時保護好其原生文化環境,協助那些傳承人健全自身的傳承機制,同時避免他們受到來自外界的沖擊,以保證其“原生”的重要,當前湖北省與恩施州各級政府已經開始著手于此事,致力于梳理出一個因地制宜的非遺傳承思路;作為傳承人本身,應當盡量不參與商業經營或藝術創新行為,以保存和保留自身手藝(演唱、創作、表演等)和作品的原生性等;此外,學界和藝術界可在不干涉、不影響原生文化傳承的同時進行大量田野工作,搜集整理出一批民歌作品,一部分可交由傳承人研習,自己也可由此進行理論探究、藝術創作、舞臺呈現,使其發揮更大現實價值(“原型的置換變形不是簡單的故事的變化、累加、改造,而是賦予了不同時代人的精神意識、情感變化和審美趨勢” {1} ,對傳統原生民歌的藝術加工及提煉亦是如此),目前已經有中南民族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湖北民族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等多個高校及研究機構開始對此開展了相關學術研究及藝術創作活動,取得了較多成果;文旅部門和商業企業的介入要更為慎重,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鄂西原生民歌的傳承“造血”,為其提供活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藝術呈現上為其提供更為廣闊的舞臺、使其傳播獲得更多渠道,目前在恩施市土司城、女兒城已經成立了民歌表演隊,在恩施大峽谷、利川騰龍洞、建始野三峽(野三河)等重要景區也有大量原生民歌的表演,盡管會因為適應市場和大眾審美而對其進行了一定改編,但相對而言并未完全影響到傳承人本身,總體上為整個傳承行為與藝術呈現提供了發展的經濟基礎與市場保證;還可以借助當前高度發展的信息技術,使用影像影音系統、VR交互及文化體驗、移動端宣傳及藝術品鑒等對鄂西原生民歌進行記錄、傳播,真正讓這些民歌(尤其是處于瀕危狀態的民歌)得以保存、推廣,也讓更多人從中感受到其中所蘊含的藝術魅力。
結 語
鄂西原生民歌的傳承與呈現未來將會走向何方,又當如何面對多項機遇與挑戰,需要對此進行更多關注。“……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同時要挖掘文化遺產的文化深度,提高參與者自身的修養……我們應該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性是在特定的環境中生長的,外界環境必然帶來保護對象的變化,但抓住文化遺產中寶貴的精神財富和魂魄,才能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精髓不在保護中流失。” {2} 由此需要提出的是,鄂西地區原生民歌的傳承與呈現要想獲得更為長遠、可持續的傳承、保護與運營,更為重要的是要讓所有人建立其對鄂西地區原生民歌的非遺意識,通過喚醒全民情感來實現文化自覺,最終以文化自信完成整體非遺文化保護的邏輯旨歸。
本篇責任編輯 李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