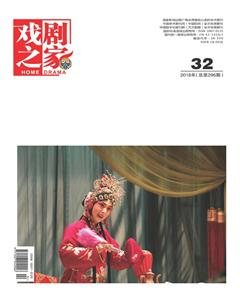從后現代回憶敘事角度分析《記住我這件事》
史旭燕 敬南菲
【摘 要】索爾貝婁作為二十世紀美國最杰出的猶太作家之一,他的小說更是以人道主義思想給人以深刻的教誨及啟迪。《記住我這件事》是貝婁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講述了一位行將遲暮的老人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候不平常的一天,并對此有了自己全新的看法和見解。本文試從后現代語境下的回憶敘事視角下對小說進行分析。回憶既可以作為一種敘事手法,也是塑造人物,抒發情感,檢驗自身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回憶敘事;索爾貝婁;《記住我這件事》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32-0199-03
一、對回憶敘事手法的介紹
關于回憶敘事的概念是這樣的:作品在內容上傾心于對過往人生場景的體驗和展示;作者的時間視角是追憶和回顧;而作者的意識趨向則是現在與未來。回憶作為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和體驗情感的方式,然而當它運用于文學作品中則超越了單純的意義。它既是一種敘事方式也是一種藝術主題,并具有審美的意味。本文所理解的回憶敘事不再是傳統敘事學意義上所指的敘事手段,而是以回憶為主線而展開故事,是作為既包括內容層面也涵蓋了敘事策略的作品整體。在對后現代敘事理論有一定理解的基礎上對該論文所指的“回憶敘事”理解為:“回憶”是貝婁小說在內容和敘事兩方面呈現出的重要特點,作者以“回憶”為敘事特點講述故事,從而向讀者傳達知識、情感、價值和信仰。
另外,回憶與記憶是一對既有區別又關系密切的兩個概念,沒有記憶也就不會有回憶,不會有人類歷史。記憶是人類特有的心理機制和儲存信息的能力,回憶則是一種方式,是一種提取記憶信息的方式,一種人類借以思考和回顧的方式。回憶是對記憶對象的一種有意識地選擇提取。選擇什么記憶來回憶體現了一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該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回憶是主人公用來表達自己的主要方式,也是作者一種獨特的敘事手段和時間模式。借助對過去的沉思,使現實與過去得以勾連在一起,回憶不僅僅是一種文本的選擇,也是作者對生活的一種選擇,或者說是以內化為作家審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種獨特的方式。
二、回憶敘事的“回憶性人物”
(一)強大的記憶力。一個喜歡回憶的人必然是對過往有著深刻的記憶。可以說,沒有記憶也就不會有回憶。在該小說中,主人公路易盡管是一位處于遲暮之年,即將離世的老人,但他擁有著非常強大的記憶力,他可以清楚地回憶起年輕時候那個隱藏著暗流的具體日子,并且能夠清晰地回憶起那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當時的環境,碰到的事情,遇到的人以及他的所思所想。他用自己超強的記憶力來回憶往昔并沉迷于對過往的回憶和思索中。同時他也表達了自己的心聲,他并不想清楚地記得那個不平凡日子的具體時間。在小說的一開始,路易就表明說:“那是二月份,我已說過,具體日子對你來說并不重要。不瞞你說,我自己并不愿意把日子弄準確。”可以看出主人公對于自己的過往仍然不能完全釋懷,所以他并不想清楚地記得具體日子。
(二)回憶中的歷史。每段回憶都代表著一段歷史。主人公對于自己個人生活的回憶,所代表著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生活的回顧,而是代表著從個人生活的回憶所引發的對于人類歷史的記憶。路易用自己超強的記憶力回憶起那段令人壓抑沮喪的日子。那段日子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那時候的美國極其混亂。人們人人自危,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對未來失去了希望。小說中對于經濟大蕭條就提到過很多次。就在故事的一開始公園里發生的打鳥人的暴力行為就表明了經濟大蕭條時候的混亂場景;路易上了電車之后,看到車上的人們說話又警覺又可憐,說明經濟大蕭條帶給了人們很大的陰影;之后當妓女問起路易他未來想選擇的職業時,路易表明了自己對經濟大蕭條絕望的心聲,他說:“職業對我沒用,一點用處也沒有。在慈善機構門口排隊討湯喝的窮人也找得到會計師或工程師。在這世界性蕭條的年底,職業一無是處。”主人公第三次回憶經濟大蕭條的場景是當他穿著女人的衣服尋求藥店老板的幫助時,藥店老板明明是知道路易身份的,但是那段時間正值經濟大蕭條他的日子也并不好過,所以他索性假裝不知道,文中路易說:“在這生意難做的年代里,他卻能把什么都抓得很緊,我想他一定很得意。”之后,當路易來到了酒吧,經濟大蕭條仍然纏繞著人們。酒吧老板對于路易的著裝感到非常驚訝,他說:“經濟蕭條也有它的好處,要不然,你永遠不會知道出了什么新鮮事。”雖然這么一句半開玩笑式的話,其實含有諷刺的成分,它隱含著酒吧老板對生活的無奈以及對經濟大蕭條的失望。
經濟大蕭條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精神上的空虛,因此路易道:“我乘電車在這城市轉來轉去,并不是為了掙錢或者為了幫助家庭,而是為了讀一讀這座令人厭煩的、沮喪而丑陋的、無邊無際的、正在腐爛的城市。那時候我不可能想到這點,但現在我明白當時我的目的是去理解這座城市。”在這個虛無的世界里,路易一心想要成為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他這么做也是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
回憶中的猶太身份。對于自我的記憶離不開歷史的記憶,同樣也離不開其自身所具有的身份。身份記憶是集體無意識的產物,民族身份是無法拋棄的,身份記憶同樣也是無法抹去的。作為猶太人,他們的身份在世界民族中注定是特殊的。主人公路易在年輕的時候對于性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而這在傳統的猶太人的觀念里是非常忌諱的。小說一開始就提到“現在的人可不對小孩談什么死亡啊,旋渦啊。而我小時候,父母卻不忌諱談論死亡和臨時的情形。他們很少提及的是性,現代人則剛好相反”。此外,路易還非常喜歡說謊,而說謊對于猶太人來說是非常不道德的行為,這與他們的猶太傳統是截然相反的,而路易則稱:“既然我的行為是無辜的,那何必為自己解釋呢?或許是因為我總在胡思亂想些不正經的事,要么因為我總是被人說這不對那不對,要么因為我常說謊話—我曾經非常熱衷于反省自己,但現在有些討厭它了。”
路易坦言自己是“一個心高氣傲的猶太學生,神氣活現不愿遵守正統教規,卻一心只想將來有一個特殊的命運”。完成了送花的差事他本可以馬上回家,他卻不想馬上回家而是試著改變自己的現狀像其他非猶太人那樣尋找不一樣的自我去滿足自己的性欲。象征他猶太身份的衣服被搶,代表著猶太身份的喪失,但是在最后他回到了家里并忍受父親的懲罰,證明了他猶太身份的回歸。路易希望能夠像其他人一樣真正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確定穩固的身份,也就是所謂的美國身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美國身份最好的辦法就是過得跟美國人一樣。但是,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所生活的環境、人際圈、生活方式、民族特征等等卻無法從他身上真正的抹去。
另外,猶太人再怎么改變也無法改變非猶太人對他們的態度,路易送酒鬼回家,酒吧老板把酒鬼身上所有的錢都拿了出來以防錢被路易盜走,雖然口口聲聲說并不是擔心路易拿錢,只是為了對顧客負責,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酒吧老板對于路易深深地不信任,這與整個猶太民族在美國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
路易生活的地方是一個典型的猶太人聚集地,而他的家庭更是一個典型的猶太式家庭。路易的父親是一個猶太商人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在家里也非常強勢,盡管如此,父親對子女卻充滿濃濃的關心和愛“如果孩子們回來遲,他會一直等著,在長長的公寓房間里來回踱步——不,是小步疾走”。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對傳統猶太教非常虔誠的婦女。他的父母都具有典型的猶太家長形象。在故事中,路易的父親再三要求路易下課之后必須要找個活干,這體現了傳統的猶太家長思想。盡管父親對兒女們有時候很殘酷,但是他們還是會無條件的聽從父親的教誨,就如路易所說:“我們從沒覺得父親殘酷。我們出了格,理應受罰。”
路易生活圈子非常小,在小說的一開始他就介紹了自己當時的情況“當時我正在讀高中最后一年,對周圍一切不感興趣,并不引人注目,也不合群。我只有在作為一名跳高運動員時才有機會在公眾場合露臉”,“我無心學習,卻有書呆子氣。對家庭生活守口如瓶。事實上我不想談起母親。此外,對自己古里古怪的興趣,也不知道怎樣用語言表達”。我們可以看出路易當時的生存狀況是被社會孤立的,就如猶太民族本身一樣,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其他民族所孤立。
路易平時除了看書沒有什么其他愛好,他帶著調侃的語氣稱自己無心學習卻有一股子書呆子氣,他將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用于買書“我把所有能搞到的錢都投入了哈默斯馬克書店”。他對各種類型的書都有所涉獵,大到晦澀難懂的書及政治小冊子,小到禁書。他對于文字有著非常執著的精神,他一旦看書就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在電車上讀書,一讀書,就不去留意外面的風景了”。“一本殘缺的書:封面丟了,書頁靠線和漿糊連在一起”卻被路易視為珍寶。因為擔心書會找不到,他把書一直放在了自己貼身口袋里。當妓女把他的書弄丟以后,他一心想把那本舊書找回來,就算經歷了如此不平常的一天,他想著的第一件事還是找回那幾頁書。在故事中,路易道:“你或許認為我是過分偏執,有一種對文字,對印刷物的瘋狂依賴。但是記住,當時街上沒有滌罪著沒有向導,沒有聽懺悔的神父,沒有教友,也沒有能給你安慰或指引的人。”路易的衣服,錢和書全被妓女搶走,但他認為損失最慘重的還是那本連書名都沒有的殘書。猶太人天生就有著對于文字的瘋狂熱愛,書本已成為他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猶太人對于死亡一向習以為常,甚至對死亡懷有極度的好奇,這在路易身上得以顯現,他一生狂熱地渴求了解彼岸的世界。從小他父母就在他面前時常提起死亡及臨死的情形,自然而然,路易漸漸對死亡進行了思考,“可是一旦我們死了,物質還原為物質,我們就被消滅了。那么,我們到底屬于哪個世界?是這個物質世界,還是另一個世界—支配物質的世界”。而這個問題其他非猶太人是非常不喜歡討論的,就連他的女朋友斯蒂芬妮,一個非猶太女孩也對此表示出不耐煩。
與生俱來的身份特殊性和差異性在主人公路易身上得以體現,隨時提醒著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對于妓女的挑逗,酒吧老板一個非猶太人會直接把妓女按倒撕掉她的衣服,然而路易不會。“在她還穿著大衣的時候,為什么不把她按倒,撕掉她的衣服?換了酒吧老板就會那樣做了。因為他生性如此,而我不是,我生來就不會那樣干”。當路易把酒鬼送回家,幫酒鬼的兩個孩子做豬排時,他感受到了深深的罪惡感“被恐懼籠罩住的教養一下子往外噴,塞滿了喉嚨,肚子在隱隱作痛”。雖然年少時候的路易有著叛逆一心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但是他的骨子里卻一直都是個非常傳統的猶太人。
與其說路易本身有著強大的記憶力,不如說是由于他自身個人原因不愿意忘記過去那段回憶。盡管過去的回憶帶給他的也許是痛苦,但是由于對個人生活的重視、對民族生活以及對人類整體生活的高度關注使他必然牢記過去。他通過回憶自己的個人經歷旨在告訴他的兒子及猶太同胞們要牢記歷史,牢記自己的身份,否則將會像他那天所經歷的一樣令人啼笑皆非。
三、回憶敘事的視角
敘事者站在現在的某個位置來講述過去所發生的事時,必然會產生一個回憶性的敘述視角。而這個時候敘述者的立場和觀點都是現在的,因此對于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往往會帶有一種現在的審視和理性的態度。在《記住我這件事》中,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身份講述過去所發生的故事就產生了回憶的視角,為了實現過去與現在的融合,貝婁選擇了采取在常規視角和經驗視角之間進行不停的轉換的敘事方式。
《記住我這件事》是以“我”——路易,一個即將壽終正寢的老人的回憶而展開的。這是一篇典型的以第一人稱來進行回憶性敘事的小說。敘事者“我”用兩種視角進行交替講述故事:一個為敘事者也就是老年時候的“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個為被追憶的年少時候單純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這兩種眼光可以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在故事的一開始現在的“我”就對自己唯一的兒子講述了一件一直以來無法說出口的事——有關性的秘密(猶太民族所一直忌諱的事)。接下來視角一下子切換到了少年時候的“我”,那個時候的“我”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并且是“一窩性欲強烈的蜜蜂”,對于性尤其感興趣,于是就發生了接下來的一幕幕不尋常的事件:先是被妓女戲弄,丟了衣服;接著穿著女裝被藥店老板和酒吧老板所嘲笑;然后被迫送酒鬼回家,還要幫忙做豬排。可以看出這一幕幕狗血的事件都是由于“我”對性的欲望所引發的。講完這段回憶,接著視角再一次切換,“我”又回到了現實中的自己,現在的“我”已不再年輕,對于性也不會像年少時候那么沖動,更多的是一種坦然和理想。
四、回憶敘事的現實意義——認識自我
回憶敘事使得使得過去與當下相融合,從現在出發來審視過去的自己,同時為未來做出一個指向。“我們不能把記憶描述為一件事的單純反轉,或是以前的一個微弱的影象或摹本。它不單單是一個重復,而是對過去的一種重生;它隱含了一個創造和建構的歷程”。路易以超強的記憶力為基礎,以回憶建構自己。過去在回憶中得到重生,這種重生已經不再是簡單意義上對過去的重復,而是過去在現在的條件下得以重生,從而幫助自我建立一個完整統一的自我認識,并以這種認識指導自己,重塑自己。
當路易臨近死亡,知道自己不久之后將會撒手人寰時,他開始以記憶的方式詢問起自己的根源,這個根源起源于生命的開始,而生命開始的源頭必然是與家庭,父母有關的,因此少年的時光在路易記憶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生命總是與死亡如影相隨的,路易對于死亡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母親的死亡。那個時候的他對死亡充滿著恐懼害怕,“當時我知道她要死了,卻不允許自己這樣想”以及他對于母親臨死之前的形象描寫,就是因為當時自己內心的害怕和恐懼才使他印象深刻。他對于死亡的恐懼除了母親的原因,還因為那個不平常的一天。那天他在送花時正好碰上客戶家的女兒去世,這讓他親眼見證了死亡,帶給他非常大的震驚。而反觀現在的路易,回憶使他對于死亡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對死亡不再充滿恐懼害怕,而是懷著坦然的心態去面對它。在故事的最后,路易道:“一切都過去了,我已做好準備。”
五、結語
敘事是作者向讀者傳達知識、情感、價值和信仰的一種獨特而有力的工具。小說《記住我這件事》一如貝婁的其他小說,是貝婁關注人類命運,關注個人與社會的融合與價值的體現。在故事中,貝婁借路易之口“在世上,我們所知的一切在死后的最初那幾天都會展示給我們。我們在這世上的經歷是宇宙所希望的,也是它自身更新所需的”,道出了真理。貝婁希望通過他的作品,讓那些脆弱的人去接受,去記住這一切。因此他將回憶敘事作為敘事策略從而達到了一種深度認識自我并高度關注人類精神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