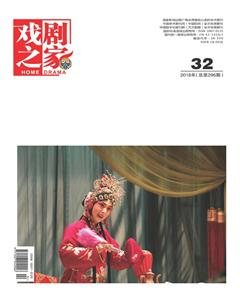李澤厚《美的歷程》中魏晉與明清時期人物心理對比
高揚鵬
【摘 要】本文對李澤厚《美的歷程》中魏晉名士和明清士大夫的心理進行梳理,對比分析了魏晉時期和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外在表現和內心深處的統一和落差,進而探討了中國文人士大夫面對不同的政治環境和精神氛圍,如何去排遣、宣泄內心,這種尋求解脫的超然精神對我國傳統藝術文化有一定的影響,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對于生命和自由的摯愛與追求。
【關鍵詞】李澤厚;《美的歷程》;魏晉;明清;人物心理
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32-0227-02
李澤厚是中國當代學術史上最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美學家之一。他是中國當代美學的建構者,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者。其代表作《美的歷程》《華夏美學》《中國思想史論》《己卯五說》在當代國內的美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史論結合的方法對于中國古典美學的梳理和分析很是精辟。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說《美的歷程》是部大書,是一部中國美學和美術史,一部中國文學史,一部中國哲學史,一部中國文化史。作者在書中以史論結合的方式就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做了經典分析,本文通過對魏晉與明清時期人物心理發展的宏觀梳理,從這兩個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異同的對比分析,發現從政治環境、科舉制度、思想精神解放的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人物心理也有差異。
一、魏晉名士心理概述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期,是一個哲學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躍、問題提出很多、收獲甚為豐碩的時期。這個時期也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都經歷轉折和變化,這種變化根本原因就是兩漢經學的崩潰。從《世說新語》中清晰看到魏晉時期一轉前朝的風格,注重內在的思辨風神和精神狀態,于是這個時候文人士大夫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隨著時代動亂和農民革命的興起,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在魏晉時期成為主流,同時也為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注入新鮮的血液。魏晉門閥士族由于離政治太近,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這些門閥士族看似生活在榮華富貴之中,卻又滿懷憂慮,身不由己的處于政治斗爭之中。所以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看起來是縱情山水,瀟灑自如,其實內心是非常的苦悶、恐懼和煩惱。李澤厚也說:“魏晉士人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非常痛苦。”[1]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提出了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觀點。人的自覺是突破兩漢經學最大的表現,文人士大夫不僅自覺地意識到要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點,當尋求自我發展的時候無疑就打破了兩漢統治者利用神學目的論支配控制人性的活動。當意識形態上突破這種束縛后,魏晉門閥士人一度縱情山水、志趣玄遠,外表看起來似乎是頹廢、消極的情緒充斥著精神生活,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看起來的悲觀頹廢,實際上門閥士族內心是對人生理想更強烈的追求和留戀。由于人的自覺則導致文的自覺,文的自覺更多表現了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作品。張法在《美學概論》中說:“藝術的目的就是美,是為美而創造出來,并讓人欣賞的。”[2]正如李澤厚所言:“認為真正有價值有意義能傳之久遠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學表達出來的他們個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從而刻意作文,‘為藝術而藝術,確認詩文具有自身的價值意義,不只是功力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3]這種文的自覺同樣也表現在了魏晉時期其他藝術之中。
二、明清士大夫心理概述
秦漢以大美拙樸為特色,魏晉注重精神思辨。隋唐科舉制度的發展,宋明理學對思維的進一步固化,歷經元朝蒙古族對中原封建王朝的統治,使得傳統文人士大夫不被視為棟梁精英,拒之于統治核心之外。文人士大夫有更多的精力和自由投身于審美文化實踐,這使得明清以來中國的傳統審美文化不論是繪畫、雕刻、瓷器,還是戲劇、小說都有了極大的發展,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造詣。這一切變化也深刻展現在了明清文藝思潮的發展之中,最典型的體現在了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明清文藝所描繪的世俗人情。與魏晉時期相比,明清時期文人從思想、意念、人物、形象、題材、主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就是從一種貴族的氣質走向一種市井小民的生活。這些世俗小說、市井文學具有現實性、世俗性與腐朽庸俗的意識滲透,主題亦沒有深刻遠大的理想,自然顯得平淡無奇卻又顯得真實豐富。明清時期文藝思潮的發展也具有兩面性,上層文人士大夫外表看起來是追求功名利祿,其實更加向往在閑暇、退隱之后對藝術的追求和對審美實踐的滿足。縱觀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不論是魏晉時期對藥、酒的偏好,還是明清時期對于實踐藝術的偏愛,其實都是對于內心這種不滿的一種宣泄,所以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上如何排遣以及如何解答貫穿了整個士族的喜怒哀樂,前者寄托山水尋求解脫的如陶淵明,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士大夫信仰禪宗,希圖某種了悟解脫皈依佛宗,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三、魏晉時期與明清時期人物心理對比
魏晉時期與明清時期人物心理統一。不論是魏晉時期門閥士族下的文人士大夫,還是明清經歷科舉制度后的文人士大夫在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都有統一性。魏晉和明清士大夫都有對于自我的認識和自我的發展,這根源于中國文人士大夫在精神上如何排遣困惑,不一樣的是明清時期封建士大夫對政治抱負的空漠之感有所增加。魏晉時期和明清時期都有對于文的自覺的理解,只是程度不同,魏晉時期其藝術作品更多表現出“藝術作品為了藝術而藝術”的實質。而明清時期藝術作品從作者本身而言要相對被動,一方面是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明清時期的政治環境的影響,文人士大夫在表達藝術的意境上委婉和隱喻。
魏晉時期與明清時期人物心理差異。魏晉和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心理相比主要是外在環境和內心理想之間的落差造成的。前面我們論述了魏晉時期文人士大夫外表看起來是瀟灑自如,但是精神是極度痛苦,但是這種痛苦的背后卻是對生命的急切渴望。而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首先是外在的政治環境不允許有魏晉時期名士一樣的灑脫自如,這一方面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主義的影響,受隋唐以來科舉制度對士人思想的禁錮;另一方面在于元朝統治集團把傳統文人士大夫拒之于政治核心之外,使自元朝以來文人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自由投身于審美文化實踐之中。所以,明清時期文人士族表面看起來忙忙碌碌追求功名,其實內心是要極力打破這種環境的束縛,尋求一種屬于文人士大夫的自由,不管是世俗文學的發展,還是寄托山水的怡情,都是要突破這種精神的壓迫。這種人物心理差異總結起來既是魏晉時期外表灑脫,內心痛苦,但對人生理想卻奮力追逐,明清時期外表看似忙碌充實,其實內心的追求是“象外之象”、“韻外之致”、“味外之味”的超越性。
四、結語
通過以上在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兩個方面分析出魏晉名士和明清文人士大夫外在的表現和內心的精神追求的統一和差異。魏晉名士外表看起來飲酒服藥、縱情山水,實質上他們內心是異常痛苦和煎熬,他們寄希望于打破束縛、建功立業。而明清時期文人士大夫階層外表看起來規規矩矩,其實質是內心是具有豐富的超越性,用自由、閑暇時間尋求更多的審美實踐和藝術欣賞。這樣看來,不論是魏晉名士外表和內心的精神差異中有多么大的不同,還是明清士人在藝術作品上表達的不滿,其實質都是現實精神感受和理想生活環境之間的落差所造成的,這不僅表現了士族階層對內心不滿的宣泄和對精神壓迫的排遣,更是表現出了文人士族對生命和理想的頑強追求與熱愛。
參考文獻:
[1]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9,104.
[2]張法.美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68.
[3]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