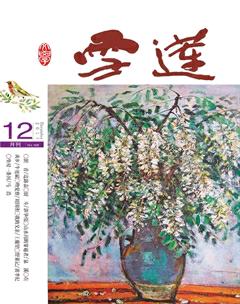黃桑林海
李陽波
黃桑自然保護區,古為苗族所在地。它藏在湘西南的千山萬嶺之地,如同一位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絕代佳人,盡管山風吹了千百年,卻未能將它的芳名吹送出萬嶺千山之外,年復一年,它只得獨守著不老的青春和深閨的寂寞。是當仲夏,久困滾滾紅塵的我,渴望黃桑山林的那一派清凈和清涼,于是和友人結伴,去朝拜黃桑的山靈和水神。
人在黃桑之外,就已感到郁郁蔥蔥的綠色照人眉睫了,及至進入黃桑,車窗就像電影里的蒙太奇一樣,汽車每轉一個彎,山神就給你換一個新的風景,將它的密樹濃陰接青疊翠綠給你看。大家在車內一會兒左顧,一會兒右盼,被見所未見的那一派嫩綠淺綠翠綠深綠墨綠濃綠總而言之一統天下的綠鎮住了,噤口無言,平日蒙塵的眼睛都頓時發亮,只顧急急忙忙飽餐窗外的秀色。高攀云霧山頭壯觀林海,是我們此行的高潮,序曲則是去源頭山瞻仰長苞鐵杉。無論對本地人還是外來客,名聞遐邇的長苞鐵杉都在那山頂上召你去朝見。我們自然也首先去趨拜,懷著遠客進香的心情。
在茂盛的樹的家族中,鐵杉確實有可以傲視同類的歷史,地質學家和動植物學家告訴我們,距今約有一兩百萬年以前,地球曾經歷了一次大的冰川期,史稱“第四冰川期”,世界上的動植物在那一場浩劫中大都無法幸免,躲過來的則只能歸之于天意了。長苞鐵杉就是世界上已經宣告斷子絕孫的名貴樹種。但前幾年卻在黃桑的源頭山上發現,這被稱為古生物活化石的長苞鐵杉,不是碩果僅存的一株兩株,而是三十八株占地三畝,它們巍然成林,在山頭上書寫顯赫的家世,在半空中張揚高貴的門第。在鐵杉林下,任你是什么目空一切的豪杰,大約也不能目空這與天地同壽的英雄吧?它們主干灰褐蒼古,粗可數圍,懷著一股岸然而傲然之氣直上重霄,枝椏在樹身對稱而平行地展開,撐起一團巨大的華蓋。鐵杉樹,真應該改為英雄樹,它排開四周的風景,昂首半空,我們仰望的目光固然被它提升,其它努力追隨而上的喬木呢?也只能仰面傾聽它的我們聽不懂的宣示。至于那些匍匐在地的矮小的灌木,更只有自慚形穢了。鐵杉樹一副英雄氣概,但它居然也有兒女柔情。那種英雄氣概和兒女柔情的對比,那種剛與柔的結合,真是造化的一大奇觀。除了個別例外的獨立特行的單身貴族,鐵杉樹總是兩株樹干共一個樹身相依相偎而直上青空,而兩株樹干的枝椏雖如觀音千手,卻互相糾纏在一起,宛如情人相擁相抱的手臂。所以當地人又贈給它許多美名,稱之為“合歡樹”、“連理樹”或“情人樹”。在號稱現代文明的人間,海枯石爛的愛情似乎越來越只能從詩經和漢魏樂府中去尋覓了,試婚成為新潮,夕和朝離視為觀念更新,不斷攀升的離婚率也似乎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而鐵杉樹卻郎心如鐵妾心也如鐵,除了個別的獨身者之外,它們在深山中彼此傾訴的是地老天荒的情話,堅持的是源遠流長的古風。
平地有好花,高山有好水。黃桑綠樹如海,是因為有豐富的水源的滋潤,而茂密的林木,又挽留了天上的雨水和地下的潛流。
清涼的山泉,是大山的沒有污染的淳樸乳汁,它們或從山谷中潺潺而下,或自巖隙間汩汩而出。我們在山道旁或農家的吊腳樓邊,常常看到不同形狀的竹管在引渡那山中的玉液瓊漿和那密林深處的神秘故事,其下則多用一個古樸的木桶接住。同行的白發已侵的詩人丁可,連聲說“美呀美呀,就是一句詩也寫不出來了。”同行的另一位詩人兼攝影家吳允峰卻正當年,他一面忙著用鏡頭去俘虜山林的風景,一面出口成章:“巖隙間汩汩的泉流,不知道是 A弦B弦,鳥語滴落在水桶,竹管把源頭的故事送到你的嘴邊……”
如果山泉是大山未成年的孩子,那么溪流則是它待字閨中的女兒了。城里人向往山林,在黃桑的林海之中,山溪卻一門心思想嫁到山外去,她知道遠方有水庫和大江都在等著她。只是山神舍不得她離家遠走,搬來許多奇形怪狀的巨石想攔住她的腳步,水石相濺,她只能提起自己白色的裙邊匆匆向前,而千山萬嶺不僅左攔右截,在兩山狹窄之處,又常常用濃枝密葉覆蓋交叉在上空,使她往往在既嚴又慈的父親懷抱中迷失了道路而百折千回。在山中,看不見山神和溪流的游戲,而令我心神震蕩的卻是那不時可見的瀑布了。黃桑的瀑布很多,它們卻甘于默默無名而在山中瀟灑送日月,只共同推舉高達三十米的六鵝洞瀑布作為它們的代表,六鵝洞瀑布在譚汲水村的懸崖之上飛流直瀉,我們未見其瀑就先聞其聲了,遠遠就聽見它轟轟而嘩嘩,仿佛在舉行深山的新聞發布會。及至走近一看,只見它真正是口若懸河,飛流濺沫,大約是在向來賓介紹黃桑的物華天寶吧?它氣盛聲洪,不容置辯,我們佇立在它面前洗耳恭聽,久久都沒有找到提問的機會。我想問的是:在漢語里,“兩全其美”真是一個美麗的成語,好山沒有好水來陪襯,好水沒有好山來捧場,都同樣令人遺憾,人和自然的關系是否也是這樣呢?
真正要欣賞黃桑林海的壯觀,還是要登上云霧山的頂峰去作一番振衣千仞的鳥瞰。
砂石路面的公路雖是現代文明派來潛入深山的哨探,但到林木森嚴的山下,它也只是戛然而止了。云霧山從山頭拋下一條羊腸小道來迎接我們,大家就順著這條繩索攀援而上,這里是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動植物種類繁多。熱帶、亞熱帶甚至寒帶的植物都約齊了到這里相會,所以它被林學家稱為“植物基因庫”。春天如火如荼的盛大花展已經過了期,綠林里現在只有夏日的野百合在綠的汪洋中堅持自己的獨白。我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綠,綠葉密密麻麻,綠樹叢叢簇簇,綠林郁郁莽莽,天上的陽光呀怎么也漏不進來,山外的風啊怎么也擠不進去。平日里人說“眼紅心熱”,我懷疑在黃桑山里呆久了會“心熱眼綠”,至少我的肺葉現在只怕已經染綠了。山林除了綠,就是靜。尤其是林木幽深之處,靜得十分曖昧,真擔心華南虎和有關野人的神秘傳說會一起竄了出來。森林的觀念太古老和封閉了,它根本不知道山外還有人間和紅塵,還有就綠燈紅的夜總會,還有大大小小遠遠近近的汽車喇叭合奏,還有別人灌向你的耳道毫無意義的講話報告之類種種噪音。來到密林之中,你的耳朵就徹底休閑,這里沒有人聲和機器聲,而只有水的濺濺,蟲的唧唧,蟬的嘶嘶和鳥的啾啾了。不知名的鳥雀在枝椏間瞅瞅弄舌,千鳴萬囀,這些正宗的純情歌手的即興演出是一派天籟,不取分文卻又令你聽得心醉神迷,不像山外某些搔首弄姿的歌星影星,要收越來越昂貴的出場費。水的濺濺蟲的唧唧固然使山林更顯得清凈,而鳥語和蟬鳴呢?你只有身入并深入山林,才能真正走進“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那兩句詩的境界中去。
終于登上最高頂了。極目四望,這才看清森林們以黃桑為中心,在這里召開四面八方的保護環境的綠色盛會。這消息傳得好遠好遠,遠近好幾個縣的邊界的森林都趕來參加了。森林啊森林,它是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支柱,是蕓蕓眾生的庇蔭,然而,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森林覆蓋率名列第一百三十一位,而至上世紀一九五0年以來,全世界的森林已損失了一半,每年以一千八百到二千萬公頃的速度遞減。在亂砍亂伐的伐木叮叮聲中,難道你不會想起海明威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我久久地佇立在山巔的云遮霧繞的懸崖之上,面對腳下那地久天長碧波翻滾的海洋,一縷幽思不禁縈繞心頭:西方金黃的向日葵找到了梵高為它傳達不朽,神州之南這茫茫蒼蒼的碧綠林海啊,會找到誰來為它作不朽的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