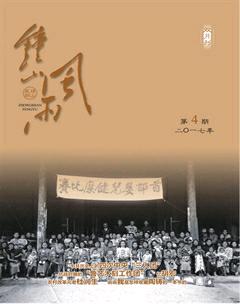抗戰(zhàn)時期的“魯藝木刻工作團”
吳繼金+賈向紅

抗戰(zhàn)時期,延安是中國抗戰(zhàn)美術中心之一,而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又是延安美術活動的中心和重要陣地。為了深入社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戰(zhàn),1938年“魯藝”成立“魯藝木刻工作團”,奔赴晉東南和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在緊張的戰(zhàn)斗環(huán)境中,“魯藝木刻工作團”成員一手拿槍,一手拿木刻刀,創(chuàng)作了許多反映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英勇斗爭的木刻作品,譜寫了一曲偉大的愛國主義光輝詩篇。
“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敵后活動近三年之久,先后輾轉活動于晉綏、晉冀魯豫、晉察冀三大抗日根據(jù)地,以木刻為武器進行宣傳,創(chuàng)辦了木刻工廠,播下了革命美術的火種,為中國新興木刻走向民族化、大眾化進行了勇敢的嘗試和成功的探索。著名美術理論家胡蠻評價說:“他們一方面為人們、為兵士供給精神上的食糧,而且,另一方面研究政治和美術,并對青年進行著美術的教育工作。這正是魯迅同志生前所講到的‘山野里的鷹隼,他們迅速地飛翔著,向著偉大的藝術的道路上邁進。”日本友人三下志朗曾贊揚說:“中國版畫家在非常艱巨的惡劣環(huán)境下,以大無畏的氣概,不向黑暗勢力低頭,用鮮血和獻身精神譜寫了中國新興版畫史。中國版畫家,是藝術家中的強者,在他們身上體現(xiàn)的是中國人民之魂,也是中國民族之魂。陳列的史料中,有一份《敵后方木刻》的報刊,是中國版畫家到敵后開展版畫活動的出版物,使我特別肅然起敬。在世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戰(zhàn)爭中,有哪一個國家的版畫家到敵人后方去戰(zhàn)斗?只有中國。”
“魯藝木刻工作團”的成立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包括美術家在內(nèi)的一部分左翼文藝家及文藝青年歷盡千辛萬苦,紛紛進入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投身于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yè)。“黃河之濱聚集著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子孫”,“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隨著全國各地大批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為了更好地發(fā)揮藝術武器在抗戰(zhàn)中的作用,培養(yǎng)抗戰(zhàn)文藝人才,活躍根據(jù)地的革命藝術活動,迎接邊區(qū)文化建設的高潮,1938年4月10日,由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發(fā)起,在延安正式創(chuàng)辦了魯迅藝術學院。
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安創(chuàng)辦的一所綜合性藝術學院。在當時如此艱難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去營建這樣一所藝術學院,其目的和意義何在呢?正如魯迅藝術學院在《創(chuàng)立緣起》中指出:“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侵略,把它從中國趕出去;為了鞏固世界和平;全中國人民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一致奮起,各黨各派團結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下進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戰(zhàn)爭,直至取得最后勝利。”“藝術——戲劇、音樂、美術、文學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最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于目前抗戰(zhàn)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養(yǎng)抗戰(zhàn)的藝術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緩的工作。我們邊區(qū)對于抗戰(zhàn)教育的實施,積極進行,已建立了許多培養(yǎng)適合于抗戰(zhàn)需要的一般政治、軍事干部的學校(如中國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而專門關于藝術方面的學校尚付缺如;因此我們決定創(chuàng)立這藝術學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國最大的文豪魯迅先生為名,這不僅是為了紀念我們這位偉大的導師,并且表示我們要向著他所開辟的道路大踏步前進。”
1938年4月,“魯藝”創(chuàng)辦之初,就設有美術系。三十年代活躍于上海的左翼美術家,如溫濤、胡一川、沃渣、江豐、馬達、陳鐵耕、黃山定、張望、張仃、胡考、夏風、劉峴、力群等紛紛來到延安,其中很多人在“魯藝”工作。在美術系剛成立時,就開設有木刻研究班,其宗旨是研究木刻技術,提高理論修養(yǎng),推動木刻運動。木刻研究班經(jīng)常性的工作是在延安街頭出美術墻報,一連出了4期。每逢節(jié)日,木刻研究班就創(chuàng)作印制許多作品,配上街頭詩,在延安街頭張貼。木刻家焦心河曾為重慶《新華日報》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魯藝”木刻時說:“我們經(jīng)常出墻報”,“所以延安的街道,城墻和延安人民的心中,都裝滿了木刻畫”。“每到紀念日,他們就印很多木刻,配上街頭詩,貼在延安周圍。”1938年10月10日,木刻研究班在延安舉行了首次木刻展覽,連展三天,觀眾絡繹不絕。參展觀眾在留言簿上寫道:“希望木刻到前方去!”“希望木刻到敵后去!”根據(jù)這一建議,胡一川于1938年底打報告給“魯藝”院領導,要求成立“魯藝木刻工作團”,深入到太行山敵后根據(jù)地,在八路軍129師、120師、115師搞木刻、辦展覽。“魯藝”決定抽調(diào)木刻研究班5人成立“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由胡一川擔任,工作團成員有彥涵、羅工柳、鄒雅、華山等。
“魯藝木刻工作團”在華北敵后的美術活動
1938年底,胡一川一行告別延安,在中共北方局的李大章帶領下,渡過黃河,越過敵人的封鎖線,翻過呂梁山、太行山,跟隨部隊在敵后抗日民主根據(jù)地進行美術宣傳活動。
從1938年冬到1939年春,“魯藝”木刻工作團主要是舉辦木刻流動展覽會。他們曾先后在晉西115師政治部、蟠龍村、雙池鎮(zhèn)、決死第二縱隊、沁縣銅川中學、長治縣蓮花池、決死第三縱隊等地開過七次展覽會和四個座談會,在長治縣出版的《戰(zhàn)斗日報》上出過一期專刊,使太行山區(qū)敵后廣大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國的新興木刻。但由于展覽的作品大部分是江豐從武漢帶到解放區(qū)的“全國第三次木刻流動展”中的作品,形式風格比較歐化,題材內(nèi)容也與根據(jù)地軍民生活有較大距離,欣賞的圈子仍不脫離美術界和知識分子,所以往往受到冷遇,雖然起了一定的宣傳作用,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木刻工作團的藝術家們在展覽的同時,也聽到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如:內(nèi)容不夠豐富、生動,情節(jié)性不強,形式上不美觀,最好有顏色群眾才喜歡看,等等。在對群眾的批評意見進行認真的反思后,木刻家認識到:“用這些內(nèi)容不夠深刻、形式帶有歐化的木刻作品,以巡回展覽的方式作為木刻工作團的主要工作,事實證明不是最好的辦法。開始以為帶一箱子木刻畫可以走遍天下的想法,看來不是那樣吃得開了。群眾要求我們放下老一套,要求我們創(chuàng)作內(nèi)容豐富而深刻的新作品,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新作品。”木刻工作團的成員虛心吸取了在敵后活動的經(jīng)驗教訓,根據(jù)上級黨組織的指示,決定集中精力,先創(chuàng)作木刻連環(huán)畫小冊子。胡一川創(chuàng)作了一套《太行山下》,華山創(chuàng)作了一套《王家莊》,彥涵創(chuàng)作了一套《張大成》,這些作品都是反映敵后斗爭的現(xiàn)實題材。形式方面都是故事連環(huán)畫,在刀法、線條的組織上力求明朗,部分地采用了國畫的技巧,使木刻藝術在走向民族化、大眾化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改變了木刻活動在抗日軍民中受到冷遇的境況,但總體而言一般群眾仍難于接受。endprint
“魯藝木刻工作團”的藝術家,深入戰(zhàn)地生活,虛心向民間藝術學習,經(jīng)過認真總結經(jīng)驗后,認為要真正發(fā)揮木刻藝術的威力,要真正實現(xiàn)木刻藝術的群眾化和民族化,應當把制作新年畫作為一個突破口,來一番新嘗試。對于木刻工作者來說,創(chuàng)作新年畫完全是生疏的工作,從創(chuàng)作、刻版到印刷發(fā)行都要從頭學起。為了解決水色套印、刻字技術的困難,他們特地從農(nóng)村請來一位民間刻工,又從新華日報社請來一位曾經(jīng)印制過舊年畫的工人,教他們刻版印刷知識。經(jīng)過20多天的突擊創(chuàng)作,新年畫終于出世了。第一批年畫共九幅,有胡一川的《軍民合作》、《破路》、《開荒》,羅工柳的《實現(xiàn)民主政治》、《積極養(yǎng)雞,增加生產(chǎn)》,楊筠的《織布》,彥涵的《春耕大吉》、《保衛(wèi)家鄉(xiāng)》等。均刻單線,印上五彩,非常鮮艷醒目。木刻團一共突擊印制了一萬多張水印套色新年畫。乘1941年春節(jié),他們除了通過組織散發(fā)以外,胡一川、楊筠等三人在臘月二十三民間祭灶日下午,到襄垣被日軍燒毀了的羊邑集市上擺地攤賣年畫,與賣舊年畫的地攤唱起了“對臺戲”。工作團賣年畫并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為了檢驗一下群眾對新年畫的喜好程度,如果賣不出去,就無償分發(fā)。不料僅用了三小時,幾千張年畫便被群眾搶購一空。木刻工作團一下子名震太行,群眾到處打聽他們的住處,紛紛趕來購買年畫。由于這些作品都是新內(nèi)容,農(nóng)民們叫它為新年畫。
木刻工作團創(chuàng)作的新年畫的成功,不僅使木工團的成員極為興奮,也引起了八路軍領導人的關注。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李大章等領導人都給予贊揚。朱德在延安“魯藝”的報告提綱中也指出:“在圖畫木刻方面,有‘魯藝派到前線去的木刻工作團創(chuàng)作的年畫,極受群眾歡迎,一出版,群眾馬上來買光。”大年三十這天,彭德懷也給木刻團寫來了祝賀信。
“魯藝木刻工作團”還共同擔任《新華日報》(華北版)美術編輯、刻制版畫的任務,為黨報刻木刻。除了經(jīng)常的配合社論刻報頭、插圖、木刻漫畫、短小的連環(huán)木刻畫外,還出過5期《敵后方木刻》,每期約印兩萬份,隨報送發(fā)。《敵后方木刻》1939年7月1日創(chuàng)刊出版,在其《發(fā)刊詞》中說:《敵后方木刻》“刻畫著一面大旗,大書‘堅持抗戰(zhàn),堅持持久戰(zhàn),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期,刊出了胡一川、華山、彥涵、陳鐵耕、鄒雅等所作木刻12幅。此外,在第3期上還發(fā)表了朱德總司令“打破敵人圍攻”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反對妥脅投降堅持抗戰(zhàn)到底”的題詞,用木刻刻出。
“魯藝木刻工作團”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木刻作品
“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胡一川赴晉東南后,任《新華日報》華北版木刻記者。1938年冬,日軍向太行山區(qū)施行“九路圍攻”合圍逼近之際,他剛給報紙社論《粉碎九路圍攻》刻好了一幅版頭畫,敵軍就快到眼前,他從容不迫地把畫和社論文字拼好版又印出一份樣張,才同報社堅持到最后的部分同志一起撤離。1940年春節(jié)前夕,胡一川遵照北方局領導人李大章的指示,創(chuàng)作了《軍民合作》等8套水印套色新年畫,用染布顏料和有光紙,趕印了一萬多張,在西營鎮(zhèn)集市上擺地攤,不到3個小時,就賣出了幾千份,此舉受到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來信表揚。《軍民合作》是胡一川深入敵后開展宣傳工作時所創(chuàng)作的一幅套色木刻。作品通過對老大爺給八路軍喜送彈藥的描寫,表現(xiàn)了抗日根據(jù)地軍民高度的戰(zhàn)斗熱情和軍民團結抗戰(zhàn)的必勝信心。畫面中雖然只有一人一驢,但通過老大爺行進中回頭顧盼的形體動作和臉部喜悅的表情,使人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運送彈藥的民工隊,收到了以少勝多的藝術效果。胡一川的另一幅作品《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創(chuàng)作于1940年。這幅作品完全采用了傳統(tǒng)中國木刻年畫的形式,以線條造型后填色的單線平涂方法,清晰明了,線條的用筆,強調(diào)了中國毛筆畫勾線時所特有的粗細流暢變化和頓挫節(jié)奏。畫面主體人物鮮明突出,畫一個八路軍戰(zhàn)士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舉起大刀,向敵人的頭上砍去。陪襯的人物是畫了一個拿著紅纓槍的民兵正要將槍刺向敵人。畫面中還出現(xiàn)兩個日本兵,一個手拿一面小旗,和另一個一樣,在八路軍強大的威力之下,作近乎仰面翻倒狀。
“延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彥涵,隨“魯藝木刻工作團”來到太行山,創(chuàng)作了一批反映八路軍和根據(jù)地人民英勇斗爭的木刻作品。1940年秋天,百團大戰(zhàn)時,彥涵創(chuàng)作的《八路軍占領井陘煤礦》及時反映了其中的一個戰(zhàn)役。八路軍對河北井陘煤礦守敵發(fā)起攻擊,一度占領了該礦,隨后將礦區(qū)設備拆卸運走或加以毀壞,使日軍占領下的該礦無法生產(chǎn)達半年以上。彥涵創(chuàng)作的《彭德懷副總司令在前線》,在1941年夏季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召開大會并向文藝界頌獎中,被授予美術一等獎。1941年春節(jié)前,彥涵在晉東南邊區(qū)刻了一幅《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新年畫。圖中畫關公頭戴紅纓夫子盔,內(nèi)穿鎧甲,外著蟒袍玉帶,足穿登云靴,坐于虎皮太師椅上,左手捋髯,右手捧書一卷。右有關平,戴朝天翅相巾,披人字甲、護心鏡,下系戰(zhàn)裙,腰扎包肚,左手按劍,侍衛(wèi)于旁。左邊周倉,頂盔披甲,扎綁腿,穿云頭灑鞋,兩手執(zhí)青龍偃月刀,目視關公手中之書。后有紅燭、帷幕。上寫“身在曹營心在漢”紅字。畫面下端,有四幅連環(huán)故事畫,內(nèi)容是漢將關羽身陷曹操營中,不受金錢美女誘惑,毅然闖關斬將返回漢營。由右至左第一、二圖畫曹操給關公送美女,贈金銀,關公無動于衷。上題“關公兵敗暫留曹營,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時時想乘機殺敵返回漢營。曹操上馬贈金,下馬贈銀,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陪侍都打不動關公忠義心腸”。第三圖畫關公騎馬揮刀斬蔡陽于古城之下。上題“關公終于脫離了曹營,過五關,斬六將,兄弟相會在古城”。最末一圖畫劉備、關公、張飛三人重聚,共圖漢室復興,關公忠義氣節(jié)永垂千古。像這樣通俗易懂的內(nèi)容,符合大眾欣賞習慣的民間形式,當時用來對敵偽宣傳,確是起了分化瓦解的重要作用。正如作者在日后回憶錄中所說:“《身在曹營心在漢》這張畫完全套用舊的年畫格式,甚至把封建的東西也利用起來了。在當時對敵斗爭異常尖銳的情況下,不難理解,要利用一切可能辦法深入敵偽心臟,去瓦解敵人,爭取抗戰(zhàn)勝利。……這種畫雖不能算是藝術,但在對敵宣傳上確實起了它一定的作用。有一位記者在報道里曾經(jīng)提過:一個偽軍官看到《身在曹營心在漢》這幅畫后表示:‘我要這樣做。當這畫發(fā)到偽‘維持會時,偽‘維持會會長也同樣表示這類意見:‘總不能忘記咱是中國人!”endprint
陳鐵耕曾在《新華日報》(華北版)刻木刻,于1939年4月參加“魯藝木刻工作團”。陳鐵耕的木刻作品《新麥》,是一幅反映根據(jù)地人民勞動場景的作品。在農(nóng)家院落內(nèi),畫面中拉磨的驢子只見到兩只耳朵,家庭主婦頭上搭了條毛巾,穿著一件深色的長褂子,肩上還趴著一個小孩,她的右手拿著掃把在照應著磨盤。在這個女人的身后,一個頑皮的孩子在拿著什么東西逗著那個趴著的孩子玩。在磨子的另一側,坐著一個老漢扎著褲腳,正架著一只腳在喝水,他似乎在看著正在動著的毛驢,又似乎在走神,反正是累了在歇著,門外一個背著一大捆柴禾的年輕人正邊走邊回頭望著什么,從門前經(jīng)過。畫面上的左下角有裝面用的簸箕和裝滿東西的布袋,畫面右上角有籮筐,靠墻還豎著一把叉草的叉子。整幅畫面構圖以磨盤為中心點,兩邊的布置達到了均衡的恰當效果,呈現(xiàn)出一派祥和的氣勢。除了木刻和漫畫創(chuàng)作外,難能可貴的是,陳鐵耕還是邊區(qū)第一幅革命國畫的創(chuàng)作家。他成功地采用國畫形式創(chuàng)作了連環(huán)畫《黃阿福》和《窮孩子》。《黃阿福》的內(nèi)容是富裕的農(nóng)民黃阿福因遭日軍摧殘而破產(chǎn),其寡妻、孤兒不堪村中惡霸的欺侮悲慘死去。惡霸當了漢奸,最后被抗日群眾處死。全畫共四十八幅,按其創(chuàng)作精神的豐富、繪畫的優(yōu)美,尤以黑色線條的渲染得宜,充分運用了國畫技術的長處,在前方魯藝開學的美展會上,頗得各方人士及敵后美術工作者的贊美。接著便是他的第二幅中國連環(huán)畫《窮孩子》,描寫一個雇工的孩子替財主放牛,不堪財主的壓迫剝削而投入抗日軍隊。從此,窮孩子過上了人的生活,還能上學識字。經(jīng)過戰(zhàn)爭的鍛煉和教育,他成長為部隊的宣傳員,把自己的身世講給戰(zhàn)友和農(nóng)家少年聽,成了優(yōu)秀的革命宣傳員。這幅共有28幅畫面的連環(huán)畫,不管從哪一方面來說比《黃阿福》更成熟,更老練,更奠定了用國畫技巧來繪制抗戰(zhàn)現(xiàn)實題材的基礎。陳鐵耕創(chuàng)作的這兩套連環(huán)畫,突破了舊國畫的陳規(guī),運用了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強烈的激情,融進了木刻、漫畫藝術成分,成為新穎活潑為群眾所歡迎的新國畫作品。同時,他發(fā)揚了傳統(tǒng)國畫的優(yōu)勢,構圖上發(fā)揮了中國畫繪畫線條勾勒簡練、墨色渲染得當?shù)拈L處,尤其是《黃阿福》,被“公認為是抗戰(zhàn)后第一幅在敵后出現(xiàn)的成功的中國連環(huán)畫”,“奠定了運用國畫技巧來繪制抗戰(zhàn)現(xiàn)實題材的基礎”。
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藝術家并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囿于藝術的象牙塔中,而是以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主義情懷,積極投身于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之中。“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敵后嚴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一手拿槍,英勇戰(zhàn)斗,不畏犧牲,一手拿木刻刀,進行抗戰(zhàn)宣傳,展現(xiàn)了中國藝術家高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斗爭的勇氣,值得人們永記。
(責任編輯: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