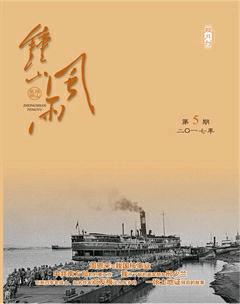催生抗戰文化的吳稚暉
徐霞梅
走進歷史深處,追溯戰爭苦難,探索抗戰文化的成因,從民族大義出發,尊重史實,客觀公正地研究和評述抗戰文化,是對所有催生抗戰文化,奉獻愛國熱忱、奉獻智慧、奉獻知識、奉獻力量,乃至奉獻生命的愛國文化人士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紀念。
1931年9月18日,日本襲擊沈陽,炮制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外敵入侵,國家危在旦夕。吳稚暉和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等人,立即向正在南昌指揮“剿共”的蔣介石發出急電,催促其速回南京,商討相應的緊急對策。但蔣介石并不主張馬上以武力解決東北問題,而希望國聯出面阻遏日本侵華。洞若觀火的吳稚暉深知希望國聯阻遏日本是靠不住的,中國早晚要和日本拼命。拼命靠什么?軍事是一方面,用文化輿論作為武器,從精神道義上克敵制勝,也是一方面。早在1906年,在法國旅法華人中享有“三劍客”之譽的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在巴黎創立“世界社”,創辦《世界畫報》《新世紀》等刊物,發表文章,為推翻清封建王朝制造革命輿論,效果堪勝槍炮。
在法國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和西方科學知識的吳稚暉,曾組織中法教育協會、中法大學,為溝通中西文化做出積極的貢獻,此舉得到英、美、法、瑞士等國家的認可和好評,他本人也因此被國際聯盟聘請為“國際文化事業協進委員會”委員。
“國際文化事業協進委員會”的宗旨是幫助各國學者改善際遇,增益學術交流,藉以促進世界和平。吳稚暉想何不借助“國際文化事業協進委員會”的力量,通過國際渠道,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的文化合作,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勢,喚起世界各國文化人士對中國的重視,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爭取全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譴責日本,孤立日本,用文化輿論制裁日本法西斯。
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淞滬保衛戰正式打響。在血雨腥風、硝煙彌漫的上海,吳稚暉利用“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的國際性及會址又在租界的優勢,指示協會工作人員采納“稍事國際暗洽”的方法,將日軍摧殘中國人民的暴行資料和照片,想方設法傳遞給國聯設在法國巴黎的文化合作學院備案公布,并與駐巴黎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交換情報,遙相呼應,揭露日本侵華暴行。與“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有著密切聯系的外國記者,如美國記者海嵐·里昂拍攝了大量日軍轟炸上海、殘害無辜民眾的照片,在海外刊登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12月13日,南京淪陷,美國記者弗蘭克·提爾曼·德丁親眼目睹日軍獸行,寫下了《所有俘虜均遭屠殺》的報道,冒著生命危險,通過英國郵輪發電報傳回美國及時報道,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日本法西斯對中國平民的反人道侵略罪行。又如法國傳教士饒家駒,從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救護難民區,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在吳稚暉的主持下,妥善安排浙江大學、中央國術體育專科學校、江蘇教育學院、無錫國學專科、廣東教育學院,上海的交通、大夏、復旦、同濟等大學,以及江浙一帶的文化學術機構和人員安全疏散,安全運送文物典籍,為賡續文化命脈、保存和培養國家人才做出了貢獻。
1937年南京淪陷前夕,吳稚暉離開南京西華里一號住所時,在墻上揮毫題詩:“國破山河在,人存國必興。倭奴休猖獗,異日上東京。”
當時蘇錫常相繼陷落,南京瀕危旦夕,“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江南,哀鴻遍地,百姓惶惶不可終日。吳稚暉這首充滿必勝信念的五言詩,無疑似黑夜里的啟明星,讓絕望者看到生的曙光,令悲觀者重鼓抗戰勇氣。
八年后,日本無條件投降,歷史證實了吳稚暉的預見。這首如今讀來仍令人蕩氣回腸,豪氣十足,言簡意賅的五言詩,字字彰顯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愛國豪情,這難道不是抗戰文化中的經典精品嗎?
八年抗戰中,吳稚暉以“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會長的身份,與海外民主自由人士密切聯系,不斷撰文對外宣傳抗日,國內國外遙相呼應,一起從輿論和道義上譴責日本侵略者,起到了飛機大炮不可替代的懾敵作用。
吳稚暉與汪精衛、陳璧君曾經都是反清革命的同道人,抗戰時,汪精衛夫婦貪生怕死,墮落成叛國投敵的漢奸。有著“民國金牌罵手”的吳稚暉,立即披掛上陣,口誅筆伐揭露和斥責汪精衛的賣國行為。
吳稚暉奮筆疾書,撰寫了《賣國賊是世上最兇惡的毒物——汪精怪夫婦因學三等娼妓而甘之》《痛斥汪逆賣國勾當》《肯亡國就調整,要救國就抗戰》《建墓鑄逆緣起》等檄文,酣暢淋漓地痛罵漢奸汪精衛夫婦,大快人心。
去過重慶的人都知道,山城出門就爬坡,上下走臺階。1942年6月26日的凌晨三點半,78歲的吳稚暉高一腳低一腳在山坡上提燈獨行來到電臺,面對麥克風,聲情并茂地把真實的抗戰形勢通過電波,講給淪陷區的同胞們聽。我們不妨想像一下,黝黑的夏夜,月朗星疏,上海、蘇州、無錫、常州、杭州、武漢等淪陷區的同胞,關上門窗,拉上窗簾,耳朵貼著無線電,通過“收聽敵臺”的方式,聽大名鼎鼎的民國元老吳稚暉講抗戰形勢,告訴他們日本人在珊瑚島、中途島都吃了敗仗,美國飛虎隊和中國空軍的飛機已經轟炸日本本土,日本快完蛋了!這黎明前的佳音,對淪陷區的同胞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視我國各級學校師生均為反日分子,不擇手段地迫害愛國師生,使我國教育事業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摧殘。視教育為生命的吳稚暉大聲疾呼“抗戰是救國,教育是抗戰建國,是真正的建國,是興國的“國家之舉”。
他說:“抗戰必須建國,建國尤重生產。生產事業之推行,首在人才之培植,故生產教育,戰時較平時尤為重要。”“將來的建設,五年中需要大學生54萬。但把現有的大學生湊來湊去,還不滿30萬。依我看,中國如真成為一個道地的現代國家,54萬大學生一定還不夠。恐怕少不少要540萬。”“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教育是百年樹人的萬年大計。”
吳稚暉為戰時教育先后寫了《教育與救國》《救國須改良教育》《談中國教育腐敗亟待改良》《門外漢意中之教育問題》《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五次全會教育組審查委員會對于教育報告之審查意見》《各省生產教育均以經費短缺陷于停頓狀況亟應切實救濟以利建國由》《寬籌社會教育費加緊推進社會教育以加速完成抗戰》《確定辦法迅籌的款以挽救全國高等級教育危機案》《提請救濟戰時高等教育以宏人才之造就案》《救濟青年與中等教育改制》等文章。1940年,未淪陷區通貨膨脹的惡果凸現,大、中、小學師生的溫飽得不到保障。眼看這些國寶級知識精英和風華正茂的學子掙扎在饑寒交迫中,心痛至極的吳稚暉敦促政府不惜負外債用美金,也要關心和改善大學的教學環境和保障師生的生存必需。1940年底,教育部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大學、中學、職業專科學校全部實行公費制,寧借外債也要為教育完全兜底。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位“兩彈一星”元勛,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后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責任編輯:劉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