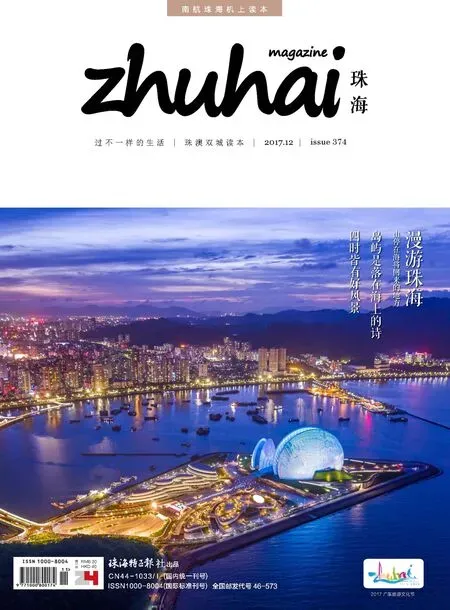釀一壇酒 就像做一世人
吳曉波
釀一壇酒 就像做一世人
吳曉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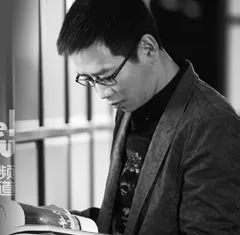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代表作品《大敗局》《激蕩三十年》。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
秦明和黃錦春是“山村風物”的創始人,兩人同為客家人,一山之隔,兩個省份,一個江西,一個福建;一個負責市場,一個負責釀造。
1
秋天,白露剛過,黃錦春就走進步云村,這是個位于武夷山脈中段東南側,常住人口不到60人的小村莊,幾乎快要與世隔絕。但就是這個村莊,森林覆蓋面積達到了84%,客家黃姓三代都在這,守著這兒的一眼好泉水。
“一定得在冬至前把水放好。”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經驗。 釀酒用的水,立冬和冬至之間的水是最好的,過了冬至就是“春水”,“用春水釀的米酒,放不久的。”這些經驗,黃家人已經用了三代,也傳了三代了。
釀酒的糯米,也必須是本地的高山稻——荊糯,這里特有的黑土地和晝夜的溫差,令荊糯的顆粒飽滿,淀粉含量高,是釀米酒的最佳選擇。“我們也用過外面的有機糯米,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釀出來的酒,味道就是差那么點。”
收來的糯米還需要加工,脫粒、洗凈、浸泡、瀝水、蒸制、淋水、發酵、放水,然后繼續酒化發酵。每一步都是黃錦春和家人親自來做。
靜靜等待100-110天,到了立春前后,壇子里開始飄出酒香,這時酒化發酵就算結束了。但這時離釀成一壇正宗的客家米酒,還有兩個重要步驟——炙酒和窖藏。
炙酒前,先封住壇口,再覆上草皮土坯,在壇子四周攏上谷殼,陰火炙烤一天,把酒煮沸,這樣既滅菌,也使口感也更醇香。
這也是客家米酒區別于江南米酒的重要一點。經過炙烤的米酒,酒體內的濕氣散去,即使存放一到兩年都不會變酸。這時的米酒酒體清亮,入口微甜,要是再經過酒窖里的低溫發酵,甜味漸漸隱去,各類芳香物質和氨基酸涌出,使得米酒具有獨特而迷人的醇香,口感更為微妙。
2
在謹遵祖傳釀酒方法的同時,秦明和黃錦春在對傳統客家米酒的創新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努力,他們不斷開發新的花果風味米酒。
“親,有桃花酒嗎?”這是今年8月份“山村風物”收到最多的客服問題,秦明不禁好奇,大家都怎么了?后來他才發現,這是因為當時影視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熱播,大家都開始瘋狂求購劇中同款“桃花酒”。
“桃花酒”他們并不是沒有嘗試過,“產品沒有識別度”,這是他們最終沒有推出桃花酒的原因。“如果僅靠提取桃花的香味和顏色,是做不出粉色的桃花味米酒的,我們也不想用人工的增色增香劑,所以就算了。”
就算面對如此龐大的粉絲市場,他們也不愿把自己不滿意的產品放上貨架。
“不能光說失敗的,我們也有成功的案例,桂花米酒就是一個,都是我們師傅手工挑的桂花,現在正是好喝的季節。”其實,秦明和黃錦春在釀酒上做出的創新,一開始是不被老一輩認可的。
但是他們堅持了下來。
3
在被問到“山村風物”的米酒有什么特別之處時,秦明不好意思地說:“其實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我們就是老老實實按照老祖宗的方法釀酒。”
關于“山村風物”這幾年來的發展,秦明略顯惆悵,“請不到有能力的人啊。前幾年的時候,也有投資人找到我,要給我投資,幫我擴大團隊,加速發展。但是他們不理解,釀酒這件事,求不了快的。”
為了保證品質,“山村風物”每年的產量都十分有限。“我們現在一年13萬的產量,要我一下子做到130萬,我只能靠外部因素的介入來完成目標,那樣就變味了。”“山村風物”對秦明和黃錦春而言,是像孩子一樣的存在,“要是為了發展而發展,會讓它(山村風物)變樣的。”
“我不懂營銷。”采訪中秦明一直重復這句話,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努力想改變。他曾聘了專人負責市場運營,“那個時候,他在酒的名字上加了一堆關鍵詞,我看著就不舒服。”秦明坦率地說,“但我想人家是專業的,我就忍著沒說,最后我還是偷偷改回來了。自己該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們不去蹭人家的熱度。”
聊到對未來的打算時,秦明說:“我想開酒館,純粹的酒館,只賣酒。現在滿大街的茶館、咖啡館,卻沒有幾家真正的酒館。”
“釀一壇酒,就像做一世人,踏實勤勞雖有笨拙,但求對得起良心。不爭不搶,不急不躁,寧可走慢些,也要走遠些。”這是秦明和黃錦春的態度,也是“山村風物”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