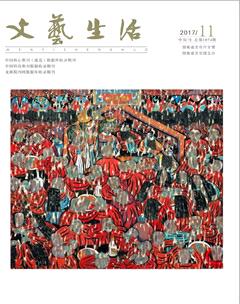交響詩《圖奧內拉天鵝》的旋律研究
陳辰
摘 要:交響詩《圖奧內拉天鵝》是芬蘭民族樂派作曲家西貝柳斯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大衛.伯奈特等《西貝柳斯傳》中稱該交響詩是第一首真正揭露西貝柳斯內心秘密線索的樂曲,并且認為該交響詩最顯著的特色就是樂曲的旋律結構,尤其是英國管綿長的環繞型不對稱旋律。因此,對該交響詩的旋律進行深入地研究,不僅可以較為深刻地認識該曲旋律獨特的創作手法與其民族風格,而且可以進一步揭示該曲英國管旋律表現出的文化內涵與美學意蘊。筆者通過觀察法、音樂分析法與比較法等研究方法,并查閱了相關文獻,認為該曲的旋律具有相似性和自相似性的特點,即在異化對比的旋律發展中,時隱時現地平行貫穿著主題旋律的兩個動機的旋律片段及其不同程度的變形與變奏。
關鍵詞:環繞不對稱;旋律片段;多利亞調式;自相似性;西貝柳斯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32-0059-09
一、前言
西方音樂史上有三只著名的“天鵝”:圣桑的 “天鵝”、柴可夫斯基的“天鵝”與西貝柳斯的 “天鵝”。三只“天鵝”可謂各有千秋,但也有類似之處。
本文重點研究西貝柳斯的“天鵝”——《圖奧內拉天鵝》。讓.西貝柳斯(Jean.Sibelius,1865-1957)是芬蘭民族樂派作曲家,古典主義音樂與浪漫主義音樂堅定的繼承者與捍衛者①,他的作品中兼具浪漫主義風格與新古典主義風格,這兩種風格分別體現在他日后創作的七首交響詩中。《圖奧內拉天鵝》是西貝柳斯早期作品“勒敏凱能組曲”(Lemmink·inen Suite,Op.22)中流傳最廣的一首。該組曲主要描繪了芬蘭史詩《卡萊瓦拉》中風流倜儻的勒敏凱能,為博芳心去芬蘭冥府圖奧內拉刺殺神圣天鵝,但反被殺死終又復活歸鄉的故事。該曲是組曲第三首,形象地描繪了勒敏凱能刺殺神圣天鵝未遂反被牧人殺死后,天鵝在圖奧內拉護城河中游動哀鳴的情景。
曲中不同的旋律因素描繪不同的事物:英國管旋律描繪天鵝,弦樂組合奏旋律描繪河水等。因而,該曲具有較強的畫面感,并具有一定的印象主義風格。大衛.伯奈特等所著《西貝柳斯傳》中稱該曲是第一首真正揭露西貝柳斯內心秘密線索的樂曲,并且認為該曲最顯著的特色就是樂曲的旋律結構,尤其是英國管綿長的環繞型不對稱旋律②。
可見,交響詩《圖奧內拉的天鵝》以環繞不對稱的英國管吹奏的旋律為其最大特色,但這條旋律只是整體旋律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對整體旋律進行較為深入的觀察、分析與思考,才能較為深入的認識該交響詩的旋律特點,才能進一步了解英國管旋律的特點及內涵。旋律亦稱曲調,是各音按一定邏輯關系互相連續的單音進行,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音高、節奏與調式③。旋律可以是單聲部音樂的整體,也可以是多聲部音樂的主要聲部。
因此,旋律是一個具有一定表現力的獨立的聲部④。該交響詩有三種主要的旋律因素: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當然,這其中還包含了一些別的旋律因素,如木管弦樂合奏旋律(第54至57小節)等。該曲旋律的最大特色在于旋律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與自相似性的特點。所謂自相似性,即分形中不同層次上的局部與整體的相似⑤。
二、旋律的形態肌理
該交響詩整體旋律的結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其中,開頭部分(第1至18小節)和結尾部分(第69至102小節)呈現出三種旋律因素的交替,形成音色橫向對置對比,其中第三部分類似于第一部分的再現旋律。而旋律中部(第18至68小節)只有英國管吹奏的旋律,則類似于中部的展開旋律。
英國管旋律的整體形態為環繞不對稱結構。環繞的旋律形態不僅是指旋律中經常出現的環繞三連音節奏型,而且也是指每一個小樂句的旋律線似乎都圍繞某一軸音進行環繞,產生類似逆行倒影化旋律的變形與異化,從而形成旋律音高的上下平衡。不對稱的旋律結構是指該曲旋律打破傳統方整性的旋律樂句結構。該交響詩旋律內部的不同旋律之間存在平行樂思、平行樂句的關聯。
(一)英國管旋律內部的旋律片段之間的關聯
該曲旋律中不斷運用模進手法,但模進音組的旋律片段并不相鄰。英國管吹奏的第一條旋律(第5至8小節)為該曲的主題旋律。
該旋律可分為兩個旋律片段:動機A與動機B,見譜例1。該曲旋律中多次出現與動機A、 B類似的平行樂思旋律片段,使全曲旋律形成相似性的有機聯系網絡。該曲中平行樂思旋律片段主要是音程結構確定的,其中動機A的確定還包含了節奏因素(因其含三連音節奏型)。因此,旋律中動機A平行樂思的確定要結合音高與節奏兩個因素,而動機B平行樂思的確定只要關注音高即可,見表1:英國館旋律中動機A的行樂思
可見,動機A與動機B的平行樂思在英國管旋律當中出現多次,見圖表2。除個別情況外,每次出現時調性各不相同。此外,一種二度顫音節奏的旋律片段也在旋律中多次出現。該旋律片段最早出現在第25小節,但音程結構關系為小二度,而其后出現的都是大二度顫音關系,這些旋律片段可以理解為動機A的另一種變形,將其稱為動機A變體,見譜例2。
此外,英國管旋律中第五條與第七條旋律也存在音程結構的關聯,只不過出現在旋律的中后部。第五條旋律中第62小節的旋律片段與第七條旋律中第88小節的旋律片段的音程結構關系相似,只有一個音不同。又因英國管第七條旋律與弦樂組全奏旋律(第75至83小節)為相同音高重復關系,故第79小節的旋律片段也與第62小節的旋律片段也為相似關系。由于第62小節這個旋律片段關聯著后幾條旋律,因而可以將其稱為該曲后半部分旋律的一種重要旋律,可以將這個平行樂思稱作樂思C,見譜例3:
可見,除了在英國管七條旋律中前四條旋律關系較為密切,且出現主題旋律的旋律片段較多。除了在開頭出現主題旋律以外,在七條旋律的中間(第四條)也出現大量與主題旋律片段音程結構相同的樂句,使主題旋律的地位得到再一次鞏固。后三條旋律與主題旋律聯系相對較弱,但也有一些關聯,其中第五條與第七條旋律中后部存在新的旋律素材片段的關聯。
(二)英國管旋律與別的樂器旋律的關聯
1.英國管旋律與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的關聯
在英國管的第三條旋律(第18至32小節)中,第23小節(與第28小節旋律的音程結構相同)的旋律材料在英國管旋律中為新出現的旋律素材,是一種琶音式的上行旋律,各音為“A-D-F-A-B-C”,如果將B音省略,構成分解和弦結構:二級小七和弦第二轉位,見譜例4:
但是,第23小節的旋律素材并非憑空出現,而是來源于更早出現于第7至16小節的三條短小的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這三條旋律各音的音程結構大體相同,為小大七和弦第二轉位(加小六度音)的分解和弦,按照從低音到高音的次序排列成旋律。第23、28小節旋律構成的和弦可以理解為是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中分解和弦式旋律線條構成的變體。前后兩個和弦還是高度相似的,首先三和弦都是小三和弦,其次轉位都是第二轉位。因此,英國管第23小節出現的新素材的旋律與第7至16小節的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片段存在音程結構相似的關系。
2.英國管旋律與弦樂木管合奏旋律的關聯
在英國管主旋律中的第五條(第58至67小節)中,第60小節后七拍出現的短小旋律,相鄰兩音的音程關系為大二度,為一種類似顫音的短小樂思,該旋律的出現并非偶然,是采用與第54至57小節弦樂組與木管樂組合奏旋律中的旋律相同的音程結構片段,體現出一種旋律片段音程結構上的模仿,見譜例5。
3.英國管主旋律與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的關聯
除了前面提到的弦樂組齊奏旋律(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中的第79小節的旋律片段與英國管第五條旋律中的第62小節(樂思C)的旋律片段為平行關系以外,英國管第七條旋律基本上完全重復了前面相鄰的弦樂組齊奏旋律(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
在第七條旋律(第82至94小節)當中,除了第92至94小節最后幾個音以外,與第75至83小節弦樂組齊奏旋律(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完全相同,除了尾音以外作了完全的重復。
(三)非英國管旋律的關聯
弦樂組兩種旋律出現在樂曲的開頭和結尾,給人印象深刻,因而對整體旋律的統一性起到鞏固與穩定的作用。弦樂組的兩種旋律因素除個別旋律片段以外,在其內部基本上都是平行的關系,都是相似樂句。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只出現在該交響詩開頭、中后部及尾部,往往與英國管旋律相互應答而出現。雖然它類似于和聲性的旋律線條,但由于水平運動感較為強烈,因而是一種“和聲意義上的旋律⑦”。該旋律為相同和弦結構按固定次序的分解和弦——不同音級下小大七和弦第二轉位的分解和弦,開頭個別旋律在和弦根音基礎上加入小六度音。
因而,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都是相似的關系,只有音域跨度的差別。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共出現四次.除第三次以外,其他三次為平行樂句,皆相似,見圖表3。弦樂組這兩種旋律的平行樂句出現在旋律開頭與結尾,起到了統一整體旋律的作用。
可見,全曲旋律除了開頭與結尾交織在英國管吹奏的旋律當中的弦樂組旋律為平行樂句以外,英國管七條旋律自身、英國管旋律與弦樂組旋律也存在許多旋律片段為平行樂思的關系。
這些平行樂思與平行樂句類似于離調模進的不同音組,只是這些音組分散在不同的旋律位置,在一些地方產生了進一步的變形與變奏。這些平行樂思關聯的旋律也各不相同,且一條旋律可能在一個或幾個不同的位置有一個或幾個平行樂思與別的旋律有聯系,可能是一條,也可能是幾條,且規律性較弱,從而使旋律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有機聯系。這些平行樂句、平行樂思的音程結構相同、節奏相似,只是調性各不相同。
三、旋律的創作手法
(一)主題旋律采用多利亞調式音階
全曲英國管吹奏七條旋律,旋律結構不對稱,有長有短。其中開頭兩條旋律為平行樂句,給人印象深刻。英國管吹奏的第一條旋律出現在第5至8小節,該旋律可以分為兩個樂思:動機A與動機B。前一個樂思為三連音回環式旋律,后一個樂思為上行音階式旋律。見英國管開頭5至8小節旋律,見譜例1。
通過觀察譜例不難發現,這條旋律采用多利亞調式上行音階的形式。動機B為多利亞調式上行音階前五級,而動機A中出現了多利亞調式的五級與六級。多利亞調式的第六級為大六度,稱為多利亞六度。動機A中不僅出現了多利亞六度——小字一組G,且以長音與環繞三連音強調了該音。
從這里可以看出,西貝柳斯在這里刻意采用多利亞調式上行音階的形式寫作主題旋律,且將多利亞調式的調式特性音——“多利亞六度”前置并且以環繞三連音的節奏型予以強調,為了突出該旋律的多利亞調式音程結構。
西貝柳斯使用這種調式音階的主題與其芬蘭民族樂派創作理念有關。芬蘭民歌的最大特點是多利亞小調開頭五個音形成的五音小調音列(比如D-E-F-G-A)。這種五聲音列應用沒有強制性的規定,旋律可以結束在任意音高。有一些芬蘭民歌中出現緊張度較高的地方,會將五音音列擴展到第六音與第七音(比如在前述音列基礎上加上B-C)作為補充。因此,在旋律中運用多利亞調式上行音階排列,是芬蘭民歌的主要特色⑧。
此外,該主題旋律還帶有一些象形的特點。如果將第5至8小節英國管旋律的符頭連接做出一條旋律線,并將該旋律線進一步抽象,可以發現旋律線形態類似“2”這個數字的形態,只是將這個數字逆時針方向旋轉了近45度。這種旋律線形態是對天鵝形態的一種抽象表現,天鵝的形態抽象后就類似“2”這個數字。
所以,該條旋律是對天鵝形象的描繪。《牛津簡明音樂詞典》(第四版)⑨中的“圖內拉的天鵝”詞條,也指出該曲英國管獨奏系描繪天鵝形象。
(二)主題旋律的隱伏級進旋律采用非嚴格的逆行與倒影手法
該曲開頭英國管吹奏的第一條旋律(第5至8小節)的動機A與動機B之間存在一個跳進,然后上行音階式的動機B再反向級進填充。如果在這里采用欣德米特作曲技法中分析級進旋律的方法進行觀察與思考,就會發現該主題旋律的隱伏旋律暗含級進旋律。而這種隱伏的級進旋律采用一種非嚴格的倒影與逆行的旋律發展手法。該隱伏級進旋律旋律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上方為折線形旋律,下方為斜線式旋律。上方旋律各音依次為小字一組G、F、bE、F,下方旋律為小字組bB、小字一組C、bD、bE、F。通過觀察可以發現,降E降這兩條級進旋律分為三個線段,因此降E作為軸音,既是倒影軸也是逆行軸。但是這里的倒影旋律與逆行旋律都是非嚴格的。在這里隱伏級進的非嚴格倒影旋律,體現出西貝柳斯在創作該曲主題旋律時在不規則的形態中尋找的平衡與對稱的旋律寫作思路,見譜例6。
(三)重要旋律采用主題旋律片段的隱形離散形式
該曲英國管第五條旋律中的第62小節旋律片段(樂思C)關聯著樂曲后幾條旋律,因而作為旋律后半部分的重要旋律。從表面上看第62小節的旋律與主題旋律似乎沒什么關聯,其實則不然。如果將第62、63小節連起來看,可以發現當中的幾個音與主題旋律當中的幾個音音程結構關系是相同的,因此第62、63小節的旋律可以理解為是主題旋律的隱形離散形式,見譜例7。第62小節第一個長音與倒數第二個音為小六度關系,而主題旋律中動機A的第一個長音與動機B的第一個音的音程關系為大六度,因而兩者音程關系相似。同時,如果第62小節的結尾兩個音,第63小節的第一、第四兩個音連在一起,這四個音則類似動機B的前四個音的音程結構。這也就是說,第62、63小節的隱伏二度級進旋律與主題旋律中的動機B相似。因此,英國管第五條旋律中第62、63小節的旋律片段采用了主題旋律片段的隱形離散形式。
(四)主題旋律及重要旋律的長音采用三全音進行
該交響詩英國管旋律中有一些時值超過兩拍的長音。這些長音在演奏時給人印象深刻,因而作為一種主干音,決定著旋律的大致走向。英國管第一條旋律(第5至8小節)的長音分別為小字一組G、小字一組降D、小字一組F。旋律大致走向為從小字一組G到小字一組降D,最后再到小字一組F,詳見譜例1。通過觀察樂譜可以發現,英國管旋律中相鄰長音之間的關系為増四減五度,而不同旋律之間的三全音關系各音內在也有邏輯聯系。第一、二條英國管旋律中的三全音關系各音與第四條旋律第一個三全音關系的各音(六個音)正好構成一個八度的全音階各音。但是,這個全音階的呈現次序卻是由I—IV、II—V、III—VI類似這樣的次序構成,并不是依次呈現的。此外,第四條旋律第二個三全音關系與第七條旋律的三全音關系正好也構成一個八度之內與上述全音階相對的全音階當中的幾個音,但是少了一組三全音關系,見譜例8。
英國管第一、二、四條旋律長音中相鄰的三全音關系的各音中(前音與后音為三全音關系),相鄰前音形成全音級進的特點(小字一組G—A—B),且所有前音和后音正好構成一個八度的全音階。而且重要旋律結構的一些長音之間形成一種增四(減五)度跳進與大三(小六)度跳進交替的全音階的運動軌跡。可見,西貝柳斯在前四條英國管旋律的重要旋律結構中不斷使用三全音關系,恰好構成一個八度的全音階。
可見,前四條旋律中只要出現相鄰長音為三全音關系的各音,該條旋律一定為主題旋律的平行樂句。因為這三組長音為三全音關系的樂句都和動機A與動機B有關,而動機AB結合在一起就是主題旋律。此外,英國管第五、七兩條旋律中的平行旋律——樂思C的相鄰長音中也出現三全音關系。該樂思正好是第五、七兩條旋律的重要關聯,因而可以理解為是一種重要旋律片段。由于這些樂句的旋律片段都是不同旋律之間關聯的平行樂思,所以屬于具有特殊意義的重要旋律。而在這些旋律的相鄰長音使用三全音關系,體現西貝柳斯在重要旋律的運動方向中注重采用三全音的進行。
(五)一些旋律中采用非嚴格擴大變形的倒裝手法
樂曲開頭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及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三種旋律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采用,形成了音色上的橫向對置對比的旋律,對旋律進行了一種色彩性的強調。
其中,第7至9小節大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與9至11小節的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可以看做是第5至8小節英國管吹奏的旋律兩個樂思的非嚴格擴大變形的倒裝形式,是一種展衍性質的旋律。
第7至9小節大提琴與中提琴演奏的分解和弦式上行旋律,為動機B音階式的上行旋律的非嚴格擴大變形旋律。動機B的是即音高依次為小字組bB、小字一組C、bD、bE、F。同時,第7至9小節大提琴與中提琴演奏的旋律為C調降七級小大七和弦第二轉位加小六度音,依次為F、A、bB、bD、bG。通過觀察發現,五音當中有三個音為八度重復,而且這三個音處于動機B的重要位置——bB位于動機B開頭,bD處于該樂思中間,F處于該樂思結尾,且bD與F時值很長,給人深刻印象。進一步思考可知,這三音為多利亞小調一級三和弦,起到一種確定調性色彩的作用。第9至11小節小提琴組演奏一種和弦式的旋律織體,采用短暫的支聲復調橫向化的多線條形式匯聚成一種音流,與前面單線條的旋律形成對比。由于旋律是一個具有一定表現力的獨立的聲部⑩,因而該旋律織體的核心成分為其高聲部旋律及其八度重復,即為第一小提琴組第一、四分部,第二小提琴組第一分部。該旋律可以理解為動機A環繞三連音旋律的非嚴格擴大變形旋律。該旋律為一種半音化的四度波浪型旋律,不僅出現了動機A中的兩個音F、G的八度重復音,而且出現在旋律高點,且音符時值較長。由于其形態與動機A的形態相同都為波浪形旋律,故而可以理解為動機A旋律的擴大變形的形態。類似的旋律還出現在第12至19小節。第12至15小節英國管旋律與第5至8小節相同,就是上移了大二度。
與此同時,弦樂組對應的旋律也上移了大二度。由此可見,這幾條旋律中含有自調性11的結構特征,因而可以理解為是一個整體。
可見,樂曲開頭第5至11小節的旋律結構為ab–B- A, B- A兩個樂句為主題旋律的兩個動機非嚴格擴大變形的倒裝形式。西貝柳斯在創作該曲主題旋律時將英國管吹奏的旋律分為兩個樂思,再由弦樂組樂器由低至高地演奏其擴大變形的兩個旋律片段。弦樂組該旋律是英國管該旋律一種非嚴格的變形,只保留了基本的旋律形態。動機A的擴大化音階的延伸與細化,動機B的擴大化逆行倒影表現在音程結構的變化擴大與織體的變化。因此,B和A是對主題旋律片段ab的變化發展。
(六)一些旋律采用主題旋律片段及其變體的重組與異化
英國管第四條旋律(第36至53小節)由許多小的樂句組成。該條英國管旋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前面兩個小樂句(第36至39小節),中間三個小樂句(第40至48小節)與結尾的樂句(第49至53小節)。這些小樂句大體類似,這些小樂句基本上都由動機A、動機B、動機A變體組合而成,只有個別片段體現出縮減和變形,因而小樂句間的關系為變奏關系。筆者就選取第40至43小節英國管旋律進行分析,這條小樂句又可以分成三個旋律片段:第40、41小節,第42小節,第43小節。通過與三種結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片段一類似動機B(動機A保留了長音,省略了的三連音),片段二類似動機A變體(最早出現于第25小節),片段三類似動機A。因此,這個樂句是前三條英國管旋律中的三個不同樂思的重組,其中動機A變體與動機A、B來源于不同的旋律位置。所以,這些小的樂句體現出主題樂句旋律片段的變形與重組,見譜例9。
英國管第四條旋律的許多小的樂句雖然大體類似,然而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比如,第36、37小節中的上行多利亞調式音階是從第三級開始的,至第七級結束,且第37小節該樂句結尾時也沒有采用動機A的節奏型,而是將三連音節奏型變為八分音符。第38、39小節小樂句中除了將音階織體擴大為琶音織體以外,還將結尾的三連音節奏型變為了小二度顫音節奏型。從第40小節開始至50小節的幾個樂句基本相似,只是調性在不斷上移,并達至高潮,見譜例10。
該曲中的一些旋律片段在出現時節奏形態上不斷發生異化,進而產生新的旋律素材。動機A節奏形態就在不斷發生變化,只要觀察七條英國管旋律的的開頭就可以看出動機A的不斷異化,而動機A變體無疑是動機A進一步異化產生的,見圖表4。
可見,該曲英國管旋律中貫穿一些重要的平行樂思,這些平行樂思可以不斷重組,也可以在發展中不斷地異化,也可以先異化再重組。重組與變形形成的新的旋律素材經過進一步發展又成為一種新的平行樂思,關聯著另外的旋律,從而形成英國管旋律的內在有機聯系。
(七)一些旋律中采用別的旋律片段的局部逆行、倒影的手法
英國管旋律當中差異感最強的第五條旋律,與動機A、動機A變體及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片段及有一定關聯。該旋律采用動機A三連音旋律變體的倒影旋律片段,采用了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片段中倒影(逆行)旋律,及動機A變體的進一步異化。
第59小節第二個音開始的三個音為動機A環繞型三連音樂思的倒影旋律片段,但非三連音的節奏型。第60小節一至三拍,第63小節二至四拍,與第三條旋律中第23、28小節的上行琶音有音程結構上的類似之處(由于第23、28小節音程結構相同,故后面都選擇第23小節做分析,相當于第28小節)。第23小節上行琶音的幾個音分別為“A-D-F-A-B-C”(英國管旋律實際音高低純五度),其中第三、四、六音形成“F-A-C”上行大三和弦,而第60小節第一至三拍為下行大三和弦,因此第60小節第一至三拍為第23小節第三、四、六音的音程結構相同的逆行(倒影)結構,兩者間有類似的關系。第60小節的內容仿佛是對第23小節印象的片段式抽取,并進行空間或時間上的倒置,或類似變化。同樣的,第63小節二至四拍為純四度加大二度構成的上行的三個音,而第23小節上行琶音 “A-D-F-A-B-C”,第三、五、六三個音形成的增四度加小二度音程結構與前者有類似之處,都是四度加二度構成的三個音。因此第63小節二至四拍是第23小節第三、五、六三個音的音程結構的變體,與其類似。第63小節的內容仿佛是對第23小節內容的片段式的抽取,并進行空間或時間上的變形,或類似變化,見譜例11。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59小節的旋律片段來源于動機A的局部倒影,第60、63小節的旋律片段的音程結構來源于第23小節(或第28小節),而前面分析過第23小節的旋律結構是以大提琴為主的上行分解和弦式結構的借鑒(來源于第7至16小節),形成該音程結構片段的倒影或逆行的音程結構的旋律片段。第60、63小節的旋律結構的變形與倒置體現為該音程結構的進一步變化。第60小節后七拍出現的旋律結構來自于弦樂木管樂旋律,也是動機A變體的變體。因此,差異感較強的第五條旋律也與別的旋律有所關聯。
(八)整體旋律采用固定調式下頻繁離調的手法
該交響詩的不同旋律因素采用固定的調式,而由不同旋律因素交織在一起的整體旋律則采用頻繁離調手法,導致調性多變,調性色彩豐富。該交響曲的調式調性的確定不僅根據旋律片段中出現的音階音級,也根據該曲的和聲進行。因為該曲的和聲進行有一個特點,每次離調都會出現該調式調性的一級和弦,對調式調性進行強調與鞏固。
該曲英國管吹奏的旋律在整個旋律中占很大篇幅,且英國管旋律有其獨特的象征事物,故筆者對其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英國管旋律除了第三條旋律的調式中含有C自然大調以外,其他六條除個別小節外基本上都是多利亞調式,見表5。
整首交響詩旋律中大量出現多利亞調式體現了西貝柳斯既不采用歐洲浪漫主義音樂傳統的大小調調式的旋律,也不采用瓦格納等人高度半音化的旋律,而是采用芬蘭民歌中常用的多利亞調式,體現其旋律在調式方面具有的一定的創新因素。因此,英國管吹奏的旋律中多利亞調式占主導地位。雖然調性變化多樣,但是調式相對穩定。該交響詩中出現了許多變化音,加之出現大量離調和弦,因而調性多變曖昧。而旋律中的變化音是由于該交響詩的旋律寫作時,運用不同調性下的多利亞調式轉調或離調所致。因此,該交響詩旋律采用相同調式下的不同調性來發展旋律。
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是一種分解和弦式的旋律,和弦結構為小大七和弦,如果使盡量多的音落在自然音級上,就是以根音為主音的和聲小調,這樣該和弦式旋律的調式調性就產生了。樂曲開頭出現的三條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調性為半音級進關系,而樂曲中后部出現的該旋律為調性相同。除上述旋律之外,該交響詩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共出現四次。其中,第三次為弦樂組齊奏(低音提琴除外),有三個小樂句。小提琴旋律每一次出現時,調性都在發生變化。雖然該旋律調性多變,但調式卻穩定統一,大體為旋律小調的調式。
小提琴旋律的調性變化規律為四度上行變化規律,類似于和聲進行中的強進行。小提琴旋律的結構為非結構性擴充的平行樂句。在這里,旋律及其調性變化屬于上行四度的移調模進。這種轉調手法類似于平行和弦的四度上行進行,只不過當中有間隔。從小提琴旋律調性變化來看,它屬于一種獨立的旋律,有其內在結構,見圖表6。
可見,全曲旋律當中除了B調的相關調式(主要是小調)沒有出現以外,在十二個調性當中大致出現了十一個調性,且大多都是以小調調式形態出現的。因此,旋律的調性非常豐富。其中,樂曲前大半部分幾乎每個小樂句的調性都發生變化,調性豐富多變,且相鄰樂句調號都不是相鄰的;樂曲的后小半部分調性相對穩定,偶爾出現變化,且相鄰樂句基本上都是近關系轉調,轉調中采用屬調與下屬調。
(九)旋律音色采用多重結構的手法
整體旋律結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中,開頭部分(第1至18小節)和結尾部分(第69至102小節)呈現三種音色的旋律織體的交替出現,形成音色橫向對置對比,第三部分音色布局類似于第一部分的變化重復。而旋律中部(第18至68小節)只有英國管吹奏的旋律,類似于三段式的中段。具體來看,從樂曲開頭第1至18小節,三種旋律因素相互交織,分別為“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
因而,其旋律結構為“A—B—C—B1—A1—B2—C2”。第18小節至68小節旋律主要由英國管吹奏。第69小節至結尾與開頭類似,又出現三種旋律因素的交織,分別為“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弦樂器分八度齊奏)—英國管旋律—小提琴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 因而,其旋律結構為“A—B—C—A1—C1—B2”。可見,樂曲開頭及結尾三種音色的旋律之間形成一種復雜的結構關系,見圖表7。
該曲開頭與結尾旋律的音色變化大致呈現在三分性結構上的二分性結構,其中開頭中間還形成了回旋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開頭與結尾都由拱形結構與一個另外的結構成分構成,恰好形成一種“結構逆行”的結構對位。旋律的音色結構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因為第三次出現的小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與其他三次反差較大,也可以認為是別的音色旋律織體。小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的音色可分為近乎弦樂器全奏(第75至83小節)和部分弦樂器演奏兩種。大提琴器相關樂器旋律可分為混合音色與純音色(第98至102小節)兩種,或者從旋律橫跨的音域范圍來看分為超不超過三個八度分為兩種。
另外,弦樂木管樂合奏旋律(第54至57小節)也可以認為是另一種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而第70至74小節的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也可以認為是另一種弦樂木管樂合奏旋律。可見,該曲的音色劃分標準并不統一,從不同角度看音色的搭配與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分類標準去劃分,形成不同的結構。
四、旋律的配器音色
在該交響詩總譜的標題文字為“圖奧內拉,死亡的帝國,芬蘭神話中的冥府,被一條黑色的寬廣河流包圍著,河水湍急地流動,來自圖奧內拉的宏偉天鵝,莊嚴地在河面上緩緩游動并引吭高歌。”該曲的英國管旋律主要表現天鵝的哀鳴歌聲(也象征天鵝形象),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主要表現天鵝橫穿水面游動,而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旋律主要表現河水波浪型的起伏及給人帶來的感受性因素12。該交響詩旋律的配器采用音色作為結構性的手段,使用樂器音色的自然貼切,充分考了標題文字中描繪的氣氛的渲染、樂器間的音色對比與融合、樂器演奏的音域范圍等因素。
(一)音色基調
西貝柳斯在該曲采用英國管獨奏恰當地表現天鵝的歌聲與形象,且起到渲染全曲音色的作用。柴可夫斯基在《天鵝湖》“場景音樂”中用雙簧管來描繪天鵝的形象,而英國管長度較雙簧管更長,仿佛圖奧內拉神圣天鵝的長頸。因而,在該曲中采用雙簧管同族樂器英國管來描繪圖奧內拉天鵝是非常貼切的。英國管音色低沉深沉濃郁,和雙簧管比較起來更加柔和飽滿,鼻音較重,擅長表現陰郁、深沉的情緒。全曲使用英國管獨奏不僅準確地渲染了芬蘭冥府圖奧內拉的陰郁的氣氛,而且該音色與黑水河顏色也是吻合的。英國管配器較為突出的曲目,如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第二樂章中有英國管的主題(歌曲《念故鄉》的旋律)。但該樂章主題也并非只采用英國管進行獨奏。可見,該曲中主旋律采用英國管獨奏的配器手法并不多見。這種使一件木管樂器的獨奏貫穿在在整首交響詩中的配器手法,類似于木管樂器的協奏曲。
(二)音色頻率
作曲家在該曲開頭與中后部采用音色的橫向對置對比描繪一幅動態的畫面。該曲開頭與中后部的旋律由英國管、大提琴及相關弦樂器、小提琴及相關弦樂器交替演奏,不同音色旋律的旋律代表不同事物,這些事物在不斷地運動、變化。
具體來看,從樂曲開頭至第18小節,三種旋律因素交替出現,相互交織,分別為“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第18小節至68小節旋律主要由英國管吹奏。第69小節至結尾與開頭類似,又出現三種旋律因素的交織,分別為“英國管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小提琴旋律(弦樂器分八度齊奏)—英國管旋律—小提琴旋律—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因此,該曲開頭與中后部通過多種音色的變化對旋律本身進行了樂器音色的色彩性強調,從而強化突出了旋律。同時,該曲開頭與中后部音色的多變反映出其音色頻率變化較快,表現一種不穩定的情緒與情景。
因此,筆者認為這種音色的橫向對置對比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一副動態的畫面——天鵝在湍急的河水上游動并引吭高歌的情景,形象的表現了標題文字的內容。
(三)樂器音域
在該曲中,作曲家采用大提琴及相關樂器音色的轉接充分考慮到樂器演奏的合適音域范圍及細微的音色變化。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出現在該曲開頭、中后部和結尾部分,它是在弦樂組聲部出現一種緩緩上行的旋律線條,基本上以三度以內的級進與小跳進為主。該旋律的節奏類似天鵝橫穿水面緩緩游動的節奏。由于天鵝可以順水流移動,這里的游動可以理解為是天鵝主動刻意的行為。在樂曲開頭,弦樂組樂器的選擇與適合本樂器演奏的音域范圍密切相關,目的是為了演奏出一種較為柔和、舒展的音色,而不是緊張生澀的音色。這種音色特點使人不僅聯想到天鵝優雅的身姿與游動。比如,第7至第9小節的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音域超過三個八度,由大提琴聲部與中提琴聲部共同完成。之所以采用兩件樂器轉接,是因為大提琴在高音區音色略顯生硬,轉接到中提琴則音色相對柔和。這種手法使音色過渡顯得較為自然,屬于同性質音響元素的轉接。
值得一提的是,在樂曲尾部出現的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第98至102小節)使用了大提琴獨奏,采用純音色的手法。該旋律音域跨度較大,大提琴在中低音區時較為自然,而在高音區音色則較為生硬,暗示著天鵝游動時略帶的一種緊張惶恐的情緒,從而對圖奧內拉環境氛圍的又一次進行了暗示。可見,樂曲的音色與需要表現的內容密切相關。
此外,縱觀全曲可以發現該交響詩的配器非常類似印象派繪畫中的原色并列的手法——在一種純凈的原色音色背景之下,另一種原色色調只有一些小的變化及一摻雜些不多的別的音色。該曲的配器體現出一種注重純音色的手法,使英國管獨奏的音色成為全曲的音色基調。英國管旋律類似一種原色,而弦樂組演奏旋律及伴奏有類似另一種原色。如果將英國管音色描繪成藍色,弦樂組音色描繪成黃色,全曲的色彩就類似文森特.梵高的《麥田里的烏鴉》這幅油畫的色彩布局。
五、旋律的美學意蘊
該交響詩的旋律三種因素主要由英國管與不同弦樂器演奏,由于英國管與弦樂器的音色分離度較大,因而英國管旋律的音色就顯得非常突出。正是由于這種配器音色上的對比,突出了英國管旋律,似乎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聲部。因此,英國管的旋律成為該交響詩中令人最為關注的因素。從前面分析的英國管旋律的創作手法中,可以隱隱地感受到該旋律中有豐富的美學文化內涵。
(一)繁衍生長現象
英國管旋律的發展含有自然界細胞等有機物繁衍生長的現象特點,主要包括分裂聚集式生長與關聯融合式生長13。分裂聚集式生長的過程體現在英國管旋律異化的過程中將先某種樂匯分裂出來,再將不同樂匯聚集,進行有機重組并異化發展。分裂與聚集是一種辨證發展的思維,前四條旋律就體現為一種這樣一種分裂聚集式生長的過程。將第三條旋律中音程結構分裂出來,與第一條旋律(或第二條旋律)進行重組,形成第四條旋律中的小樂句。然后,通過不斷地調性變化,該小樂句不斷的變化重復,構成第四條大樂句。
總之,英國管第四條旋律中旋律的音程結構來源于主題旋律片段的音程結構。關聯融合式生長的過程體現在英國管旋律異化的過程中將外在于該旋律的其他旋律的音程結構片段納入英國管旋律之中形成類似或相同的音程結構,然后再異化生長的旋律生長過程,第三條旋律與第五條旋律就體現這種異化的過程。英國管第三條旋律采用與前面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相似的音程結構片段上,而第五條則采用前面弦樂、木管組合奏旋律的音程結構。
(二)意識流現象
西貝柳斯的一些作品中蘊含了20世紀結構主義哲學的思想14,主要體現為發生學結構主義15(流動的結構論)。該思想把對象看為一種在時間中產生并變化發展的結構,經歷由簡單結構為基礎逐漸構成復雜結構、最后到整體結構的過程。結構主義通常強調其共時性,而發生學結構主義卻從歷時性角度探討了結構主義。該曲英國管旋律片段對其他旋律片段的模仿主要表現在使用一種音程結構相同的短小旋律片段。
一些旋律片段在旋律流動中雖然具體音高與調性發生變化,但是音程結構卻保持一致,體現出一種結構性:音程結構片段是一個統一體,體現了整體性;音與音是音程結構中的音,通過一定音程能相互轉換體現了轉換性;如果音程中的一個音發生變化,那么另外的音為了保持相同的音程結構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體現出一種自調性。因此,英國管旋律中的短小片段的固定音程結構(主題旋律的動機片段)體現了結構的整體性、轉換性與自調性16三大特點。
19世紀8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在其論文與著作中提出了“意識流”這個概念。意識流寫作是作者主觀的心理活動,因此意識流寫作中作者對故事主人公心理活動的描寫,體現為主觀的“主觀”,即結構的綿延17(即某種音程結構在樂曲中連續出現)。在寫作手法上體現為內心獨白與自由聯想。而對外界的人、事、物及一些模棱兩可的過渡的心理狀態的敘述為主觀的“客觀”,即綿延的結構18(即多重宏觀結構),體現為不同的人、事、物在意識之中不斷流動形成的整體結構。意識流小說中經常描寫主人公處于某個情境(空間)下開始自由聯想,不同的世界、不同空間的對象則紛至沓來,這種現象就與樂曲的多重結構現象類似。一個結構可以由更小的結構構成,也可以去構成一個更大的結構,這點與空間的性質類似,因此該曲的某種整體結構可認為是一個空間或一個世界。全曲不同劃分標準下的多重的二分性與三分性結構相互滲透可以認為是不同空間的相互交融。因此,小的片段旋律結構可認為是事物、對象,大的整體旋律結構則是空間、世界。
該曲英國管七條旋律統一于多利亞調式,特別是當中出現了一些多利亞調式的上行音階,就類似主觀的“主觀”。從更大范圍看,主題旋律的片段形成的樂思(動機A、B及動機A、B的變體)都可認為是主觀的“主觀”。該交響詩旋律中出現的動機A、B及其平行樂思在英國管吹奏的前四段旋律中反復出現,類似某種濃烈的情感反復縈繞內心,反映一種主觀上情感的強烈與糾結。此外,動機A、B的變體由于和動機A、B類似,即統攝于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就類似于小說中對主人公的內心活動的描寫,即意識流小說中采用的內心獨白的手法。
(三)延異現象
德里達的“延異19”并非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延異是不斷用符號代替存在,但是主觀思想無法完全達到客觀現實(這是基于主觀、客觀平行的理論),所以這種符號代替永不能達到存在,只能無窮的運動——永遠想成為“是”,但永遠也無法“是”;近似于“是”,但始終不是“是”。一個符號產生,表面上代替了存在,但由于它不是存在(只是意識中的符號),故而只能被另外一個符號取代。由于人的意識本性就是不斷要為現象賦予意義與命名,于是就不斷有符號產生,但是又由于該符號與存在之間的差異,又不斷被否定,這種差異是大寫的差異。因此,一個符號產生隨即馬上又被另外的符號否定其自身,由能指向能指不斷運動,四散游走,無休無止,始終處于“是”與“不是”之間懸而未決的狀態——無法完全命名某個存在。說白了,延異就類似于想表述某個對象但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匯表達的“語滯”狀態,類似于“既不…,又不…”的不斷否定的語句,一直想尋求一個“是”,可是永遠無法成為,無法真正在場。所謂“是”就是在延異的過程中把握了蹤跡的蹤跡(類似一種函數形式),產生一種在場的幻覺。而延異的符號跡化如果毫無規律,則其無法在場,但又不是完全的不在場——“不是”。一方面,“ 不是”是對“是”的否定與“是”處于兩個極點,而延異處于“是”與“不是”之間的過渡地帶;另一方面,“是”與“不是”又是延異的一種特殊狀態。因此,延異包含了全部。德里達的“能指”或是聲音的、物理的現象,而“所指”是指書寫的意義,并非指向真正的存在也無法指向真正的存在,指向的只是存在于主觀的符號——意義。由于聲音的現象與書寫的意義都可以被認為是能指,因而“能指”只能是不斷地指向另一個“能指”。
該曲從宏觀到微觀呈現出多重結構,特別是動機A、B的平行旋律片段及其變體,其他旋律的平行旋律片段及變體,甚至變體的變體,都可以作為一種劃分標準,來劃分旋律的結構。由于其他旋律片段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動機A、B有一定關聯(類似),因而可以認為是動機的無窮變奏中的某一個層次。這些類似的旋律可以成為一種結構劃分的標準。但是由于劃分標準牽涉到幾個不同的音樂要素(如音色、調式調性等),因而呈現出不同的結構。這就導致了該曲的結構在每種結構元素及劃分標準下具有多解性,而這種結構的多解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解構主義的思想。該交響詩結構上的這種多解性,多重性與滲透性,類似后結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提出的“潛結構(infrastructure)20”現象(即結構成分的延異形成的非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結構)。從結構主義哲學的視角來看,能指就是一種結構。能指與能指的區分,體現為結構與結構的區分。
因此,該曲多重結構之間的統一性、滲透性與多解性,又仿佛是由“能指”指向“能指”的無窮運動的現象。能指不指向所指而是不斷指向能指,體現出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哲學中的“延異”現象。因此,該曲中多解性的多重結構的音樂現象類似德里達提出的“延異”的現象。
一種結構元素通常只和一種音樂要素相關聯,這樣劃分的結構就比較穩定。但該曲中結構元素與音樂要素關系較為曖昧,一種結構元素有時出現與兩種或幾種不同步的音樂要素相互牽扯、關聯。這導致該曲中一些結構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構了——根據這種結構要素劃分的音樂片段形成的結構并不絕對,但根據其中一種確定的音樂要素劃分的音樂片段形成結構的內在關聯出現局部不緊密的特點。
比如,第三次小提琴與相關樂器旋律從音高、節奏角度來看與第一、二、四次差異較大,但是從開頭與結尾音色布局、調式調性的角度來看卻與第一、四兩次聯系緊密。該曲中兩種或多種音樂要素形成的結構要素,有主導要素與非主導要素之分。這些音樂要素還可以與別的音樂要素結合,形成結構力較弱的結構劃分。另外,劃分標準的多樣化與劃分點的不同選擇也影響到該曲結構的形成。這就是該曲在結構上的多解性的原因。正是這種特點使得該曲在具有結構特點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解構特點——介于結構和非結構之間,統一了結構與非結構。
因此,該曲既有一種較強的結構力,但是這種結構力又被一些因素轉化了,產生不同層次的結構力,形成一種曖昧的結構現象。由此可見,在該曲中不僅憑借各種結構元素或音樂要素形成不同的結構,這些不同的結構之間也有一種指向的運動——由較強的結構力的結構向較弱結構力的結構運動。
值得一提的是,解構主義音樂大量出現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包含偶然音樂、環境音樂、概念音樂與行為主義音樂21。這些音樂的創作是受到解構主義美學思潮的影響產生的。而該曲中的多重結構及結構的的多解性,表現了結構之間的無窮運動,形成類似“能指鏈”的“結構鏈”,類似一種延異的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該曲體現了解構主義美學的審美理念,而只是音樂結構形成的現象與“延異”現象有一定的類似。因此,該曲中體現的延異現象是一種溫和的延異現象,而并非極端的延異現象。
六、旋律的獨有特質
晚期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大師瓦格納名噪一時,他的音樂作品中會采用“無終旋律”寫作手法。瓦格納在其1860年一篇論文“未來的音樂”(Zukunftsmusik)提出“無終旋律”這個名詞。瓦格納的無終旋律至少包含三個特點:旋律的對位化、和聲的無終化、結構的貫穿化22。雖然從表面上看,交響詩《圖奧內拉的天鵝》的旋律形態不規則,帶有半音化的特點類似于瓦格納的無終旋律,但是它與無終旋律還是有很大的區別。首先,該曲旋律使用主調音樂形式,采用單線條的旋律線。雖然弦樂組偶爾出現和聲性的旋律形式,但也是有其主要聲部的。其次,該曲的前半段出現大量離調和弦,但是后半段和聲卻相對穩定。即使樂曲前半部分使用不協和和弦,也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不斷出現轉調后該調式調性的一級和弦,如果轉調較明顯,還會圍繞這個和弦產生和聲進行。后半段和聲穩定使樂曲的調式調性相對明確。再次,其結構大體上為再現的三段式,這種結構也是較為傳統的。最后,該曲主要旋律英國管旋律中大量使用多利亞上行音階與多利亞調式,而不像瓦格納那樣在旋律進行中大量采用半音化。西貝柳斯這種創作手法體現了旋律中不規則中的規則,深刻的表現了西貝柳斯芬蘭民族樂派的音樂理念。
法國印象派大師德彪西開創了印象派音樂并將之發展至頂峰。印象派的音樂注重和聲、織體與配器等方面的因素,而在旋律的處理上是淡化的。德彪西的旋律創作特點可以概括為經常運用經過截短、縮聚的短句旋律,隨處是不對稱的短小旋律片段與音型化的織體,追求旋律的隨意性與模糊性23。從表面上看,德彪西旋律創作中的不對稱性、隨意性與該曲旋律創作頗有相似之處。但是,該曲旋律中出現悠長如歌的旋律線條,且該曲旋律創作是非常強調主題旋律動機片段及其旋律片段的發展的。這些特點都與德彪西印象派音樂的旋律創作特點是迥然不同的。
七、結語
交響詩《圖奧內拉的天鵝》的旋律創作堪稱經典。該交響詩旋律的最大特點就是將主題旋律分解為兩個動機旋律片段,再將旋律片段由淺入深進行各種異化變形,且將原型旋律及異化變形的旋律片段不規則地使用在旋律的異化發展中。但是,這種不規則當中似乎又有點規則,由規則到不規則也有若干層次。因此,該交響詩的旋律可以理解為將主題旋律兩個旋律片段進行無窮變奏(變形),且規則性較弱地平行出現在不斷異化對比的旋律當中。在旋律運動進行中,主題旋律片段相鄰的主干音非常有規律地向著其三全音的方向運動。該曲旋律充分反映出曲作者更關注旋律片段,體現出其片段化的旋律寫作思維。從調式調性角度看,該曲中每種旋律因素的調式相對統一,而調性卻豐富多變。該曲的前一大半旋律幾乎每個樂句都進行遠關系轉調,而后一小半旋律的樂句調性相對較穩定,呈現為近關系轉調。因此,旋律前后的調性變化呈現出差異——前半段轉調頻繁,后半段調性變化相對穩定。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出西貝柳斯在創作該曲旋律的同時不僅追求旋律在某種創作規則下不斷變化,而且追求創作規則自身的變化——異化由淺入深的在不同層次上發生。因此,這種旋律創作蘊含一種生成性的創作思維。但是,縱觀全曲又可以發現,不論旋律片段的音程結構還是英國管旋律調式都一致地統一于多利亞調式,因此多利亞調式作為全曲的核心調式。這種調式既非歐洲浪漫主義音樂傳統的大小調體系,也非歐洲晚期浪漫主義時期高度半音化的旋律體系,而是采用了芬蘭民族調式多利亞調式與其他一些中古調式在不同調性下形成的半音體系。以多利亞調式為核心充分體現作曲家西貝柳斯的芬蘭民族樂派的創作理念。可見,該曲注重旋律的橫向延展,在旋律的進行發展中采用了獨特的手法。因此,該交響詩的旋律為主調音樂旋律創作的一個經典獨特的作品。
深入來看,該曲的旋律結構非常有特色。該曲前半部分和聲進行中出現大量的離調意外進行,并沒有明顯的屬功能終止,且樂曲的后半段呈現為靜態和聲。從和聲角度看該曲可以理解為一體化的結構特點,因而旋律自身的結構就凸現出來并顯得尤為重要。在旋律的結構劃分中,相似或重復的旋律片段往往是一種重要的結構劃分標準。因此,某段旋律的相似或重復往往涉及結構的劃分。動機A、B以平行樂思的形式在樂曲中多次出現,且有隱伏出現(第62、63小節)。根據混沌與分形理論,音樂作品中無論產生什么樣的變化其實都是對初始條件完整或不完整的映射24。因此,該曲旋律的其他部分或多或少都可認為與動機A、B存在某種關聯——有些是旋律片段與整體的相似,有些是旋律片段之間的相似。比如,動機A與第9至11小節小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動機B與第7至9小節大提琴及相關樂器旋律,在形態上有一定的自相似性。所謂自相似性即分形中不同層次上的局部與整體的相似25。可見,樂曲開頭的三種音色形成的主題旋律中就形成了一種自相似性。由于該曲中動機A、B的平行樂思有時不是同時出現的,因而兩個動機在具有一定聯合性的同時也具有一種獨立性,可以形成不同的結構劃分標準。如果將動機A及其平行樂思作為一種標準,全曲旋律則呈現出一種結構,同樣也可將動機B及其平行樂思作為一種劃分標準進行劃分。該曲旋律中除動機A、B外還有許多旋律片段具有相似性。這些旋律片段也可以作為結構劃分標準,就是結構力較為薄弱。因此,該曲旋律可認為是動機A、B的平行旋律或者其他重要旋律片段的平行旋律或變體構成,且變體有不同的層次之分。音樂中的確定性因素為動機AB及其平行旋律,具有相似性;音樂中的不確定因素為動機AB的不同層次的變體,具有自相似性。
該曲由于英國管旋律在該曲旋律中所占比重較大,又因其音色較為獨特,可將英國管吹奏的旋律作為獨立的一個部分。從旋律中直接出現重復或平行的角度來劃分,英國管旋律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兩條旋律(第1至18小節),后五條旋律(第18至102小節)。進一步,從動機A及其平行旋律的出現的角度來劃分,全曲可分為兩個部分:英國管吹奏的前四條旋律(第1至57小節),英國管吹奏的后三條旋律(第58至102小節)。前者大量出現動機A及其平行樂思,而后者則沒有出現。更進一步,如果從動機A平行樂思及其某種變體出現的角度來看,可能又出現別的二分性結構。由于變體有多種層次之分,所以形成的結構也是多樣化的。有一些結構力較強,有一些則較弱。動機B與其他旋律片段的劃分與此類似。由于旋律中相同層次的變體可以作為一種劃分標準,且旋律片段的變體有不同層次,加之對變體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全曲旋律可以呈現出根據旋律片段的平行與不同層次的變體劃分的多解性結構。音樂作品可以認為是一種非線性動力系統,具有一定的混沌狀態。在理想的狀態下,混沌狀態具有無窮的內部結構26,比如曼德布羅特集。可見,該曲旋律類似一種相對較為理想的混沌狀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解性的結構特點。分析至此,筆者認為西貝柳斯這種具有高度自相似性的旋律線條來自西貝柳斯對芬蘭大自然中線條(比如芬蘭海岸線)的感悟。
注釋:
①賀春華.西方交響音樂賞析[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
②大衛.伯奈特,詹姆斯.偉大的西方音樂家傳記叢書.西貝柳斯[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09):35.
③繆天瑞.音樂百科詞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10).
④瑪采爾,孫靜云(譯).論旋律[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12):9.
⑤姜萬通.混沌.分形與音樂[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05):80.
⑥“Jean Sibelius Orchesterwerke”,“Der Schwan von Tuonela”[Z](Legende a.d. Finnischen Volksepos,“Kalevala”,OP.22 Nr.3.).Leipzig:Breitkopf & H?rtel,1901: Plate K.F.W.48.
⑦恩斯特.托赫,顧耀明(譯).旋律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12):80.
⑧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2004-1.“Jean·Sibelius”
⑨邁克爾·肯尼迪等.牛津簡明音樂詞典(第四版)[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09).
⑩瑪采爾,孫靜云(譯).論旋律[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58(12):9.
11賈達群.結構詩學:關于音樂結構若干問題的討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07).
12沈旋,等.西方音樂史簡編[M].上海:音樂出版社,1999(05).
13孫宇超.自然繁衍生生不息——解析西貝柳斯交響曲中的衍生思維[J].音樂生活,2013(12):85-89.
14魏楠妮.西貝柳斯作品中的北歐風情[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2:43.
15劉放桐,等.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06):424-425.
16賈達群.結構詩學:關于音樂結構若干問題的討論[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07):20-23.
17王澍.德彪西音樂中的意識流現象初探[D].上海:上海音樂學院, 2005:30.
18王澍.德彪西音樂中的意識流現象初探[D].上海:上海音樂學院,2005:31.
19J.德里達,張弘.延異[J].哲學譯叢,1993(03):42-51.
20劉放桐等.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06):431-432.
21宋瑾.解構主義音樂美學思想[J].音樂探索,2011(03):41.
22陳鴻鐸.試論瓦格納的無終旋律[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02):9-16+86.
23錢智凌.探索德彪西音樂中的夢幻意境——對旋律、和聲、節奏、配器與音色、踏板運用分析[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9-4):90-92.
24姜萬通.混沌.分形與音樂[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05):98.
25姜萬通.混沌.分形與音樂[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05):80.
26姜萬通.混沌.分形與音樂[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5(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