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足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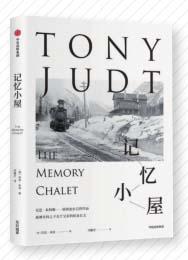
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錮在輪椅上,下半身已經(jīng)癱瘓。從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對(duì)他來說都成了嚴(yán)酷的考驗(yàn)。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車歲月結(jié)束了。“我的病最讓人沮喪的事情是,”他寫道,“我意識(shí)到自己從此再也不能乘火車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媽媽考慮把骨灰撒在兩個(gè)地方:拉特蘭和繆倫。但他們擔(dān)心,我們也許會(huì)賣掉拉特蘭的房子,畢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經(jīng)把他的偏好公之于眾。“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啟程,卻可以選擇于何處結(jié)尾,”他寫道,“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diǎn),就這樣一直坐下去。”
火車對(duì)爸爸來說是一切的解毒劑,正如他認(rèn)為火車對(duì)我們也意味著如此。“如果我們失去了鐵路……我們就忘記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鐵路,他就忘記了如何獨(dú)自生活。“當(dāng)然,我本應(yīng)該孤獨(dú)地體驗(yàn)鐵路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gè)悖論。”他曾這樣推測。
爸爸沉溺于虛構(gòu)的繆倫和虛構(gòu)的拉特蘭,如此他違反了自己最基本的準(zhǔn)則,即我們有責(zé)任了解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的歷史。檢視它們的過去,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繆倫成了一處優(yōu)美的監(jiān)獄,拉特蘭成了她前身的陰影。如果這些小鎮(zhèn)及其火車沒有任何歷史,那么它們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懷舊之情主宰了美國大選,這可能是一個(gè)簡單但有用的提醒:拒絕承認(rèn)某地的歷史會(huì)招致對(duì)此地現(xiàn)狀的錯(cuò)誤觀點(diǎn)。)
我父親把拉特蘭和繆倫視作免疫于歷史潮流的地點(diǎn),除此之外,他沒有再寫到過這兩地。這個(gè)決定不是純粹而簡單的否認(rèn),也不是一種道德矛盾。對(duì)爸爸來說,歷史是一項(xiàng)鑒別性的技藝,其中必須有一種值得認(rèn)真對(duì)待的張力,而在現(xiàn)代歐洲的宏大圖景中,繆倫或拉特蘭看起來似乎毫無問題。“那里甚至沒有過不對(duì)勁。”他寫道。
但是,我覺得爸爸這一拒絕背后有更多的東西。他理解歷史可以多強(qiáng)大。檔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時(shí)所實(shí)踐的專業(yè)化歷史,以及我爸爸踐行和相信的歷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現(xiàn),既沒有清晰的歷史發(fā)展感,也沒有為迷思制造提供足夠的空間。檔案能夠擊碎懷舊之情和多數(shù)人的記憶。在顯而易見的益處之下,還有一些遺憾的不可更改的東西。我們可以修改歷史,歷史學(xué)家也常常這么做。但是撤銷歷史,收回我們知道曾經(jīng)存在的歷史,這要難得多了。
我打算寫這篇文章是因?yàn)椋蚁胫牢野职质侨绾伟l(fā)現(xiàn)了這兩個(gè)小鎮(zhèn),它們遠(yuǎn)隔重洋,唯一的聯(lián)系就是他的所愛——火車與它們的關(guān)系。為了回答這個(gè)問題,我本能地轉(zhuǎn)向檔案。這種本能來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蘭和繆倫這兩個(gè)原始的迷思,留給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