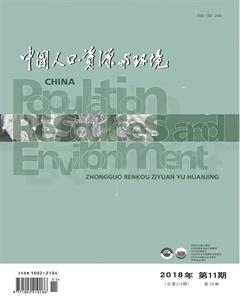土地制度安排與半城鎮化問題研究:分野、論爭及引申
朱要龍
摘要 以城市融入為主導的城鎮化學術主張,不斷成為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然而伴隨城市戶籍改革的持續深化與相關障礙的逐步掃清,“半城鎮化”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因此,重新審視半城鎮化問題的發生機制,是一個值得關切的議題。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存在兩個典型事實:城市建設的規模偏向、農村人口的永久性遷移與制度性遷移分化,均明確指向現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基于文獻研究,本文凝練概括了兩大經驗假說:農村地權退出與土地財政沖動,并力圖統一于一個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內,以尋求半城鎮化的發生機制。現行土地制度以城市征用地制度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行為提供制度庇護,同時,以村集體所有權配置土地權利,無法為農村人口的土地財產權實現提供制度通道。當前,關于土地制度與半城鎮化關系及改革方向,出現了三類分歧:土地制度優勢論認為半城鎮化是制度運行的理想結果,土地制度扭曲論認為要重構土地私權;穩健的改革論認為關鍵是提防城鎮化中的土地私有化陷阱與重構利益分配機制。本文分析認為,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內,“半城鎮化”問題是農村人口微觀行動策略與地方政府宏觀政策選擇共同的合意均衡。半城鎮化向徹底城鎮化的轉型建設,不能以互相割裂的改革方案替代。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議題是農地制度改革,國家關于農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公權之上重塑私權,即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地位不動搖,并逐漸向追求效率的經濟功能與賦予權利的保護功能讓渡,將人地依附關系轉向人地保障關系。制度建設要允許偏遠農村人口將退地后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作為流動資產,可以有償進行轉讓;要探索帶“地標”城鎮化方案,以構建建設用地指標物權化機制。一則糾正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沖動與錯配支持,二則賦予進城農民的土地退出權或市場化收益權。改革理想狀態是,地方政府與非屬地進城農民建立起激勵相容機制,以走出地方政府增長選擇與農民損失厭惡的博弈困局,實現半城鎮化到完全城鎮化的轉型。
關鍵詞 土地制度安排;半城鎮化;兩大假說;分歧與進展;評述與思考
中圖分類號 F2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8)11-0029-08 DOI:1012062/cpre20180705
在經濟新常態的現實語境下,中國城鎮化的發展,無論是在學術呼吁還是政策設計上,均被寄予了推動經濟轉型增長的厚望。然而,中國的城鎮化道路卻遭遇了“半城鎮化”困局,一個既不能完全從農村、農業中“非農化”退出,也不能完全“市民化”融入的“城鄉兩棲式”人口遷移模式[1]。它通常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差測度[2],其經濟學的蘊意是,農村戶籍半城鎮化人口的相對規模比值[3]。由于城市內部按戶籍界定屬地化權利與配置社會福利,戶籍的本源屬性從統計意義異化為身份權。因此,取消“中國特色”戶籍制度成為解決“半城鎮化”問題的關鍵[4],并成為行政共識與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伴隨城市戶籍改革的持續深化與相關障礙的逐步掃清,甚至在相關學者看來,“真正是制度限制而讓農民無法進城的因素已是少之又少了”[5],但是半城鎮化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截止2017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達58.52%,而戶籍城鎮化率僅為42.35%,半城鎮化率為16.17%,粗略估算有2.2億農村人口未能獲得城鎮戶籍。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快速增長的情境下,戶籍城鎮化率卻增速緩慢,乃至于不斷加劇了“半城鎮化”態勢。戶籍功能異化所引致的上層建制改革,以城市融入為主導思路,但是沒有實質性解決半城鎮化問題。因此,重新審視半城鎮化問題的發生機制,是一個值得關切的議題。
1 表征與事實:半城鎮化問題研究無法回避土地制度安排
在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歷程中,兩個重要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第一,城市發展存在規模偏向,在短期內難以糾正。中國城鎮化進程與經濟發展密切關聯,并被綁架于“經濟增長”的邏輯中,突出表現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在官員晉升錦標賽機制與國家GDP主義地誘導下,城鎮化的發展背離了“人本主義”的發展路徑。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慮,通過征地制度安排壟斷土地供給市場,以最大化攫取土地收益為目標,以彰示政治績效而獲得政治晉升機會,由此不斷推動行政主導式的城鎮化。這一城鎮化發展模式,嚴重扭曲了“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的正確價值立場,過度追求城鎮擴張中所釋放的“土地紅利”(土地財政),只強調城市的“向外擴張”,而不注重“向上發展”,即城鎮化發展存在規模偏向。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城市人口增長越快的城市,新建樓房的總樓層數就會越少,建筑容積率就越低,即越傾向于向城市外圍擴張規模[6]。第二,農村人口的永久性遷移與制度性遷移出現嚴重分化,其中,永久性遷移是指農民工行為性的愿意長期留居城市,制度性遷移則是指農民做出戶籍遷移決策[7]。根據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顯示,進城農村人口在留居城市和落戶城市兩個維度的選擇上,呈現出嚴重的分化態勢。超六成流動人口(60.89%)愿意留居城市,僅有9.62%的人口明確表明不選擇長期留居城市;而一旦以落戶為預設前提,僅有37.67%的選擇落戶城市,不愿意落戶率高達31.55%。兩者形成的鮮明對比與強烈反差,凸顯了農民的地權邏輯,這主要表現在進城農民對政府政策的期望選擇上,第一為“穩定的城鎮工作”(33.33%),第二為“保留農地承包權”(28.09%),第三為“保留農村宅基地”(16.48%)[8]。在宏觀農村土地數據層面表現為農村常住人口每年以1.6%的速度減少,但宅基地卻以1%的速度增長[9]。此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伴隨城鄉利益格局重塑,依附于農村戶籍的土地紅利日益顯現[10]。由于農村戶口與農村土地關系被捆綁在一起,顯然,農民進城的一個理性算計結果就是以農民身份留居城市。這一現象折射出農民群體共同的價值判斷與行動取向。
基于上述兩個重要事實,無論是地方政府基于政治績效所推動的土地城鎮化(規模偏向)沖動與目標激勵,還是進城農民基于理性算計,企劃以“城市-鄉村”之間的“流而不退”來主張農地權利;諸此種種均指向現行的土地制度安排與半城鎮化問題。一方面,關于“半城鎮化”問題的研究,主流學術呼聲集中發力于“城市戶籍制度改革”,乃至于影響了政策設計,并成為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政府提出了推動1億農民進城落戶的政策目標。然而,針對這一制度建設目標,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徹底重塑“土地財政”與官員晉升的行政邏輯,將地方政府從土地城鎮化的路徑依賴中剝離出來,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意愿或激勵來推動農民進城,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于地方政府而言,現階段人口城鎮化的預期成本遠遠高于收益,勢必會影響經濟增長,損害晉升利益。另一方面,鄉城人口轉移的“兩階段三環節”理論[11-12]認為,中國的城鎮化被制度阻隔為農村退出、城市進入、城市融合三個環節。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再重新審視中國的半城鎮化問題,不難發現,目前學術研究忽視了一個重要環節,即農村退出的徹底性。隨著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持續深化,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環節獲取相關基本權利的障礙將逐步掃清,農村退出環節在遷移決策中的重要性將會日益凸顯,而恰恰是現行土地制度并沒有賦予農民農村退出權[13]。是以,關于半城鎮化問題的探討,無法回避土地制度安排。許成鋼在《談“中國模式”》一書中直言:“當前所有最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都產生于同一個體制問題——分權式威權制和土地國有制的結合。回避基本體制問題,以行政方式大力推動城鎮化,不僅無助于解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反而有可能加劇社會穩定問題和經濟結構性問題,激化社會矛盾,最終有可能成為政策陷阱”[14]。因此,城鎮化正確路徑的選擇不應該回避“基本體制”,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土地制度。這一觀點在周其仁那里我們也得到了印證,他認為“農地產權與征地制度是中國城市化面臨的重大選擇”[15]。
2 因果推定:基于農村地權退出與土地財政沖動假說
關于城鎮化發生機制的論題,發展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著述頗豐,核心內容是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來解釋勞動力的城鄉流動[16]。但是經典理論遭遇了中國實踐挑戰。基于進城農村人口“留而不退”與城市建設規模偏向兩類現象,關于中國半城鎮化問題的發生機制與因果推定,開始轉向現行土地制度。
2.1 農地產權與退出權假說
Dixon[17]基于遷移生存以及土地是生存重要支持的假定,推定認為土地是人口遷移的函數。土地對于農村居民的真切意義,既承擔了家庭財產期望,亦扮演了重要的就業功能[18]。因此,農戶土地產權的完備性,將對其轉移成本及方式產生重要影響[19]。Haberfeld[20]以印度不完全的土地產權為視角,分析發現不穩定產權使農民流向城市存在季節性偏向。顯然,中國農地制度安排遭遇了同樣困境。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產權特征為村社地權[21],它將地權與村社地緣身份關系捆綁在一起。按照康芒斯的理解,制度就是“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為”[22]。村社地權正是集體意志的制度結構,因為任何村社成員遷居城市的行動決策,都必須以“放棄村集體權利”為置換條件。盡管這一制度結構正逐漸松動,國務院于2014年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尤為強調:“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現階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但是多年以來的村社地權安排,驅動農民樹立了根深蒂固的成員權觀念。加之,地方政府在政策實施過程中,藉以落戶城市侵害農民地權的行為時有發生。上述客觀事實導致農民對于退出集體,落戶城市,仍存在失去土地風險之憂慮。可見,中國農村地權的不確定性將會顯著降低鄉城人口的遷居與落戶意愿[23-24]。來自微觀調查數據的實證考察,亦佐證了上述結論。黃忠華等[25]分析發現擁有土地稟賦越高的農民,越不傾向于市民化。一個主流的解釋機制是,當面對“城市歧視”“制度性障礙”與不公正待遇及絕對剝奪等諸多現實困境時,進城農民難以有效獲取融入城市的資本,此時,土地承載了農民的就業支持、社會保障功能與財產權期望。土地依附的社會功能日趨強化,導致農民“離農”卻不“離地”。更為重要的是,土地于農民而言,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問題,而是表達了農民對土地財產權利的訴求[26]。恰恰是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村社地權特性,存在平均主義傾向,導致農地產權殘缺與不穩定,致使農民不具備土地市場化退出的自由選擇權[27]。囿于現行農地制度無法為土地提供市場交易通道,進而引發的后果是,農地難以轉換成農民市民化的資本;加之,于多數人而言,任何試圖通過進城打工收益以融入城市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是以,土地不再是簡單的生產資料,而是被賦予了財產權、保障權功能,是進城農民抵御城市非正規就業所面臨的“失業風險”以及高昂城市融入成本的最后“儲蓄屏障”。出于風險規避與自我保護的考慮,進城農村人口構建了“進入城市能打工,退守農村能種田”的自我防護機制[28]。在當代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土地制度存在強粘性效應,將農村人口吸附于土地之上,在事實上維持了農本社會的人口分布[29]。一方面,地權期待邏輯下的財產權訴求與福利功能,引致農村人口與土地的依附關系難以割斷,農村人口在脫離農業與農村時遭遇了退出困局;另一方面,現行農地制度阻滯了農村土地市場化交易機制的發育,引致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缺失,增加了農民失地風險,增加了其落戶城市的機會成本;在諾斯、科斯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產權的顯著特性就是排他性,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保護私人財產,最大化地追求經濟收益,而這恰恰是中國農村土地交易所面臨的困難。無論是黨的十八大所倡導的“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探索增加農民增收渠道”,還是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在“農民財產性收入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土地財產性收入”[30]的現實語境中,均明確指向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關切要義。囿于農村土地產權的歷史沿革與現行制度設計缺陷,農民并沒有被賦予農村退出的自由權。由于個體力量微弱,加之土地失去明晰產權保護,進城農民對于土地退出沒有議價權,其土地增值空間十分有限,進而,希冀通過用土地換取城市融入資本的愿望與前景變得渺茫。同時,進城農村人口出于自我保護機能,存在風險轉嫁傾向,將城市進入的制度風險轉嫁到農地之上,形成了對土地的強依附效應。
2.2 地方競爭與土地財政沖動假說
中國城鎮化的發展帶有強烈行政色彩,“‘政府推動因素遠大于市場力量”[31]。其中,地方政府被視為“推進城鎮化的首要責任主體”[32],甚至被冠之為“市長城鎮化”[33]。在分權式威權體制下,地方官員的考核績效指標(KPI)主要是經濟增長(GDP主義)與財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官員基于政治晉升收益的考慮,為使其處于“有利可圖”地位,便會十分關注經濟業績,陷入唯GDP論。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各級政府間產生了財政層層傳遞效應[34],引致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不對等,財政資金缺口巨大,促使地方政府亟待尋求財政收入的新出路。一場始于1998年的城市房地產改革開啟了“土地資本化”的潘多拉魔盒,并開創了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34]。這一階段城鎮化發展的典型特征是,由工業城鎮化讓渡到土地城鎮化[35]。地方政府利用現行土地制度(主要是城市用地制度)的缺陷,壟斷了城市土地市場供給,并取得了巨大的土地財政績效。在此目標激勵與沖動下,為覬覦土地一勞永逸之利益,地方政府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強烈的規模偏向,突出表現為熱衷于以土地為中心進行城市擴張[36],“盲目增加城市數量、擴大城市面積,以行政擴張型虛假城鎮化攫取土地高額收益”[37]。伴隨這一過程,城鎮化的系列問題漸次顯現,突出表現為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張速度要遠快于人口城鎮化,即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38],或表達為“化地不化人”的城鎮化。至此,地方政府的唯GDP主義被納入分析視野,以尋求“半城鎮化”問題產生的理論機制與破解之道。汪立鑫等[39]認為外來人口增加了城市競爭性公共資源的擁擠成本,且伴隨城市人口的增長而邊際遞增。如果地方政府追求城市戶籍居民的人均公共福利改善,那么勢必會增加地方財政支出負擔,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擠占效應,最終會妨害其政治晉升。顯然,地方政府更偏向于推進土地城鎮化,而對推進人口城市化缺乏動力[40]。綜上,地方競爭與土地財政沖動假說,對半城鎮化問題的作用機制可以歸結為:在現行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壟斷土地市場供給達成政治收益目標,而缺乏足夠的激勵解決人口城鎮化問題,將城鎮化發展帶向了一個偏誤:半城鎮化困境。這一發展偏向最終導致地方財政資源錯配,在支出結構上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41]。基于此,諸多學者試圖通過相關經驗數據以驗證假說。曾冰[33]基于地級市市長數據分析發現,地方官員升遷變動與城鎮化發展存在正向關系,并且地方官員偏好于推動土地城鎮化,而對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并不積極。杜書云等[42]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土地財政對半城鎮化產生的影響機制,分析認為土地城鎮化所引致的半城鎮化問題,最終是人地要素失調的結果。岳樹民等[43]借鑒Hansen、Prescott的馬爾薩斯增長模型過渡到索洛增長模型的分析機制,并引入土地財政要素,分析發現土地財政減少了馬爾薩斯部門的土地使用面積,并促使勞動力轉移至索洛部門。周敏[44]基于GDP錦標賽的地方競爭假說,分析發現地方政府經營土地城鎮化的沖動主要是覬覦土地財政的增長與晉升利益。總結來看,現行土地制度為地方政府尋求土地財政提供了法理支持與便利條件,引致地方政府走向了一個偏誤。地方政府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存在強烈的規模偏好,而不注重人口城鎮化的建設,導致制度性排斥農村人口[29]。
3 分歧與進展:關于土地制度與半城鎮化關系及改革方向的論爭
關于土地制度與半城鎮化關系及改革方向,出現了巨大分歧。其中,賀雪峰的“第三類城鎮化的道路主張”、文貫中“吾民無地的私有產權之路”之吶喊、華生的“提防城鎮化中的土地私有化陷阱與利益機制重構”是為典型代表,本部分將對這三類觀點進行簡要報告與評述。
3.1 土地制度優勢論與半城鎮化的中國式路徑
土地制度優勢論認為,中國應當堅持現行土地制度,當前的半城鎮化是一個制度的理想狀態。他將中國的城鎮化(半城鎮化)稱之為是有別于歐洲、亞非拉的第三種類型,因為我們的城市建設得像“歐洲”,但是卻沒出現亞非拉國家式“觸目驚心的貧民窟”[5]。顯然,這得益于新中國獨有的兩大“歷史制度遺產”:城鄉二元結構與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農村土地制度。“這兩個特殊制度安排使進城農民可以保留返回家鄉的權利,當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時,他們可以選擇返回農村家鄉。”因為“返回家鄉可以生活得體面而舒服,至少要好于城市貧民窟漂泊無根的生活。進城農民在進城若干年后發生分化,少數運氣好收入高的農民在城市中安居下來,……,運氣不好收入不高的農民則退回村莊過收入不奢華卻很穩定的生活”[5]。遵照此邏輯,土地制度優勢論認為征地制度下的土地財政是一種合理存在,“中國有960萬km2的國土,與屈指可數的4.6萬km2的建成區面積相比,土地財政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5]。同時,正是得益于土地財政的巨大收入績效,中國的城市化才得以完成資本積累,把城市建設得像歐洲。因此,現行土地制度應當堅持,如若一味追求清除城鄉二元結構、消滅小農經濟、改革征地制度,以此推進城鎮化的道路,無疑是“激進型的城鎮化”策略[5],勢必會使中國陷入“城市二元”的“拉美宿命”。事實上,“現存的城鄉二元結構與土地制度安排有效地消解了城市二元結構”[5],同時,“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5]建構起了“進城農民工與農村家鄉的密切聯系”[5],使“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5]。但是,秉承制度優勢論的理論邏輯,我們無法面對和回答兩大現實難題。第一,如果中國堅持現有土地制度,當如何應對農村宅基地冗余、土地資源浪費的問題?當前,半城鎮化問題所導致的矛盾日益顯現,主要表現為:伴隨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土地所依附的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導致土地資源浪費問題嚴重。例如:盡管中國農村常住人口每年以1.6%的速度減少,但農村宅基地卻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9]。據測算,中國農村宅基地具有非常大的整理空間,到2020年大致為0.3億畝土地[45]。第二,盡管土地財政實現了“漲價歸公”,但是未能實現“地利共享”。制度優勢論認為:“中國有960萬km2的國土,與屈指可數的4.6萬km2的建成區面積相比,土地財政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5]。我們姑且不論土地財政下的“黑箱財政”與“尋租行為”,僅從“地利共享”制度構想來看,“土地”價值具有強外部性,其對“城市化的意義不在于肥沃程度,而在于位置”,“農地之主對‘位置生產力顯然沒有多大貢獻”[15]。因此,非近郊進城農民無法通過土地城鎮化以分享發展紅利。更為重要的是,土地財政下的農民土地“高額收益”與“補賞”(相較于農地生產性收益而言),被狹隘于“少數人”,限定于屬地化的城市戶籍人口。即使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大一倍至10萬多平方公里,也僅占國土面積的1%多一點,涉及被征地的農村人口也僅為少數,并不是驅動半城鎮化轉型的建設主體。此外,城鎮化過程中的巨額征地費用,將進一步加劇城市近郊社區與非近郊社區的財富差距。任何一條城鎮化的道路表明,城鎮化的推進勢必會減少貧富差距,例如:日本、韓國等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以后,基尼系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46]。反觀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盡管有所收斂,但如果加入“城市財產性收益”,差距是否收斂仍有待商榷。
3.2 土地制度引致城鄉結構性扭曲,于農無益
土地制度扭曲論認為,現行土地制度扭曲了城鄉土地要素市場,導致城市自我現代化,于農無益,因此,要以私有化思路改革現行土地制度。在中國現行的土地憲法產權秩序體系內,盡管糾正了“人民公社”生產的負外部性與非激勵問題,將農業生產剩余所有權賦權于民,但是“土地交易市場被政府雙重壟斷”[29]。在中國只有兩種土地,政府手里的國有土地,農民手里的集體土地[47]。農民手中的集體土地完全被狹隘化于農業生產用地與宅基地,無法通過市場化途徑以分享城鎮化發展紅利,因為任何企圖通過市場交易實現農地價值轉換的努力,都必須予以國有化為前提,這即為城市用地、征地制度的缺陷。同時,農地產權的不確定性恰好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行為,提供了巨大便利空間與制度土壤。在官員晉升激勵與國家GDP主義導向中,行政主導的土地供給制度以“近乎壓榨式的強取豪奪”為基本特征,通過“低價征地、高價出讓”手段,最大化地攫取土地價值。以“土地財政-城市擴張”為特點的外生型城鎮化發展道路,“無論是以效率,還是以社會公正衡量,其低劣和不得人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29]。它嚴重扭曲了“人”的城鎮化的基本價值立場,損害了社會公平與正義。土地財政調節社會公平,實現財富再分配的功能,被弱化于經濟增長的粗暴邏輯中。土地因“位置”的級差收入通過“低價征地、高價出讓”的形式被最大化攫取,以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即賀雪峰教授眼中的第三類城市化,因為唯有如此,土地財政的經濟效力及其關聯的政治晉升才能夠最大化實現,并且不必承擔“為進城農民福利供給”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成本。基于此,土地制度扭曲論認為,政府主導的城市自我現代化必導致制度性地排斥農村人口,于農無益[29]。受“壟斷土地供給”所帶來的高額收益驅動,地方政府建構起了按城市戶籍配置社會權利的運行規則。由此,制度性排斥進城農民逐漸內生為地方政府的自覺行動與價值主張,導致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是化地不化人,致使大量人口被黏附于農村土地之上。基于此視角來看,文貫中教授“吾民無地”的呼吁似乎直指“半城鎮化”問題的癥結所在,據此,所倡導的“農地私有化”主張是有效的改革方案。但是針對此觀點,本文仍存疑慮。土地私有化制度所標榜的平等權利,“充其量也就是局限于社區之內的,非常狹隘的公平,并且固化了社區之間的巨大不平等”[46]。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因為近郊社區集體總能夠在城鎮化的擴張中獲取巨量土地增值,而改善社區內部福利。因此,若主張土地私有化,實為近郊農民聲張財產權。這一論斷可以從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有力證實,1996—2010年,全國建設用地增加了7 410萬畝,造成3 0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48],如果排除工礦、國家重點工程占地所導致的失地農民,大致僅剩2 000萬人,占約9億農民的3%左右[46],即僅有3%的農村人口可以從城鎮化地擴張中獲取土地增值財富。無疑,“農地私有化使得農民有權分享土地升值而帶來的巨額財富”[46]的制度構想,無論在表面上顯得如何公允,實際上只是在為大約3%的被動城市化的城郊農民說話,卻抹殺了97%的自主城市化主體的土地增值訴求[46]。
3.3 提防土地私有化陷阱與重構土地利益分配機制
土地制度優勢論,堅持既有的城鎮化道路,顯然無助于半城鎮化的轉型,無法讓農村人口分享土地增值紅利;土地制度扭曲論,主張土地私有化改革,但是會陷入社區不平等陷阱。華生教授[46]秉持穩健的改革理念,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要提防土地私有化陷阱,關鍵是重構土地利益分配機制,核心是讓人的城鎮化與土地的城鎮化協同推進。研究中國城鎮化,必須以農民、農村、農地為邏輯起點[46]。中國在農本社會向城市現代社會轉軌的過程中,出現了農田流轉、農民進城、農地轉用三個問題[46]。這三個問題交織于城鎮化進程中,構成了理解半城鎮化問題的核心與實質——土地權利的再分配[46]。其中,土地權利的再分配涉及的重要議題是土地財政與農村土地集體制度安排。一方面,土地財政的真正問題是“它的支出完全忽略了農民工等移居者這個城市化主體的需要”[46];另一方面,農地集體制度存廢之爭“與其說是土地所有權的形式,不如說是土地開發權的歸屬與分配問題”[46],“中國億萬農民工及其留守家屬子女之所以落入今天這樣無助弱勢的地位,也正是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土地開發權不公正分配的直接結果”[46]。上述土地權利的錯配與扭曲,遲滯了農民城鎮化進程,導致了當代中國的半城鎮化困局。目前,無論是土地財政的收益,還是城鎮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財富,都是逆向配置的,這兩個方面的收益主要被配置于少量近郊或城市屬地人口,而巨量的遠郊農民或非屬地農民(作為城鎮化的主體)未能享有[46]。是以,主張私有化的發展道路必將陷入土地陷阱而抹殺了城市化構成主體的利益訴求。因此,與其過多地爭辯所有權形式,倒不如“調整既得利益結構,將土地增值收益回歸到城市化主體”[46],關鍵路徑是“改變體制換糧斷奶,將地方政府撥出賣地財政陷阱”[46],同時,要賦予公民自由遷徙權,在堅持社會公平公正的原則基礎上重塑城鄉居民平等地擁有、處置土地及其附著物的財產權利[46],理順農田流轉、農民進城、農地轉用三大問題,以城鎮化引領與推動農業現代化,協同推進人的城鎮化與土地的城鎮化。
4 評述、思考及引申
土地制度對半城鎮化的生成機制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以村集體所有權配置土地權利,無法為農村人口的土地財產權實現提供制度通道;二是以城市征用地制度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行為提供制度庇護。因此,如若不能全面理清其中的利害關系,而寄希望于通過任何單方面的努力便將半城鎮化問題解釋清楚,都可能將中國城鎮化的研究引向偏誤。關于土地制度對半城鎮化的因果推定與機制識別,主要是農地產權與退出假說、地方競爭與土地財政沖動假說,一個偏微觀分析,一個偏宏觀考察,并沒有建立起“微觀-宏觀”的互動解釋機制。事實上,現行制度結構所導致的“半城鎮化”問題,并不是任何一方力量的結果使然。地方政府在晉升激勵與GDP目標導向下,自然強調城市利益,并內生為自覺的行動主張,以彰示政治績效,而忽視了人的城鎮化的統籌推進,進而不必支付高昂的市民化成本。農村人口的流動遷移仍是托達羅過程,只要索洛工業部門提供略高于生存水平的制度工資,馬爾薩斯(傳統農業)部門邊際產出為零的剩余勞動力便會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初始的制度條件(主要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了農民農業退出的權利,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是為“民工潮”。此階段,盡管面對城市制度性排斥與福利歧視,但是于進城農民而言“不僅是可以被接受,而且是他們獲取非農收入以改善其家庭在農村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手段”[49],此時,他們只需要支付較低的農業退出成本。當進入制度性遷居決策階段:農村退出環節,鄉城轉移人口需要承擔“失地”之后的社會保障成本與土地財產權的機會成本。相較于城鎮化的非農收益,農村人口的退出損失大于收益。受短視性損失厭惡驅動,非制度性遷居城市將是農民群體的理性算計。綜上,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內,“半城鎮化”問題是農村人口微觀行動策略與地方政府宏觀政策選擇共同的合意均衡。緣于此,半城鎮化向徹底城鎮化的轉型建設,不能以互相割裂的改革方案替代。
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經驗表明,城鎮化的真諦只有一條,就是吸納農村人口進城定居,并降低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是以,推動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行動方案與制度建設目標,在一定意義上,契合了“人”的城鎮化的價值主張。秉承土地制度優勢論者,強調穩健的農村人口退出策略,誠然看到了土地及制度設計所衍生的“穩定功能”與“蓄水池效應”,卻背離了城鎮化發展的一般化規律。因為土地制度的村社地權性,導致農村人口退出困難。關于土地私權的主張,本文依然深存疑慮,因為推行土地私有化對半城鎮化問題的糾偏,可以預見,并不能產生多大效力。它只是在為極少數人的土地價值辯護與聲張權利。作為個人主義的忠誠衛士哈耶克,在討論土地私人產權的時候,亦不得不保持謹慎態度,一旦“涉及到土地時,就會產生一些更為棘手的問題,在這方面,承認私人產權原則對我們幫助甚小,除非我們清楚知道所有權所包括的權力和義務的真切意義”[50]。盡管關于土地公有制與私有制的論爭十分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思考,但卻很難講清楚現行土地制度與半城鎮化的關系。這囿于現行農地產權能夠為政府進行城市征地、用地以尋求土地收益,提供尋租空間。作為半城鎮化的重要的實踐主體、參與者:地方政府,如果不能予以改變或糾正這一激勵機制,財政資源的配置必然與農民進城行動脫節,城市建設與農民市民化錯位,進而“超越半城鎮化”的努力將會是徒勞的。當然,本文并不反對賦予農民清晰地權的學術呼吁,但是過分顯化所有制的探討,將無裨益于“半城鎮化”問題的解決。
國家關于農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公權之上重塑私權,即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地位不動搖,并逐漸向追求效率的經濟功能與賦予權利的保護功能讓渡[51]。回溯新中國土地制度的歷史沿革,土地制度的變革與城鎮化發展休戚相關。歷史經驗表明,我們可以在不觸及所有權的改良方案下取得城鎮化發展的巨大績效。一場始于8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政府提出了“集體所有制+承包制”的制度構想,并最終形成了“兩權分置”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恢復家庭生產的主體地位,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解放了農村人口,推動了城鎮化發展的第一次跨越: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快速實現。當前,國家制定了農地制度“三權分置”的改革方案,旨在剝離承包權的生產功能,僅賦予其權利的保護功能,并力圖以經營權形塑土地生產功能與提升農地價值。一方面,經營權從承包權中分離出來,騰挪農業現代化的規模空間,以有效整合農地資源,進一步發展土地生產力;另一方面,經營權、承包權的分置,可以將“人地依附”關系轉變為“人地保障”關系,繼續發揮農地保障功能,推動鄉城轉移人口的半城鎮化轉型。但是,我們應當注意,“人地依附”關系轉向“人地保障”關系,并不意味著人口農村退出的順利實現。它有賴于相關激勵制度的建立,尤其是要建立農村土地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構建建設用地指標物權化的體制機制,允許偏遠農村人口將退地(宅基地、承包地)后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作為流動資產,可以有償進行轉讓,探索帶“地標”城鎮化方案。顯見,未來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關鍵是建立“地權隨人走”、“人地錢”掛鉤機制,一則糾正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沖動與錯配支持,二則賦予進城農民的土地退出權或市場化收益權。作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地方政府與非屬地進城農民應當聯動起來,建立利益共同體機制與激勵相容機制,以走出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理性與農民經濟收益理性的博弈困局,實現半城鎮化向完全城鎮化的轉型。
(編輯:王愛萍)
參考文獻
[1]辜勝阻. 統籌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改進低價工業化和半城鎮化模式[J]. 中國人口科學,2007(5):2-4,95.
[2]李愛民. 中國半城鎮化研究[J]. 人口研究, 2013(4):80-91.
[3]李春生. 中國兩個城鎮化率之差的內涵、演變、原因及對策[J]. 城市問題, 2018(1):11-16.
[4]王小剛, 李太后. 中國“半城鎮化”問題與農民工的理性選擇[J]. 天府新論, 2012(1):111-114.
[5]賀雪峰.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4.
[6]WANG Z, ZHANG Q, ZHOU L. To build outward or upwar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GB/OL]. http:// dx.doi.org /10.2139/ssrn.2891975.
[7]蔡禾, 王進. “農民工”永久遷移意愿研究[J]. 社會學研究, 2007(6):86-113,243.
[8]史清華. 中國農家行為研究[M].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9:215.
[9]李勇堅, 袁錦秀, 李蕊. 我國農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創新研究——“宅基地指標化”改革思路與方案設計[J]. 西部論壇, 2014(6):7-16.
[10]趙民, 游獵, 陳晨. 論農村人居空間的“精明收縮”導向和規劃策略[J]. 城市規劃, 2015(7):9-18,24.
[11]蔡昉. 勞動力遷移的兩個過程及其制度障礙[J]. 社會學研究, 2001(4):44-51.
[12]朱宇, 楊云彥, 王桂新, 等. 農民工:一個跨越城鄉的新興群體[J]. 人口研究, 2005(4):36-52.
[13]鐘水映, 李春香. 鄉城人口流動的理論解釋:農村人口退出視角——托達羅模型的再修正[J]. 人口研究, 2015(6):13-21.
[14]許成鋼. 許成鋼談“中國模式”[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5]周其仁. 農地產權與征地制度——中國城市化面臨的重大選擇[J]. 經濟學(季刊), 2004(4):193-210.
[16]姚從容. 論人口城鄉遷移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變遷[J]. 人口與經濟, 2003(2):69-74.
[17]DIXON G I J. Land and human migr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 1950, 9(2):223-234.
[18]VANWEY L K. Land ownership as a determinant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Mexico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ailand[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0, 39(1):141-172.
[19]黃善林, 盧新海. 土地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研究綜述[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5):22-27.
[20]HABERFELD Y, MENARIA R K, SAHOO B B, et al. Seasonal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in India[J]. Population research & policy review, 1999, 18(5):471-487.
[21]溫鐵軍. 中國城鎮化戰略中的農地制度創新[J]. 中國鄉村發現, 2015(3):29-35.
[22]康芒斯. 制度經濟學(上冊)[M]. 于樹生,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62: 100.
[23]YANG D T. Chinas Land arrangements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7, 8(2):101-115.
[24]MULLAN K, GROSJEAN P, KONTOLEON A.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123-133.
[25]黃忠華, 杜雪君. 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阻礙農民工市民化:托達羅模型拓展和義烏市實證分析[J]. 中國土地科學, 2014(7):31-38.
[26]羅必良. 農地保障和退出條件下的制度變革:福利功能讓渡財產功能[J]. 改革, 2013(1):66-75.
[27]文貫中. 土地制度必須允許農民有退出自由[J]. 社會觀察, 2008(11):10-12.
[28]陳會廣, 劉忠原. 土地承包權益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托達羅模型的修正與實證檢驗[J]. 中國農村經濟, 2013(11):12-23.
[29]文貫中. 吾民無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在邏輯[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4.
[30]丁琳琳, 吳群. 財產權制度、資源稟賦與農民土地財產性收入——基于江蘇省1 744份農戶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2015(3):80-88.
[31]陳甬軍, 徐強, 袁星侯,等. 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分析[J]. 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 2001(9):16-20.
[32]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 城鎮化進程中的地方政府融資研究[J]. 經濟研究參考, 2013(13):3-25.
[33]曾冰. 地方官員推動了城鎮化嗎?——基于江西省地級市的經驗證據[J]. 財經論叢, 2015(11):10-17.
[34]許經勇. 分稅制、土地資本化、土地財政與城鎮化轉型[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11):5-9.
[35]周飛舟, 吳柳財, 左雯敏, 等. 從工業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到人口城鎮化: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社會學考察[J]. 社會發展研究, 2018(1):42-64.
[36]LICHTENBERG E, DING C. Local officials as land developers: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8, 66(1):57-64.
[37]李學. 行政擴張型虛假城市化現象的機制分析——委托—代理理論的視角[J]. 東南學術, 2006(2):43-49.
[38]李子聯. 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之謎——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解釋[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3(11):94-101.
[39]汪立鑫, 王彬彬, 黃文佳. 中國城市政府戶籍限制政策的一個解釋模型:增長與民生的權衡[J]. 經濟研究, 2010(11):115-126.
[40]謝冬水. 地方政府競爭、土地壟斷供給與城市化發展失衡[J]. 財經研究, 2016(4):102-111.
[41]傅勇, 張晏. 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 管理世界, 2007(3):4-12,22.
[42]杜書云, 牛文濤. 土地財政是否加劇了“半城鎮化”問題?——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4):56-60.
[43]岳樹民, 盧藝. 土地財政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數理模型推導及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J]. 財貿經濟, 2016(5):37-47,105.
[44]周敏. 一個基于土地財政的經營城市模型[J]. 世界經濟文匯, 2017(1):87-98.
[45]宋偉. 中國農村宅基地整理潛力估算[J]. 中國農學通報, 2014(33):301-307.
[46]華生. 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3.
[47]周其仁. 土地財政的功過是非[J]. 財經界, 2014(9):56-59.
[48]嚴之堯. 關于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J]. 行政管理改革, 2015,12(12):18-20.
[49]鄒一南. 特大城市戶籍管制的自增強機制研究[J]. 人口與經濟, 2017(2):55-65.
[50]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 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 鄧正來,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
[51]鄧大才. 中國農村產權變遷與經驗——來自國家治理視角下的啟示[J]. 中國社會科學, 2017(1):4-24,204.
Abstract Academic proposition on urbanization that highly emphasizes urban inclus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issu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However,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gradual overcoming of relevant obstacles, the problem of periurbanization in China still hasnt been solved effectively. Therefore, reexamining the reasons behind peri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 There are two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are the size of urban construction, permanent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migration and polarization all explicitly depend on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arrangement.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paper summarizes two empirical hypotheses: quitting of the proprietorship of rural land and the impulsion of land finance. Besid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periurbanization under a holistic analysis structure of land system.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provides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the land financial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by means of urban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Meanwhile allocating land rights through village collective proprietorship cannot provide institutional channels to realize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of rural popul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vergence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system and periurbanization and its reform orientation. The theory of land system advantage believes that periurbanization is the ideal outcome of system operation. The theory of land system distortion holds the opinion that land private rights need to be restructured. The theory of steady reform thinks the crux lies in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traps in land privatiz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s. After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land system, periurbanization is the ideal balance reached collectively by the micro behavior strategies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macro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riurbanization to complete urbanization cannot be substituted by fragmented reform schemes. The core of land system reform is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The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is to reshape private rights on the basis of public rights. That means we should unswervingly uphold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and gradually transit to the economic function that pursues efficiency and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that can empower people, diverting the humanland dependence to humanland guarante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should allow remote rural population to use the new construction land index gained through returning their land as liquid assets, which means they can be transferred with compens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scheme with landmark ca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l right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land index. It can not only rectify local governments impulsion of land finance and misallocated support but also entitle the rural migrants the right to waive their land proprietorship and the marketized right for earnings. The ideal status of the reform is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with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local rural migrants so that the dilemma between the growth choi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aversion to famers losses can be solve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riurbanization to complet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land system arrangement; peri urbanization; two hypotheses; argument and progress; review and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