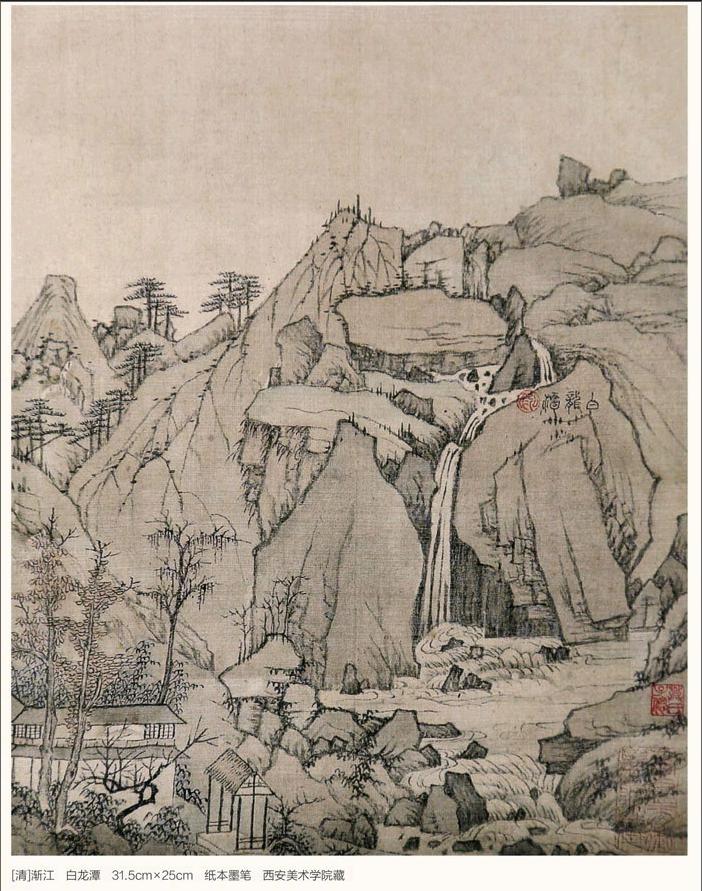坐二望一
張渝
如果說“千年老二”是一種悲情的話,那么“坐二望一”則是一種“樂觀”的幸福。
作為“新安畫派”的二號人物,查士標在“新安畫派”中的排位,僅次于漸江,而在孫逸、汪之瑞之前。巧的是,查士標恰恰字二瞻,號梅壑。“二瞻”這個字,關聯的當然是查士標的名而非其他,比如我說的“坐二望一”。但是,一語成讖。中國繪畫史寫到明末清初的“新安畫派”時,查士標基本是“坐二望一”的地位。這種“既生瑜何生亮”的尷尬處境究竟意義何在?
漸江劍走偏鋒的冷逸出塵,使得他的藝術在黃公望、倪瓚之后,真正具備了形態學的意義。
在《正統風尚中的詩性之光——從漸江看中國繪畫的寫意精神》一文中,我曾如此開篇:在一個崇尚正統的時代,漸江顯得有些落寞,即使“江南人謂得漸江是當倪高士。”這也依舊難改漸江落寞的形象,倒不完全是因為這樣的說法僅僅是“江南人謂”,在我看來,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相比于“四王”所代表的正統畫風在當時以及之后的影響力來說,漸江是落寞的。無論是從當時的認知,還是當下的認領來看,漸江都不是主流藝術家,他只是畫壇之內一棵孤獨而又少有果實的樹。在他的時代以及稍后,盡管有一個新安畫派,但這個非主流畫派并不能改變他的孤獨處境。因此,他靜靜地立在那里,不為證明,只為生長。于是,一種真正的藝術精神,也就是我所謂的詩性之光,靜謐而又孤冷地射了過來,冷光之中,所謂寫意有了精神。
由于過于強烈的風格特征及其一人獨往的藝術成就,漸江作為“新安畫派”的頭號人物,應該沒有異議。但是,由于幾近極致的藝術風格,以漸江為首的“新安畫派”也基本上是在逼仄的藝術空間里散發自己“靜謐而又孤冷”的光。它的處境很像王安石筆下那枝偏居墻角的梅:雖有暗香襲來,卻空間不大,很難發揚。也正是在這里,查二瞻的意義呈現出來:一個畫派的持續發展力。
如果稍加留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強大的畫家陣容幾乎處于同一時間段。漸江(1610-1663),查士標(1615-1697),程邃(1607-1692),程嘉燧(1565-1643),戴本孝(1621-1691),汪之瑞(?-1660),孫逸(?-1658),蕭云從(1596-1673),石濤(1642-1708),髡殘(1612-1692),八大山人(1626-1705),王時敏(1592-1680),王鑒(1598-1677),王翠(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吳歷(1632-1718),惲壽平(1633-1690)。在這個陣容中,“四王吳惲”等被人視為正統畫派。對于中國畫的傳承發展,正統畫派起了主要作用。與漸江交好的查二瞻,其藝術風格中,有漸江的影響,但不大。真正影響他的還是黃公望、倪瓚、沈周、董其昌等人。而正統畫派也基本是順著這個路數下來的。基于此,就繪畫本身發展言,在“孕后”這個維度,查二瞻的意義要大于一號人物漸江。
其實,這個問題,用藝術史的眼光看,就是先鋒和常規(中軍、主力)的問題。
就藝術史的發展言,先鋒前傾的沖鋒姿態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視的是,先鋒們前傾的姿態并不是生命發展的常態,而是矯枉必須過正的非常態。所有的生命包括藝術史的正常發展必須是常態發展,是先鋒以前傾的姿態搞完成熟或不成熟的攻擊動作后,靠大部隊(中軍)的大兵壓境或走過來完結的。如此,漸江可以說是先鋒派的代表,二瞻則是中軍的領軍人物。就個人成就言,漸江高于二瞻:就團隊發展言,二瞻高于漸江。
在《中國畫的可持續發展》一書中,徐建融以正文化和奇文化來談論中國藝術的持續發展。他以為,“正文化的傳統,以晉唐宋元的正規畫為代表,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王維、張萱、周嗷韓斡、韓滉、孫位、荊浩、關仝、董源、巨然、黃筌、徐熙、李成、范寬、顧閎中、周文矩、李公麟、趙昌、崔白、郭熙、王詵、趙令穰、文同、趙佶……弘仁、髡殘”。我基本同意這一看法。但把弘仁(字漸江)歸入“正文化”這一譜系,略嫌牽強。弘仁的藝術出奇制勝,應該歸入徐先生自己強調的“奇文化”譜系,即“徐渭、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可能因為二瞻在“新安畫派”中“千年老二”的處境,徐建融先生沒有在“正文化”譜系中列明查二瞻。但就藝術風格言,如果“新安畫派”有一人進入“正文化”譜系,也只能是查二瞻而非弘仁(漸江)。
一個畫派,一號和二號人物,都可能是領軍人物,就看從哪個角度來看待。以我相對熟悉的“長安畫派”言,趙望云和石魯兩位藝術家,都很重戛但他們在畫派中的作用卻不同。石魯是天縱之才,可看不可學,更具先鋒意義:趙望云則言傳身教,“術巧成風”(石魯語),可學者眾。故其身后學生眾多,著名者黃胄、方濟眾、徐庶之、韋江凡等。
有一個現象非常耐人尋味:查士標夫子自道,“我家黃山未識面”。身為山水畫家且又出生并生活在黃山邊上,卻從未上過黃山。這對于一位山水畫家來說,有點兒匪夷所思。這一點,任軍偉先生解釋說,由于查士標與擅畫黃山的漸江關系很近,他在漸江的作品中耳濡目染,已領黃山風神。這是一種解釋。此外,如此事實或許還指明查士標手頭資料很多(家藏豐富)以及他的朋友圈很強大。當然,查士標生長的地方,自然風景也不錯,入畫足以,也是一個原因。不過,如此藝術路徑,一個現實的結果是:查士標的作品臨仿有余,原創不足。藝術本體的功夫不錯,某些方面甚至強過“新安畫派”排名首位的漸江,卻依舊只能“坐二望一”。這就如同林丹和李宗偉。李宗偉個人羽毛球技術的細膩程度強過林丹,卻缺少林丹致命一擊的霸氣,只能是“千年老二”,令人感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中國繪畫大師精品·查士標》,是任軍偉的大著。這是我所見到的有關查士標藝術資料搜集最全面、論述最周到的一本書。該書關于查士標的生平、交游以及繪畫之外的詩詞、書法,都有自己的見解,難能可貴。美中不足的是,軍偉的研究還是忽略了“常態的天平。一個藝術家,一個像查二瞻這樣“坐二望一”的藝術家,對于藝術常規發展的意義在哪里?
一如軍偉的老師樊波教授在為軍偉所寫序文所指出的:“查士標并不是明清之際最杰出的書畫家,卻是極為重要的書畫家之一。研究查士標既可以了解元人以及董其昌所確立起來的高逸的文人畫風由明到清得以延傳的脈絡,可以了解……而查士標是一位具有節點意味的人物,他的家世,他的朋友圈,他的人文和藝術素養,甚至他的書畫為何偏于守成而難有突破,凡此種種,都是值得人們深入探究的學術議題。”的確,如此提綱挈領的方家之言,幾乎點明有清一代美術史的另一種寫法,但這不是軍偉這本《查士標》可以囊括的。
不僅如此,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態以及禪佛影響,可寫者甚夥。但是,藝術的常態或常規,一個關于藝術持續發展的問題,還是不能忽略。“坐二望一”,強調的不是世俗排序,比如排座座,吃果果,而是更內核的藝術發展的本體問題,比如法統。
開眼是他。閉眼也是他。
責任編輯:劉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