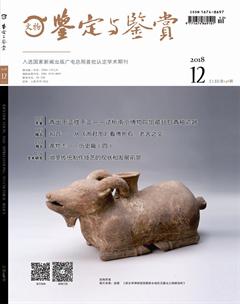青出于藍勝于藍
馬成
摘 要:顏色釉瓷是中國明清瓷器的重要種類,而氈包青釉瓷器是眾多顏色釉瓷器中的一小眾品種。以前,國內從事博物館文物專業研究的工作人員常把其與霽藍釉和茄皮紫釉區分模糊,因為氈包青釉瓷器的存世量并不像黃釉、紅釉、青釉、藍釉、白釉等瓷器那么大。但南京博物院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藏有數量可觀的氈包青釉瓷器。筆者于2016年參加了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發現了一定數量的氈包青釉瓷器。文章從氈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器形和燒造工藝進行了初步分析,并對其和霽藍釉、茄皮紫釉瓷器進行區分介紹。
關鍵詞:顏色釉;氈包青釉;霽藍釉;茄皮紫釉;燒造工藝
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館四樓“盛世華彩”展廳的陳列柜里擺放著一件藍中微微泛紫的爵杯,它被定名為“清乾隆氈包青釉爵杯”。以前,國內從事博物館文物專業研究的工作者常把氈包青釉與霽藍釉和茄皮紫釉三者區分模糊。霽藍釉無論是官窯制還是民窯燒造,都有比較多的產品;茄皮紫釉雖較為名貴產品,但也有一定數量;而氈包青釉的瓷器的存世量就更少了。南京博物院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藏有數量龐大的官窯瓷器。筆者于2016年在文物庫房里參與了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發現其中氈包青釉的瓷器存在一定數量,也和霽藍釉、茄皮紫釉有明顯區別。本文從氈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器形及其與霽藍釉、茄皮紫釉的燒造工藝進行分析、比較、研究。
1 對氈包青釉瓷器的相關研究概述
《陶雅》記載氈包青釉瓷器:有一種盤、碟,表里皆如濃深之積藍(即霽藍釉),而釉質發亮,亦名曰玻璃釉,康、雍、乾三朝皆有之,略有似于氈包青也。還描述:“豇豆紅之于茄皮紫,差別在于幾希微忽之間,茄皮紫之于氈包青也亦然。”[1]
許之衡著《飲流齋說瓷·說彩色第四》一書中對氈包青釉和茄皮紫釉有比較明確的描述。前者:“至若青色之較濃者,曰天藍、淺藍。而近于綠者,曰翠藍、深藍。而有芝麻星者,曰魚子藍(即灑藍),殆謂其形有類似,非謂其色同魚子也。至于藍紫相和,而藍尤濃厚者,曰氈包青,亦好奇之所嗜云。”后者:“茄紫一色,始于明末,康熙繼之,皆系玻璃釉。淡者比茄皮之色略淡,深者比煮熟茄皮之色又略重,故有淡茄、深茄之分。淡茄尤為鮮艷,介于豇豆、云豆之間。”[2]
南京博物院老一代古陶瓷研究專家王志敏所著《學瓷鎖記:王志敏文物鑒定1000例》中第569例記載道:“康熙景德鎮窯單色釉瓷之孔雀藍、雞油黃、氈包青等……自是比較沉重,與新燒不同。”[3]
南京博物院在2013年出版的《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窯瓷器》一書中寫到:“氈包青釉始于明嘉靖朝,因其釉色似一種蒙古包的色澤而名。氈包青的造型多為盤、爵杯、犧尊,亦見花盆。”[4]
古人直觀的概述和現在人們對氈包青釉瓷器的理解有許多誤解和不全面之處。筆者認為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里對氈包青的描述最為確切:“至于藍紫相和,而藍尤濃厚者,曰氈包青。”藍紫相互諧調而藍色尤為渾厚的,稱作氈包青釉。
2 氈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及種類
要搞清楚氈包青釉瓷器在歷史中的地位及用途,首先要從清代大規模使用顏色釉瓷器說起。顏色釉是瓷釉的一個種類,是在釉料中加入鐵、銅、錳、鈷等氧化金屬著色劑,在相應的燒成條件下,釉面呈現出青、褐、紅、藍、綠、紫等顏色。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燒造顏色釉瓷器的頂峰期。清代大督窯官唐英《陶成紀事碑》記載窯廠燒制的顏色釉就有35種之多,其中單色釉是顏色釉里的重要組成部分。
顏色釉瓷器的使用與祭祀活動的需要密切相關。祭祀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從春秋戰國以來就把國家大事定義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清朝依舊是把祭祀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一年中會有四次大的祭祀,分別為天壇祭祀、地壇祭祀、朝日壇祭祀、夕月壇祭祀。天壇祭祀是清代最為隆重的祭祀,于每年的冬至進行,其祭祀的對象是天神。地壇祭祀又稱“拜壇”,是皇帝祭祀皇地祇之所,也是大祭,規模僅次于天壇,于每年夏至舉行。朝日壇和夕月壇是用于祭祀太陽神和月神之地,分別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之際舉行,規模大小為清廷中祭。
據《元史》記載,從元代開始祭器、禮器由瓷器逐漸代替金、銀、銅等金屬器皿。到明代初期,規定祭器皆用瓷,一直延續至清朝。而明、清兩朝祭祀所用瓷器的顏色有著明確的規定。《欽定皇朝禮器圖示》記載,天壇祭祀用瓷為青色,地壇祭祀皆用黃瓷,朝日壇用瓷均為紅色,夕月壇用瓷則以月亮一般的白色為色調。
清朝初期對祭器的材質也有明確的規定:“初延明制,壇廟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總理禮器圖館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人奉赦修撰《欽定皇朝禮器圖示》,后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加校補,并有所增補,將所有祭器的材質、尺寸、紋飾、顏色都做了明確的規定。書中用文字及圖片記載單色釉瓷器是清朝皇家朝廷用來祭祀的必備品。所用瓷器種類有登、簋、豆、爵、犧尊、盤等,氈包青釉瓷器則有尊、爵、盤等造型。
瓷爵是以商周青銅爵為藍本仿制而成,多用于祭祀。將瓷爵作為宮廷祭祀用品,最早始于宋代。明洪武初年,朝廷規定“祭祀皆用瓷”后,明清官窯都有瓷爵生產,明早期以白釉爵為多,明中期開始有祭藍釉爵。氈包青釉瓷爵始見明代嘉靖年間,此后各朝官窯有燒造,但多見于康熙和乾隆年間,民窯則不多見。
《欽定皇朝禮器圖示》記載:“謹按,《周禮·太宰》:‘贊玉幣爵之事。《說文》云:‘爵,禮器,象雀之形。陸田《禮象》:‘古銅爵,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博古圖》謂:‘前者噣,后若尾,足修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為耳。”乾隆十三年(1748),欽定祭器:天壇從位爵用青色瓷,通高四寸六分,深兩寸四分。兩柱高七分,三足相距各一寸八分,高二寸。”[5]
陳列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館四樓的“盛世華彩”展廳里的這件清乾隆氈包青釉爵杯高9.7厘米,口徑11.8厘米。口沿上有兩菌形柱,爵舟的腹部較深,爵身一側有柄一只,小平底,底周邊下置三條柱形足。通體施氈包青釉,釉色藍中微微泛紫,釉面平整渾厚(圖1),底足見支燒點。底部暗刻六字三行“大清乾隆年制”篆書款,但極不清晰。
《欽定皇朝禮器圖示》記載:“天壇正位尊,謹按,鄭鍔曰:‘尊以盛五齊三酒,用以獻,且上及于天,故名曰尊。祭天用瓦泰。《禮記·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孔穎達曰:‘以《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故知泰尊用瓦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注云:‘太尊,太古之瓦尊。蓋溯皇初之制,莫質于此矣。”乾隆十三年(1748),欽定祭器:天壇正位尊用青色瓷,純素,通高八寸四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圍二尺三寸七分,底徑四寸三分,足高二分。兩耳為犧首形。”(圖2、圖3)由此可見氈包青釉瓷器主要乃天壇祭祀所用之器。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氈包青釉犧耳尊(圖4),高35.3厘米,口徑16.7厘米,足徑14.8厘米。帶蓋,寶珠鈕,直口,短頸,溜肩,肩部以下漸收,平底。其內外壁均施氈包青釉,藍中泛紫,釉面渾厚,施釉至底部,中心露胎,顯出明顯的旋坯痕,更有三個對稱的支燒點,可以推斷出這是用了三角形支燒窯具燒成(圖5)。這是氈包青釉燒造工藝的一大特色。
盤作為祭器雖《皇朝禮器圖示》不載,但《清宮瓷器檔案全集》中傳辦燒造頗多。不同用處的盤有不同稱呼,有毛血盤、供果盤、供鮮盤、供肉盤等。基本造型為敞口或撇口,淺腹,平底,矮圈足。毛血盤為祭祀時盛牲畜的大盤。南京博物院也有此類氈包青釉大盤(圖6、圖7),此盤口徑25厘米,底徑16厘米,高4.5厘米。通體施氈包青釉,釉面渾厚,藍中泛紫,并保留了宮廷所用的黃標簽,上面以文字寫到“為十八號里外霽青盤三百六十九件起”。由此可見,除了當時用盤所需要的件數和規模外,器物名稱不以燒造工藝定名,而主要是以釉色來區分(在古代,“青”通常指綠、藍、黑三種顏色)。
3 氈包青釉瓷器與霽藍釉及茄皮紫釉的燒造工藝差異
以前國內從事瓷器專業研究的工作者對氈包青釉瓷器與霽藍釉和茄皮紫釉的劃分不明確,或者說界限模糊。霽藍釉無論是官窯制還是民窯燒造,都有比較多的產品,茄皮紫釉雖為名貴產品但并非不可遇,而氈包青釉的瓷器的存世量還是比較少的。我們下面就通過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幾件霽藍釉瓷器和茄皮紫釉瓷器的比較,對它們的燒造工藝進行分析,弄清楚它們的區別所在。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代氈包青釉瓷器的種類,除了上文提到的爵杯、犧尊、大盤外,在2016年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中,還發現了一件清代氈包青釉菊瓣式花盆(圖8)。花盆口徑25厘米,底徑15.5厘米,高13.4厘米。花盆為花口式,器身以菊瓣裝飾,全身施氈包青釉,釉面藍中泛紫,施釉至花盆底部,圈足亦施釉,顯出和盤子的裹足支燒一樣的現象。但其釉面脫落嚴重,露出白胎,釉面呈現出細小開片。由此可見,此物雖然釉面較肥厚,但因非高溫燒造,導致胎釉結合不佳釉面出現脫落,依此現象可以推斷氈包青釉瓷器為中溫釉瓷。
霽藍釉是以天然的鈷土礦作為著色劑,這種鈷土礦除含氧化鈷外,還含有氧化鐵和氧化錳等,是一種高溫石灰堿釉,在做好的瓷胎上施釉,在1200~1300度的高溫下形成的。其特征是胎釉結合緊密,色澤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調濃淡均勻一致,發色也較穩定,與氈包青釉藍中泛紫的特征有所區別。
我們再以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兩件康熙霽藍釉盤為例,此種盤和上文所述氈包青釉盤區別明顯。第一件霽藍釉瓷盤雖與上文所述氈包青釉瓷盤一樣內外壁施滿釉,顏色呈寶石藍色。但因為霽藍釉是高溫燒造而成,釉面大多平整,用放大鏡觀察會看到釉面顯出大量氣泡。且霽藍釉在熔融下口沿邊緣會露出一圈白色的胎釉,亦被稱為“燈草口”,這實際是燒造過程中藍釉流動的一種現象。盤底施白釉,落雙圈兩行楷書“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圖9)。第二件霽藍釉瓷盤則是盤內施白釉,外壁施霽藍釉,其他特征與第一件霽藍釉盤一致(圖10)。再者,這兩件霽藍釉盤的圈足胎釉結合處修胎整齊,分界線明顯,可見用刀犀利果決,與氈包青釉的“裹足支燒”形成鮮明對比(圖11)。上述花口花盆圈足寬厚,但也施釉露胎,顯示出氈包青釉獨特的燒造工藝。
揚州博物館“流光溢彩——館藏元明清瓷器精品展”里就有一件藍紫相和而藍尤濃厚的清康熙氈包青釉瓷盤,被標為“清康熙霽藍釉暗刻龍紋盤”,這是值得探討的(圖12、圖13)。
茄皮紫釉是低溫釉,清代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三載:“紫色釉,黑鉛粉末加石子青、石末合成。”[6]由此可知其著色劑為錳,釉料中鐵、鈷起調色作用,經800~850攝氏度燒成。顏色似茄皮,故稱“茄皮紫釉”,由于配料和窯火氣氛變化有別,紫釉呈色不同,有深、淺茄皮紫之分。我們再以三件茄皮紫釉瓷器為例談與氈包青釉瓷器的對比。南京博物院藏兩種形制類似但釉色有濃淡之分的清代茄皮紫釉瓷盤。一件是清雍正茄皮紫釉暗刻石榴紋瓷盤(圖14),口徑20.5厘米,足徑13厘米,高4.4厘米。敞口,弧壁,圈足。盤內壁素面,外壁暗刻纏枝石榴紋一周,紋飾清晰可見,罩淺茄皮紫釉,底部白釉,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兩行雙圈楷書款。還有一件是清雍正茄皮紫釉暗刻八吉祥紋瓷盤(圖15),形制和上件相同,內壁素面,外壁暗刻一周八吉祥紋(輪、螺、傘蓋、花、罐、魚、腸)紋飾,紋飾不如上件清晰。外罩深茄皮紫釉,并帶有強烈的蛤蜊光澤。款識亦相同。這兩件茄皮紫釉盤的圈足胎釉結合處修胎整齊,界線分明,也與氈包青釉區別明顯。
南京市博物館于2017年初舉辦的“勝代崇文物官窯重楷模——景德鎮·南京明清官窯瓷器聯展”中有一件清代茄皮紫釉瓜棱形扁瓶(圖16),這是茄皮紫釉瓷器中的一件典型代表作品。此瓶口沿呈花口式,直頸,腹呈瓜棱式。全身施茄皮紫釉,釉色深紫泛亮,釉施至底足處,已微露白胎。此特征與上文所提氈包青釉犧尊的施釉及底部且中心露胎有三個近似粘沙支燒點的現象成鮮明對比。
細觀兩種對比,差距比較明顯。行業內尚未對氈包青釉的化學成分進行科學檢驗。只能推測氈包青釉是一種石灰堿釉,含氧化鈷和氧化錳兩種天然著色劑,所含比例不同,呈現出來的顏色就會發生變化,如氧化鈷所占比例稍大時釉面顯藍色,氧化錳偏多時釉面便會泛紫。釉面流動性差,施釉均勻。
上文介紹的清代康熙時期的氈包青釉瓷盤施釉至圈足處,盤底施白釉,底足釉的邊界線往往不齊,但會留下五個對稱的支燒點,說明此種盤是用支燒工藝燒造而成。業內人士稱之為“裹足支燒”(圖7),包括清氈包青釉犧尊、花盆等,也都用此燒造技術。到了清代乾隆時期,氈包青釉瓷盤發展為全身施釉,圈足露出一圈白胎,胎釉界限分明。底部暗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楷書雙圈款(圖17)。這是霽藍釉和茄皮紫釉瓷盤不曾出現的燒造工藝和落款方式,也是除了燒造溫度之外的不同之外,更是區分氈包青釉和霽藍釉及茄皮紫釉的一個重要依據。
4 總結
總之,色多而純的顏色釉瓷器是中國古代制瓷業的一個特殊種類,在古代陶瓷體系里無論從品種、用途及藝術價值上看,都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氈包青釉瓷器則是一小眾品種,其從顏色、燒造工藝的角度看,終究還是與霽藍釉及茄皮紫釉有區別。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色也深于藍,且微微泛紫。它既不像高溫霽藍釉那樣明亮輕快,也不像茄皮紫釉那樣時而色紫而深厚,時而色淺而顯紅,帶給人們含蓄之美。氈包青釉色澤深濃,給人以渾厚深沉之感。相信隨著文物資料和科學儀器測試的不斷豐富和進步,我們對氈包青釉的定名和深入研究,會使其露出更加準確的身份。
參考文獻
[1]寂園叟.陶雅[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
[2]許之衡.飲流齋說瓷[M].合肥:黃山書社,1992.
[3]王志敏.學瓷鎖記:王志敏文物鑒定1000例[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4]龔良.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窯瓷器[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5](清)允祿等.皇朝禮器圖示[M].揚州:廣陵書社,2004.
[6](清)藍浦,鄭延桂.景德鎮陶錄[M].合肥:黃山書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