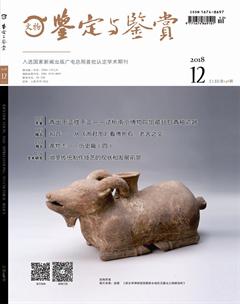西江流域書(shū)院文化的開(kāi)端
徐義偉
摘 要:星巖書(shū)院由北宋名臣包拯創(chuàng)辦,是西江流域最早的書(shū)院,對(duì)西江流域的教育和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文章對(duì)星巖書(shū)院的創(chuàng)辦過(guò)程和影響進(jìn)行了梳理,并對(duì)包公創(chuàng)建星巖書(shū)院的原因進(jìn)行了分析。
關(guān)鍵詞:星巖書(shū)院;過(guò)程;影響;原因
星巖書(shū)院由北宋名臣包拯治理端州期間(1040—1042)創(chuàng)辦,是西江流域最早的書(shū)院。星巖書(shū)院在傳播中原文化、培養(yǎng)人才、移風(fēng)易俗、改善西江流域教育等方面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創(chuàng)辦星巖書(shū)院是當(dāng)時(shí)北宋政府重文背景下,包公力圖改變端州狀況而采取的應(yīng)對(duì)措施。
1 包拯創(chuàng)建星巖書(shū)院
關(guān)于包公創(chuàng)辦星巖書(shū)院,古籍古志多有記載,如明萬(wàn)歷《肇慶府志》載:“星巖書(shū)院,在寶月臺(tái),宋守包拯建,遺址尚存。”清康熙《肇慶府志》載:“縣北百步為寶月臺(tái)。平地突起,望之如臺(tái)。宋包拯建星巖書(shū)院其上。”古籍記載星巖書(shū)院的創(chuàng)辦者是宋朝著名清官包拯,院址在寶月臺(tái)。那么包公為什么會(huì)選擇在寶月臺(tái)創(chuàng)辦書(shū)院呢?
包公選址寶月臺(tái)創(chuàng)辦書(shū)院,主要是因?yàn)閷氃屡_(tái)的地理環(huán)境非常適合讀書(shū)學(xué)習(xí)。寶月臺(tái)前依西江,后靠北嶺,東有景山崗,西有龜頂山,山護(hù)水偎,龍藏氣聚,山丘隆起,如月如臺(tái)。依山傍水,環(huán)境清幽,正適合創(chuàng)建書(shū)院、研書(shū)講學(xué)。書(shū)院大多建在形勝之地,重視自然對(duì)人的陶冶,注重人與周圍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幽靜、秀美、宜人的環(huán)境,是包公選址寶月臺(tái)創(chuàng)建書(shū)院的重要原因。
寶月臺(tái)風(fēng)景特色也是包公選址寶月臺(tái)的重要原因。《蕉軒隨錄續(xù)錄》載:“端州北門(mén)外寶月臺(tái),四面荷花,星巖拱峙,為名勝之最。”每當(dāng)池塘荷花盛開(kāi),清遠(yuǎn)溢香,景色怡人,與包公年輕時(shí)讀書(shū)的地方——香花墩有幾分相似,是讀書(shū)學(xué)習(xí)的絕佳之地。修建書(shū)院既是包公教育理念的實(shí)踐,也體現(xiàn)了包公對(duì)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特性的向往,表達(dá)了他“清心為治本”的志向。
包公除了創(chuàng)辦書(shū)院,還在端州城西景星坊創(chuàng)建了文昌祠。文昌祠位于“城西景星坊,宋郡守包拯建”。文昌本是天上的星官名,又名“文曲星”“文星”,是神話中主宰功名、祿位的神,舊時(shí)讀書(shū)人期望達(dá)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對(duì)文昌崇祀有加。包公創(chuàng)辦文昌祠,是為激勵(lì)讀書(shū)人努力學(xué)習(xí),效力國(guó)家,弘揚(yáng)不為自己求安樂(lè),但愿眾生得離苦的奉獻(xiàn)精神。
面對(duì)民族眾多、州貧民困的狀況,包公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善了端州的教育狀況,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中原文化在嶺南的傳播,加速了民族融合,整個(gè)端州的社會(huì)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志書(shū)稱“地方千里,不識(shí)盜賊,水疍山瑤,向化奔走,恩威并著,歲乃太和,稱為神明之政”。
2 星巖書(shū)院的影響
星巖書(shū)院不僅是西江地區(qū)最早的書(shū)院,也是廣東省較早的書(shū)院之一,是西江流域書(shū)院文化的開(kāi)端,它起到的作用也不僅僅是縮短了嶺南和中原地區(qū)的文化差距。星巖書(shū)院建立時(shí)就有以儒家文化訓(xùn)化時(shí)人的愿景,隨著書(shū)院的創(chuàng)辦儒家文化開(kāi)始在端州發(fā)芽,并最終確立了儒家文化在端州的正宗地位,地處偏僻的端州因此得以融入中華主流文化圈。
2.1 文脈傳承至今
星巖書(shū)院創(chuàng)辦后,雖有廢置,但辦學(xué)的歷史長(zhǎng)達(dá)500余年,宋元時(shí)期曾一度是肇慶地區(qū)唯一的一所書(shū)院,在清末辦學(xué)達(dá)到頂峰,為肇慶最著名的兩所書(shū)院之一。新中國(guó)成立后,書(shū)院發(fā)展為現(xiàn)在的肇慶市第一中學(xué),文脈得以延續(xù)至今。
星巖書(shū)院的發(fā)展并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歷史上屢遭廢置,但都涅槃重生,可以說(shuō)是風(fēng)雨兼程、愈挫愈勇。星巖書(shū)院的復(fù)辦,多是由知州、知府主導(dǎo)完成,由《星巖書(shū)院歷史沿革表》(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除在南宋時(shí)期由黃執(zhí)矩恢復(fù)星巖書(shū)院外,都是在地方行政長(zhǎng)官或政府的主導(dǎo)下完成。這一方面體現(xiàn)了包公作為地方行政長(zhǎng)官創(chuàng)辦星巖書(shū)院良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星巖書(shū)院的影響力。
清咸豐五年,知府郭汝誠(chéng)沒(méi)收觀音殿,改辦龍圖書(shū)院,就是為了紀(jì)念包公。其實(shí)在星巖書(shū)院停止辦學(xué)的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寶月臺(tái)是以紀(jì)念包公的寺庵、包公祠或園林的形式而存在,這也體現(xiàn)了包公對(duì)后世的影響。
2.2 官吏效仿,重學(xué)興教
包公以地方知州身份在端州首興書(shū)院,重學(xué)興教,對(duì)后任為官者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星巖書(shū)院文脈延續(xù),多賴后任為官者的努力,紀(jì)念或效法包公,前文已有說(shuō)明,不再贅述。然而,進(jìn)入明季,隨著王陽(yáng)明心學(xué)的傳播,書(shū)院教育一度興盛,在肇慶地區(qū)相繼建立了25所書(shū)院,其中只有4所是民間創(chuàng)辦,其他21所皆為當(dāng)?shù)刂⒅h或總督等政府官員創(chuàng)辦(表2)。肇慶官員重視教育,熱衷創(chuàng)建書(shū)院,固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包公首創(chuàng)之示范作用,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星巖書(shū)院的創(chuàng)辦帶動(dòng)了肇慶書(shū)院文化的興盛。明代,廣東書(shū)院數(shù)量總數(shù)達(dá)168所,其中肇慶地區(qū)有書(shū)院25所。清代,全國(guó)可查的書(shū)院達(dá)3868所,珠江流域約占38%,從康熙至光緒(1666—1901),肇慶書(shū)院有73所。由明清兩朝肇慶書(shū)院數(shù)量占廣東書(shū)院比例可以看出,肇慶地區(qū)書(shū)院文化是比較興盛的,尤其清朝端溪書(shū)院發(fā)展為影響整個(gè)廣東省的著名書(shū)院,肇慶書(shū)院文化之盛可見(jiàn)一斑。
2.3 名人雅士吟詩(shī)傳頌
星巖書(shū)院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它對(duì)歷代名人雅士的吸引力上。清代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星巖書(shū)院是以遺址的形式存在,但這并不妨礙有學(xué)之士對(duì)其的喜愛(ài),來(lái)肇文人多會(huì)造訪書(shū)院遺址,其中不乏當(dāng)時(shí)的大儒袁枚、全祖望、梁鼎芬、朱一新等人,且多有詩(shī)文留下。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清代有關(guān)星巖書(shū)院的詩(shī)文近20首,袁枚曾寫(xiě)有文章《游端州寶月臺(tái)記》,梁鼎芬曾為星巖書(shū)院眾綠廳題聯(lián):“招邀數(shù)君子;沉醉萬(wàn)荷花”。不僅如此,當(dāng)時(shí)許多著名學(xué)者都曾為復(fù)辦星巖書(shū)院而積極奔走。梁鼎芬曾修治星巖書(shū)院舊址軒窗,就而著書(shū),聚徒講學(xué);朱一新曾為復(fù)建星巖書(shū)院而積極奔走,后因經(jīng)費(fèi)不足而止;曾國(guó)藩之侄曾紀(jì)渠曾籌集經(jīng)費(fèi)七千金,復(fù)建星巖書(shū)院,但因去任而未成。晚清大儒陶邵學(xué)在光緒二十二年任星巖書(shū)院主講,連任八年,培養(yǎng)士風(fēng),磨礪“實(shí)學(xué)”,使星巖書(shū)院與端溪書(shū)院并稱于時(shí)。
2.4 促進(jìn)儒家文化在肇慶地區(qū)的傳播
星巖書(shū)院的創(chuàng)辦是端州城破天荒的大事,書(shū)院以傳播儒家文化為宗旨,因此偏遠(yuǎn)的端州城從此開(kāi)始了有規(guī)模的儒家文化系統(tǒng)教育,書(shū)院教育教化人心,儒家文化在端州地區(qū)慢慢生根發(fā)芽,并最終確立正宗地位。
包公治端時(shí)期,端州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60%以上,就算是漢族群體普通民眾也很少有機(jī)會(huì)接受系統(tǒng)的儒家文化教育,民眾文化素質(zhì)比較落后,民族沖突時(shí)有發(fā)生。星巖書(shū)院創(chuàng)辦后,在北宋辦學(xué)達(dá)38年之久,對(duì)持續(xù)、系統(tǒng)傳播儒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南宋復(fù)辦后,成為傳播理學(xué)的重要場(chǎng)所,遺址明朝初年仍存在,傳播儒學(xué)的功績(jī)是難以估量的。星巖書(shū)院和后來(lái)逐漸建立起來(lái)的地方官學(xué)一起,最終確立了儒家文化在端州的正宗地位,地處偏僻的端州逐步融入了中華主流文化圈。
3 創(chuàng)建原因分析
包公創(chuàng)建星巖書(shū)院的原因,一是宋朝政府重視書(shū)院建設(shè);二是端州當(dāng)時(shí)文化教育狀況落后,與中原地區(qū)存在很大差距,嚴(yán)重影響了社會(huì)發(fā)展。
3.1 宋朝政府的鼓勵(lì)政策,促進(jìn)了書(shū)院的發(fā)展
宋初采取了一系列發(fā)展文化、教育的政策,推動(dòng)了書(shū)院教育的興盛,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
興文重教,鼓勵(lì)創(chuàng)辦書(shū)院,書(shū)院講學(xué)之風(fēng)盛行。
宋既統(tǒng)一海內(nèi),戰(zhàn)亂漸平,民生安定,文風(fēng)日起,讀書(shū)士子紛紛要求讀書(shū)就學(xué),國(guó)家也需要大批治術(shù)人才。但是,宋初朝廷還來(lái)不及興學(xué)設(shè)教,無(wú)暇顧及文教事業(yè),也沒(méi)有充足的財(cái)政實(shí)力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對(duì)民間興起的書(shū)院教育采取了鼓勵(lì)政策。太宗、真宗、仁宗皇帝都重視書(shū)院建設(shè),大力支持漸興的書(shū)院,連續(xù)不斷地賜田、賜額、賜書(shū)、召見(jiàn)山長(zhǎng)、封官嘉獎(jiǎng),對(duì)書(shū)院加以褒揚(yáng),“書(shū)院之稱聞?dòng)谔煜隆薄W运翁娼≡曛了稳首趹c歷三年(960—1043),凡84年,興復(fù)創(chuàng)建書(shū)院約21所,以“四大書(shū)院”為代表的多所著名書(shū)院和位居京師的國(guó)子學(xué)一起,實(shí)際構(gòu)成從地方到中央的官學(xué)體系,承擔(dān)著國(guó)家最主要的教育任務(wù)。在中原地區(qū)興起了書(shū)院建設(shè)的熱潮,影響遍及全國(guó)。
科舉錄取人數(shù)增多,取士范圍擴(kuò)大,激發(fā)了天下士子求學(xué)之心。
北宋定鼎,社會(huì)趨向穩(wěn)定,急需能治理國(guó)家的人才,錄取人數(shù)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取士范圍也打破門(mén)第界線,面向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寒庶之族、工商階層登科者比比皆是。《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卷十六》載宋太祖開(kāi)寶八年(975)曾下詔:“向著登科名級(jí),多為勢(shì)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wú)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jìn)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宋史·選舉志·卷一百五十五》載宋太宗言:“朕欲博求俊顏于科場(chǎng),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得政治之具矣。”宋朝最初的兩位皇帝,治國(guó)心切,求才若渴,改革科舉制度,擴(kuò)大取士范圍,不遺余力選拔人才,為后來(lái)的皇帝做了榜樣,也激發(fā)了天下士子的求學(xué)之心,另一方面也促進(jìn)了書(shū)院教育的發(fā)展。
與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辦學(xué)校招生范圍擴(kuò)大,入學(xué)資格降低。表3還只是紙面上的規(guī)定,太學(xué)實(shí)際上已敞開(kāi)大門(mén),招收“遠(yuǎn)方孤寒之士”。這對(duì)讀書(shū)求學(xué)的促進(jìn)作用是巨大的,天下寒門(mén)學(xué)子看到了希望,有了機(jī)會(huì),也無(wú)疑進(jìn)一步刺激了對(duì)書(shū)院的需求。
3.2 包公所面對(duì)的端州教育、文化狀況,是包公創(chuàng)辦星巖書(shū)院的直接原因
當(dāng)時(shí)的端州,蠻荒偏遠(yuǎn),交通不便,瑤僚聚居,文化貧乏,教育落后,中原官員不愿意到端州任職。
3.2.1 端州荒遠(yuǎn)
古端州地處嶺南,屬?gòu)V南東路,與中原之間五嶺橫隔,交通阻塞,瑤僚聚居,語(yǔ)言不通,有“殺人祀鬼”“巫覡挾邪術(shù)害人”的陋俗,被稱為蠻荒之地,文化貧乏。
3.2.2 無(wú)官治理,急需人才
古端州屬蠻荒之地,官員寧可賦閑,也不愿到廣南為官。自秦漢至唐宋,古端州多為朝廷貶謫流放罪官之地,到端州當(dāng)官,也就和流放差不多。由于廣南路缺官嚴(yán)重,北宋時(shí)期實(shí)行嶺南官員“南選”制度,由地方自行選拔“攝官”,沒(méi)有品級(jí),只權(quán)攝政事。“攝官”沒(méi)有升遷機(jī)會(huì),大多無(wú)心治理,有心貪婪,廣南“無(wú)治”。宋仁宗時(shí)期實(shí)行“蔭官”,由朝廷派任廣南路的州一級(jí)官員,但多為紈绔子弟,知識(shí)淺薄,無(wú)法管治好嶺南,當(dāng)?shù)匕傩沼性┯锌酂o(wú)處申訴,民不聊生。端州缺少有能力的官員是端州社會(huì)發(fā)展滯后的重要因素。
3.2.3 文教落后
端州無(wú)官學(xué),也無(wú)書(shū)院,系統(tǒng)培養(yǎng)人才的機(jī)構(gòu)缺失,教育落后,與中原地區(qū)書(shū)院文化昌盛的景象存在很大反差。《宋史》記載:“自仁宗命郡縣建學(xué),而熙寧以來(lái),其法浸備,學(xué)校之設(shè)遍天下,而海內(nèi)文治彬彬矣。”宋仁宗時(shí)期官學(xué)制度才逐漸建立,而到全國(guó)建起完善的官學(xué)體系,要等到熙寧年間。端州偏遠(yuǎn),歷史上從沒(méi)建立過(guò)官學(xué),直至在朝廷開(kāi)展的興辦官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端州知軍州事朱顯之才在端州創(chuàng)辦州學(xué),約在1043—1048年間,那已是包公離開(kāi)端州后的事情。本地人才匱乏,影響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長(zhǎng)足發(fā)展。
文化貧乏,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包公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改變端州落后的面貌。興辦書(shū)院,推行教化是其中重要一環(huán),他希望通過(guò)書(shū)院教育,培養(yǎng)人才,促進(jìn)端州社會(huì)的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
在州困民窮的情況下,包公克服重重困難,毅然創(chuàng)辦了星巖書(shū)院,重視文化教育。星巖書(shū)院成為西江流域書(shū)院文化的濫觴,它的創(chuàng)辦及所產(chǎn)生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和重視。
參考文獻(xiàn)
[1](明)鄭一麟,葉春及.萬(wàn)歷肇慶府志[M].明萬(wàn)歷十六年刻本.
[2](清)史樹(shù)駿,區(qū)簡(jiǎn)臣.康熙肇慶府志[M].康熙十二年刻本.
[3](清)方濬師.蕉軒隨錄續(xù)錄[M].盛冬鈴,點(diǎn)校.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5.
[4][5](清)屠英.道光肇慶府志·卷七[M].道光十三年刻本.
[6]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