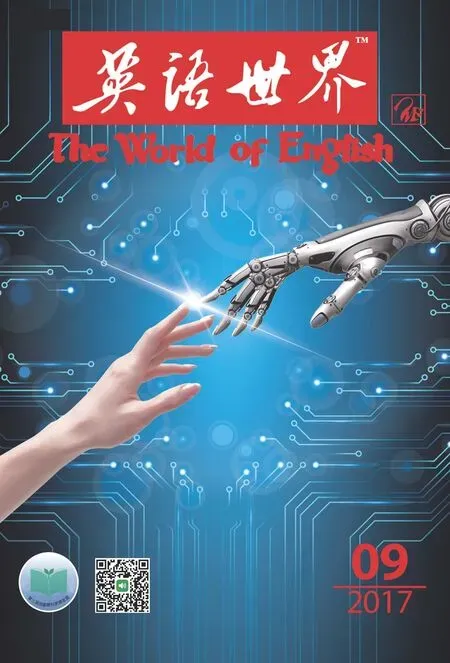翻譯理論怎樣幫助翻譯實踐
文/葉子南
介紹了這么多中西翻譯理論,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難道從事翻譯實踐的人非得學習這些理論嗎?回答應該是很明確的:譯者并非一定要學習翻譯理論。我們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個回答,比如一些公認的優秀翻譯家并沒有系統地學習翻譯理論,特別是西方的翻譯理論,但是他們的譯著卻非常成功,比如傅雷。你可以說,傅雷肯定知道“信達雅”,但他肯定沒有學習過對等和目的論這類譯論,因為傅雷譯筆飛馳時,這些理論還沒有問世。傅雷自己總結了“神似”的理論,但那也基本是源于實踐的一點兒心得體會。其實,老一輩翻譯家都沒有像我們這樣在翻譯系學過翻譯,不用說翻譯理論,連翻譯實踐也沒學過。什么詞性轉換、正說反譯之類的技巧,都是后人總結他們的翻譯方法時總結出來的,他們自己并沒有想到這些技巧。對他們來說,這樣轉換、這樣調整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事,不用刻意去學習,翻譯時根本不會想到技巧。他們很多是外文系或其他文科專業畢業的學生,因為愛好或其他原因,開始從事翻譯,終于碩果累累。但是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中外兩種語言基礎扎實,對于語言、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本質有非常深入的體會,這種體會可以是理論的,但也完全可以是經驗的。所有這些經驗,如果進行整理,完全可以成為文學或翻譯理論,但對于翻譯實踐者來說,沒有系統整理的、分散的、點點滴滴的想法有時反更有益處,因為翻譯實踐遇到的問題并不是系統的,而是分散的、點點滴滴的。所以“沒有理論的理論”(theorizing without theory)也許是理論切入實踐的一個相當不錯的角度。另外,還有一點大家都忽視,老一輩翻譯家雖然沒有翻譯理論的熏陶,但他們語言文學造詣都很高深,而翻譯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語言文化理論。
但是難道學習翻譯理論就毫無益處嗎?當然不是,如果理論學習得法,完全可以使譯者如虎添翼。有人說,學了那么多東西,反正沒用,學它干什么?理論虛無的態度并不應該推崇。比如醫學院的學生都要學習解剖學,需要背誦很多東西,如“一嗅二視三動眼;四滑五叉六外展”十二對腦神經都必須背出來。但假如一個學生畢業后專攻足科疾病,這些腦神經的名稱也許用不上。但是作為醫學科學的學習,對腦神經的了解卻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很難斷定在與腦神經無關的科目中就永遠不需要有關腦神經的知識。所以,如果我們能學習一些理論知識,并能正確運用這些知識,理論就完全會成為我們的幫手。比方說,描寫學派重目標語言的理論是否會給我們啟發,在翻譯中影響我們的決策? 目的論是否會在我們原本不敢大膽刪除時給我們這樣做的底氣?對等理論是否會幫助我們不過度游離原文、造成錯譯?理論幫助我們的空間其實是很大的。
但如果理論應用不當,完全可能適得其反,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我們自己并不是真正熟悉某個理論,卻要在翻譯實踐中套用上去,這樣結果往往不好。在翻譯這臺“戲文”里,理論不應該是總在“前臺”晃悠的演員,它應先由譯者消化成自己的知識,成為譯者雄厚的內涵,然后在背景處潛移默化地影響他的決策,而不是對號入座地硬把某個理論與某個譯法配對成雙。這就像說笑話一樣,硬說出來的笑話很難奏效。“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翻譯理論之于實踐,也應該是自然的應用,而不是硬逼出來的。譯者最終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好的譯文,而不是應用一個好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他們這批優秀翻譯家的理論基礎其實是非常厚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