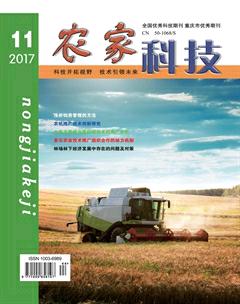仁愛思想的起源
王維民
摘 要:仁愛是中華傳統中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觀念。一般認為,仁愛思想集中體現在儒家政治哲學中,但通過文字學、文獻學的分析看,這一思想體系是中華人文地理的自然演義,儒家只是博采眾長,將其提煉萃取而已。
關鍵詞:仁愛;儒學;中華文化
《說文解字》釋“仁”:“親也,從人從二。”徐鉉解釋說:“仁者兼愛,故從二。”這說明,“仁”不是個體的生命體驗,而是一種超越個體的行為方式和道德原則,它必須滿足二人以上的共同體組織條件。段玉裁引《中庸》“仁者,人也”說,人的意思是“相人偶”,即它不是反身、自我的,而必須有一個對象,彼此互相致敬與相親近。又引《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及“仁,人心也”兩種不同的說法,指出“仁”既是一種人類行為,又是一種心靈追求。當然,我們對“仁”的認識,更多來源于孔子。在《論語》中,“仁”是一個標志性的高頻詞。孔子對“仁”的定義可謂多矣。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仁者其言也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茍志于仁矣,無惡也。”“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當仁不讓于師。”“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既是言行,又是心理,也是禮儀,還是政治。但不論如何解說,“仁”都代表著一種克己、利他、奉公以及親善、關懷、尊重。這正是一種良好的共同體之間人與人關系的最佳選擇。“仁”的理念在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空前發展,成了民族道德的典范和藍本。經過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巨子的多方位多角度解釋、補充,“仁”幾乎已經獲得了中華思想最佳代言者的地位,再由宋明理學家的發展拓寬,上及君王,下達百姓,無不以“仁”為思想修養和行為規范的最高準則。
那么“愛”呢?依照《說文解字》,“愛”的本義是行走貌,這應該是愛慕、私相親密的形象刻畫,表達的是一種隱秘、隱藏的心理感受。后來更加上恩惠、憐寵、喜好、吝惜等多重意義。同樣,這是一種面對他者的情感方式,具有與“仁”相通的共同體意義。孔子釋“仁”為“愛人”,孟子的仁政愛民、“保民而王”,又體現了儒家將“仁”和“愛”并列齊觀,相提并論的人情、人性特色。仁愛二義的并駕齊驅,是民族心理和道德建設成熟的體現,也成為治國理政、和諧萬姓的法寶。它是政治的、心靈的、哲學的交集公約,是文明傳統的精髓所在。
我們這里談論的仁愛,是以儒家的思想范例,其實,中華思想是千流歸海的浩蕩歷程,“仁愛”的思想早就是民族共識了,孔孟不過是集大成者罷了。人類的生命關切,必然不是自我實現的,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已從最初意義上涉及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仁”和“愛”。老子雖然有“大道廢,有仁義”的反說,但他提倡的“道”、“德”與后來的“仁”、“愛”是分不開的,某種意義上完全重合,反映的是先民從原始的小國寡民、分散獨處到統一聚合,形成民族共同體的演進過程。他的許多觀察如“天之道,以有余奉不足;人之道則不然,以不足奉有余”反映了循天道任自然的平等思想,這本身是仁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仁愛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墨子“尚同”也是對平等思想的追求。“兼愛”、“非攻”、“愛無差等”,所反映的也正是對珍愛生命、返歸淳樸的先民遺德的追懷。究其實,由于中華民族自始生息繁衍在東亞大陸上,這里地大物博,天賜豐厚,憑借著溫柔敦厚,刻苦耐勞,過著和樂豐足的生活,無事于無謂的爭奪擾攘,久而久之,鑄成了順應天時、憑借地利、依靠人和的自然主義的哲學觀。即使這種觀念中在后來走向大一統的民族國家過程中有所失落,諸侯紛爭,列國戰亂,但是基本的道德面目卻未曾置換,而是轉圜變易,以適應新時代的姿態,重新寫進民族性格之中。儒家的超群出眾,終居百家之冠,成為此后三千年國家哲學思想的源泉,正是這種繼承與發展的雙重性所決定的。在孔孟思想中,傳統與時代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最終將仁愛定為民族道德基石。它既不同于復古的老莊一派的“返樸”、墨家的“兼愛”以及陰陽術數家的自然主義,也避免了走向法家、縱橫家的鐵血主義、獨裁思想的危險,而是強調順時而為,剛柔并濟,中庸諧和的原則。
任何一種成熟了的道德思想最終會演化為恒定的政治哲學。仁愛思想既然成為中華傳統道德的共識,也有與之相匹配的政治格局。也正是政治實踐,鞏固了儒家仁愛思想的獨尊地位。仁愛從個人道德上升為共同體精神,對此,上古以來的政治思想都有表述。中國人已習慣于將天下太平稱作堯舜之世,就是稱頌上古賢君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天下歸心的風范。而對桀紂的否定,是針對其喪失仁愛,失去民心而遭到滅亡的命運。總結上古和當世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著作《呂氏春秋》,其中有《順民》、《愛士》、《上德》、《愛類》等篇,都闡述了先王時賢以仁愛致勝的道理。類似的著作《淮南子》也一再強調這一原則。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修務訓》里“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這也是仁愛二字聯袂使用的初始,但所述事實是上古軼事,充分表明了仁愛原則不但是先民的社會風習,而且早就成為政治準則。這兩部書分別成書于秦漢,由當時具有政治野心,但又不在正統王權地位的兩位政治家——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發起,網絡匯集了各門各派的海量人士作為編篡者,可以說王權性質和民間性質俱備,所以可以確信的是,早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代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之前,仁愛政治思想就已深入人心了。儒學思想的發端以及最終勝出,在于回應時代人心的變遷和政治的暫新局面。孟子說孔子之偉大在于他是“圣之時也”,孔子也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里的“時”與“權”,就是思想家如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回首過去,展望未來,給出利國利民的最佳答案。隨著中華帝國大一統體制的深入人心和日漸鞏固,仁愛這一道德律條上升為國家意志,崇尚仁愛哲學的儒學也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言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