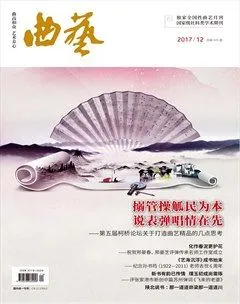謝謝你給了我“面子”
孫立生
亞峰小先生:
你好。叫你一聲小先生,絕無嘲諷、挖苦的意思,乃是我這個年逾六十三歲之人的畢恭畢敬;先生之前的“小”,也和你的年齡無甚關系,只是覺得相較于我,你在諸多方面具備做先生的能力,但“我”,畢竟是一個很小的個體,將你定格在“小”先生,含有我的期待,期待著你能在曲藝乃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影響下,以自己更加美好的德行、智慧、作為、作品等,早日獲取更多“學生”的青睞、追隨。我還喜歡你的名字,“亞峰”,不到“頂峰”的高峰,于是便有夢想、熱情,向上攀登。
我緣何向你這樣一個“娃娃”討好,以至于不顧年長你幾十歲的尊嚴、身價甘做學生?這當然緣于我的價值觀與審美觀。所謂能者為師,你這個“曲藝小先生”著實有令我這個“曲藝小老頭”折服的玩意。這不,它們逼得我都有些不吐不快了。
我服氣,我的“意識”不如你。我的作為頂多只是對曲藝閉目反思而已,而你對曲藝卻是熱情行動。誠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在自己困惑迷茫的時候,不怨天尤人,而是勇于反思、反省,亦不失為一種姿態,但對比你的“用作品說話”顯然略遜一籌。我曾在多個場合強調“傳承發展‘本為本”的觀點,呼吁新時代需要具備新時代品質的曲藝新作,大概是人微言輕或者表達方式的乏味等原因,最終皆以自言自語告終。可是你師亞峰卻與我大相徑庭。記得2016年7月下旬,在第九屆中國曲藝牡丹獎合肥賽區的角逐中,59個參賽作品與來自近30個城市和地區,203位曲藝名家、新秀登臺亮相,你以自編自演的山東快書《面子》獲得姜昆、崔凱等曲藝專家評委與現場觀眾的一致好評。作為現場評委之一,大賽過后我曾對優秀山東快書演員陳振說:“即使你的表演幾近完美,但,師亞峰的《面子》對比你表演的傳統作品《武松打虎》,顯然更貼近這個時代以及廣大受眾的生活……”記憶中陳振頻頻點頭,心悅誠服地告訴我:“師亞峰令我們參賽的很多選手都意識到了新作品的重要性,《面子》是他自編自演的作品,所以在臺上能夠隨心所欲、揮灑自如;一看他就演出過無數場次了,與現場觀眾交流、互動非常默契。”陳振的話引起我很長時間的思考。2017年11月18日,我在與相聲名家唐愛國共同主講的山東書城“文學經典論壇”上說,相比經典文學作品本身,所有圍繞它的演講、評論等都相形見絀。說唱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即使我巧舌如簧,也比不上唐愛國表演一段好相聲能夠證明其“經典力量”;一萬個“相關活動”都取代不了一部經典作品的價值。于是,德國詩人歌德在詩劇《浮士德》中留下的那句話才成為名言:“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
很服氣,我的“能耐”不如你。我寫的作品多是自我抒情,而你的《面子》卻是為眾而生。并非自貶,雖亦被人稱之“曲藝作家”,但我畢竟離開舞臺多年,與恩師趙連甲及姜昆、崔凱、王宏、李立山、楊子春、楊魯平、崔琦,等等,那些始終堅持為舞臺實踐寫作的曲藝作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即使我獲得過中國曲藝牡丹獎文學獎的作品,亦是有意回避了曲藝須臾離不開的趣味,而多在情感演繹、表達上下些笨功夫。在《曲藝》上讀過你寫的唱詞《喬派往事》,在合肥欣賞過你自編自演的山東快書《面子》,品味其中美妙的情趣,當時便有自嘆弗如之感。后來專門找到本子又重讀一遍,當讀到“我說這話恁不信,有一段故事對恁談,說的是無名省難查縣,找不到村的王孬蛋……那位說:哎,你別說啦,有叫孬蛋的么?小名。大名叫什么?大名叫? 俺不告訴你。萬一有個重名的人家不揍我?反面典型,我說是誰誰都不好受,說到誰誰都不待見。因此咱就用這么個無名省難查縣,找不著村的小孬蛋……”我默讀著其中這類俯拾即是的夾敘夾評、似說似唱、自然貼切、趣味橫生的描述,竟忍俊不住地多次笑出聲來。我也是作者,對文字創作之艱辛有極為深刻的體味,有時寫罷一篇文字就像“死過一回”,從結構到文字,以至于將每一個字、詞安置在它最合適的地方,談何容易!年紀輕輕的你面對諸多誘惑,竟然坐得住“冷板凳”,將說唱文學的趣味與尺度拿捏得如此自然、合適,這豈止令我慚愧不已,準確說,應是欣賞有加。其實,換種視角,對你師亞峰的認可也是對我本人曲藝觀的肯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眼里與心里的曲藝家:“雖然沒學歷的學生,但生活逼著他們學習歷久不倦;雖是沒名字的作者,但給個‘梁子編出的段子個個都貼近實踐;雖是沒編制的樂隊,但自拉自唱或用板敲著節奏可以隨機應變;雖是沒影子的導演,但他可以揚長避短讓自己的個性、絕活等得到最佳呈現;雖是沒講臺的教師,但老百姓覺得與之沒有距離、彼此親密無間。”誠然,你或許并沒有抵達如此境界,但,我卻堅信,你,正朝著這個方向行走……
真服氣,我的“熱愛”不如你。我對曲藝的熱愛或多或少地摻雜了一些“功利”,而你對曲藝的熱愛遠比我的情感“純正”許多。在合肥,你一上臺便令我一驚:頭發理得半長不短,舞臺形象雖然不丑,但與時尚靚仔相差十萬八千里。關鍵之關鍵,面對如此神圣的全國性大賽,你上臺竟敢沖著評委與觀眾極不嚴肅地來了個“現掛”:“我前邊那位山東快書演員上臺晚了,我得替他給大家解釋解釋,聽到他叫啥名字了吧?人家叫申振柱? 申振柱就是‘深圳住,想想住在深圳往合肥這兒趕,晚點情有可原啊……”是啊,觀眾、評委被你逗得哄堂大笑,可我卻沒笑出來,且心中暗暗“罵”你:師亞峰你就不怕哪個評委為你的“不規矩”扣分數么!你以為你這是下基層為老百姓演出么?坐在臺下聽你調侃的除了觀眾還有決定你參賽命運的一群專家呢……我本人這些年來獲獎的作品、文章幾乎都是無可爭議,因為我知道按評委的口味、眼光取舍、平衡,而我的骨子里當然期待你也能萬無一失捧回獎杯。你一定還記得2008年中國曲藝家協會等單位在濟南舉辦的“山東快書英雄會”吧,我在之后發表的評論文章里曾如此評價你這位“英雄會”的一等獎得主:“我喜愛師亞峰,并不完全緣于他的多才多藝,更多的則是通過他在臺上表現出的放松、不經意,插科打諢式的與評委、觀眾調侃、互動,尤其是他山東快書表演的另類,讓我發現和感悟到了一種勾人魂魄卻鮮為人見的曲藝靈性,及其‘昂首嬉笑戲權貴,躬身作揖敬平民的優秀曲藝家潛質。正因為這與當下曲藝界評價習慣相悖且與前輩先生的教導抵觸,我才愈發覺得珍惜與驚喜:它對打破當今曲藝界那種言必稱門戶,行必提師父,帶著有色眼鏡觀察評判現實,一看到或聽到新的觀點和理論,不是冷靜地分析,而是根據前輩既定標準進行指摘和抵觸的現狀,無疑是一種挑戰和叛逆。總之,喜歡師亞峰,更多的理由是我在他身上寄托了我的審美理想,即呼喚富有創新精神,個性鮮明,具有強烈的求異愿望,不甘于墨守成規和人云亦云,敢于挑戰舊思維和固有定律的新一代創新型曲藝人才。”時過境遷,10年之后,不曾想你師亞峰依然我行我素,而我卻變了,我比過去成熟了許多,成熟的標識便是由過去的求新求變變成懂得中規中矩了……判斷變與不變的價值,當然要用實踐與事實去驗證。所以,當獲悉你成為第九屆中國牡丹獎新人獎得主的時候,我服輸了:無疑,我的變是退縮,你的不變是前進。
其實,有關你的事我都挺關注的,那年在連云港舉辦第八屆中國曲藝節,我看了你師父范軍與你們主演的方言劇《老湯》,看到你將“武墜子”塑造得如此富有個性,鮮活、深刻,對你的欣賞、喜愛又增加許多。我還知道,你前些日子去青島參加了“首期中國曲協藝委會專家研修班”,且成為中國曲協山東快書藝術專業委員會最年輕的專家委員。這,當然可喜可賀,但我卻擔心榮譽來得過早,反而影響你的前程。絕不是在你高興的時候“澆冷水”,我女兒當年領結婚證后我曾給她寫過這樣一段話:“女兒領取了結婚證,舉辦婚禮喜筵,就像我當年獲得了高級職稱頭銜,與朋友聚一塊兒喝了場慶祝酒,千萬別以為真的就成了‘家。我的‘專家證就像你領取的新房房卡,沒有精神力量為依托或愛的支撐,誰敢說它就是充滿自信、溫馨如夢的‘家呢?是的,我是出過幾本評職稱用得著的書,寫過百八十篇讓人‘眼花繚亂的文章,但它大不了也就算是你新房里添置的那些時尚家具呀,如果沒有人氣,缺少底蘊,再花哨亦不過是吃飯睡覺、維持生命的房子或者就是‘工具罷了……”
說這些,無非是想告訴你,謝謝你,為曲藝贏得“面子”;“小先生”的稱謂里包含著我對你的敬意也承載著我對你的期盼…… endprint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