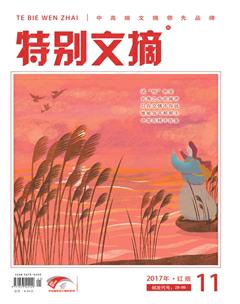小吉活了十七年
梁文道
當同桌友人問我何以神情沮喪、精神萎靡的時候,我說:“我的貓剛死,它是我看著長大的,就像女兒一樣。”結果舉座十來人竟然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干笑。
其實我是懂的,除了干笑,也許真的不會有更加恰當的反應。知道別人近親去世,自然誰也笑不出來。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從一只貓到一個家人之間畢竟有著太大的距離,這段距離甚至使人尷尬;而笑,確是面對尷尬的條件反射。
我那幾天都擺脫不了那種空白,仿佛無法參透“小吉死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死了?意思是它不再與我共存于此世嗎?
那幾天我不可抑制地想象它最后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它可有搏盡力氣地發出最后的哀鳴?抑或疲憊已極地沉沉睡去?生命究竟是什么?那具躺臥的軀體分明就有小吉的樣子,但它比起之前還爬得起來的活物到底少了些什么呢(或者多了什么)?
我再三強調它是我的“女兒”,可是我連這句話也不太敢自信地肯定。據說貓壽一載可當人壽七年,所以它走的時候已是不可思議的高齡了。
想當初它出現時仍是只未開眼的小貓,五官不停流液,醫生說活下來的機會不大。長到后來卻居然比我還老。如果這叫父女,那又是種怎么樣的父女關系呢?
它一直健康,即便到了臨終前的三個月,也還能吃能跳能跑能玩,表面看來與小貓無異。可是另一方面,我亦明白它早就不再年輕,根本是個老婦。至于我,雖然不比當年青壯,但又遠遠不能說老,起碼算不上是白發人送黑發人。不是白發送黑發,難道這是很正常的壯年人給老人家送終?莫非一個女兒在十七年間就變化成了一個長者?
在“年輕”與“衰老”的概念之外,我當如是思維:這原是兩道平行生命之不可能的相遇。
有人說,我不應該用“養”去形容與貓的交往,因為這貶低了貓的地位,貓可不能當作寵物;甚至連“它”這個字也不能用,因為“它”同樣是種小看了貓的稱謂。可是,你若真把它當人,你又怎能侵犯它的隱私,時時觀看它如廁的肅穆表情;你又怎能不顧它的意愿,隨手撫摸它的柔順毛發?
我無數次地與小吉對視,并且以我的方式理解它傳達的信息,或者將它看成是種吻前的親昵,或者將它理解為不滿的抗議;然后我反應,用自己的鼻子輕輕點觸它濕涼的鼻尖,又或許挪開身子不敢再在門縫邊偷眼望它。
由于眼神的交會,我和它產生了種種互動,就像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一樣。然而,我仍然擺脫不了一股疑惑的情緒,因為我實在無法肯定那些眼神的意義,甚至不能百分百地確定貓之“眼神”的存在。
我怎么知道貓眼的背后是什么?我如何可以確認它正在用眼睛和我交流?那雙眼如此巨大,在它的臉面上占據了好大一塊的比例;它們漆黑如深淵,吾人就算縱身一躍,亦不知何日見底。
那一雙沉靜的黑眼,我看著它,想念它,終于相忘江湖。
(摘自“牛棚讀書記” 圖/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