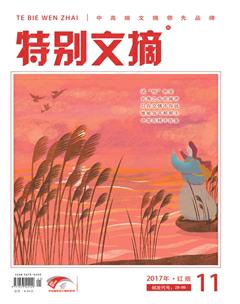談“性”色變
何申
最近無意中看了電視劇《山楂樹之戀》,內容比電影要豐富許多。看得出編劇對當年的生活很了解,于是一些細節就讓人感到真實可信。比如靜秋和老三挨在一起待了一個晚上,就以為自己會懷孕。這種事放在今天,當是笑話,但當時絕對不是。
天津市的中學,在“文革”前,名氣大的,就有男一中、女四中等學生為同一性別的學校。這類學校有一事好辦,廁所不用標男女(教師異性單有)。當時,大部分以阿拉伯數字為校名的學校,如16中、20中、21中、34中等,都男女分班,到了高中才混班。據說這種設置的緣由,是基于初中生正值男女發育又缺少理智的時期,怕弄出事來;到高中,人大些,就沒事了。
沒事當然好,但不懂事也未必是好事,為此有的學校初三開生理衛生課。我們初二趕上運動,沒上過這課。對男女分校分班,有的說好,學生單純了——其實不然,是更復雜了。我們那時在學校里,男女生之間禁止來往,假如我五姐來找我,我就得嚷嚷,讓同學知道來的是我姐。而曾經的小學女同學,有一次在操場喊我過去說了句話,給我招來好大麻煩。
猜疑起哄,說誰與誰相好、搞對象,但何為搞對象,不少人都到二十大幾了還不清楚。說來不是笑話。
說實話,我們插隊知青到鄉下后,最先接受的再教育,就是補上了生理衛生課。這課堂就是廣闊天地,馬牛羊驢豬狗是獻身啟蒙者:干活歇著,沒管住,叫驢、草驢搞到一起,大姑娘小媳婦紅臉背身,知青不知道,一女知青問另一個:他們干啥呢?那個傻乎乎地說:它累了,讓它背著。把社員腸子都要笑斷。往下,再笨的人也得琢磨人家為什么笑,一旦明白了,就聯想到人。而我們男知青得到的教育則更簡單:生產隊里有些重活兒,全是男勞力干,老司機式的隊員幾乎沒有不說葷段子的時候,你想不聽都不行。
中國歷史上的儒家社會,講的是“男女授受不親”。但人丁要興旺,男女不親又做不到。所以古人很聰明,到什么時候說什么話,在什么地方辦什么事。皇上要結婚,先看春宮圖。小姐出嫁,有老婆子點明洞房里的事。結果那個社會,雖一直都說封建、不好,可唐宋元明清,國人就沒斷種。太平天國都說好,好大勁了,跟和尚比賽禁欲。設男館女館,夫妻都不能在一起住。弄得太平軍將士都郁悶:沒參加時,雖然吃不飽,還能和老婆孩子在一個窩里偎。咋參加了,卻和出家一樣了?那洪秀全也不往長遠想,太平軍若能再堅持二十年,后備力量從哪來?
曾幾何時,國人畏“性”如虎,談“性”色變。先前,我們是啟蒙不夠,現在是引誘過頭;過去女的是捂得嚴,現在是露得多;過去新婚聽房沒動靜,現在是才認識就一夜情;過去是分居難聚,現在是同居不登記;過去是自己一個人忙活性生活,現在是有權有錢的都不閑著,找情人、會小三……
(摘自《今晚報》 圖/黃文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