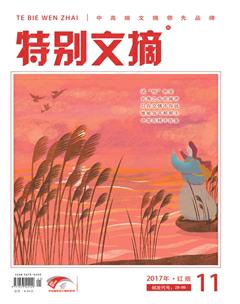壓根兒就沒有“女鬼子”
郭東風
抗日神劇中,常常會有女鬼子這一角色。不過我得讓人十分掃興地說,所有這些神劇中的女鬼子,全是編導們的意淫而已,因為日本鬼子從建軍到滅亡,壓根就沒有過女兵。
日本的武士道傳統和男尊女卑的痼疾,根本不允許女人做出挑戰男人的行為。這樣一個以男人為中心的、連女人最起碼的公民權都不給予的國家,這樣一個丈夫殺死妻子頂多只能坐一年牢的國家,怎么可能會出現與男人平起平坐甚至凌駕于男人之上的女大佐、女將軍,那些神劇制造那么多盛氣凌人的女鬼子,不是胡說八道是什么。
日本保留了大量有關包括“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在內的婦女方面的文字資料與圖片,在網上很容易搜到,如果到了日本,應該就更容易購得,可你找上一萬遍,也甭想找到他們的女人像神劇中那樣穿上軍裝拿起刀槍上戰場的記載,因為它沒有。
有記者采訪當年參加平型關戰役的老兵和當地的老人,他們都說在打掃戰場時發現日本鬼子女兵的尸體。采訪者還列舉了多位當地村民的證言,都言之鑿鑿地說他們親眼看見了鬼子尸體中的女性。
這應該不會有假。可為什么日方資料絲毫沒有記載,眾多研究二戰的專家學者也堅決予以否認呢?
其實這一點不矛盾。因為不論是當年的老兵還是當地的村民都說得不準確,他們親眼看到的那些被打死的日本女尸,并非女兵,而是侵華日軍中的女護士。
這就怪了,既然是軍中的女護士,按中國的認定標準就該是女兵呀!怎么說不是女兵呢?
這有一個對軍籍的認可在不同國家的區別問題。出于對軍人身份的看重與愛護,為抵制一些非戰斗人員穿上本應該屬于軍人的服裝占用軍人的名譽,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對于軍官與士兵等名列軍籍人員的認可是相當嚴格苛刻的。在他們看來,士兵的稱呼,包括士兵的服裝、軍銜,只能屬于那些沖鋒陷陣的勇士(這點我極表贊同)。在舊中國,在以日本軍隊為樣板建軍的北洋軍中,在以日、德、美等軍隊模式建軍的國民革命軍中,那些做財務、軍需、衛生等工作的,是不能佩戴軍官的軍銜的,舊軍隊中他們被稱作“軍佐”,佩戴“軍佐”的專門符號,以區別于帶兵打仗的軍官,這有點像今天我軍的文職人員。而服務于軍隊從事一些文字、技術等工作的,則稱作“軍屬”。這個“軍屬”,不是今天我們使用的軍人家屬的意思,而是軍隊附屬人員的意思。“軍屬”與“軍佐”又有不同,“軍佐”是有軍籍的,而“軍屬”是沒有軍籍的。“軍屬”是軍隊中的非現役文職人員。當然,哪些人員屬于“軍佐”,哪些人員屬于“軍屬”,各國分類標準并不一致,但大同小異。在日本軍隊中,那些戰時日軍中的女護士,就是“軍屬”。
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軍就有了征召隨軍護士的做法,但受制于傳統對女性歧視的影響,其數量并不大。所有這些分屬于“軍屬”的軍中女護士,她們都不是士兵,甚至說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人。
我們退一步說,即先甭管她們屬于什么了,只要她們也穿軍裝,也佩戴軍銜,也配備戰刀沖鋒陷陣,神劇中那樣的表現也就沒錯。但遺憾的是,這些日本軍隊中的女護士,她們根本就沒有軍裝。她們也有統一的制服,但這制服不是軍服,而是與軍服有著明顯區別的專門的護士制服。既然不是軍服,因而也就不可能會有像神劇中那樣的將、佐、尉和士兵的軍銜標志,當然也更不會有揮舞著戰刀和肩扛著火箭筒上陣作戰的情況,因為戰刀屬于軍官和士官階級所有,女看護連兵都不是,自然沒資格使用武士們才能使用的戰刀。
除了隨軍的女護士,日軍中還有另外一種“軍屬”,即女子通信隊員,其主要任務是在情報室接聽防空監視所的電話,將敵機來襲的情報輸入情報臺,傳達到隔壁作戰室的“地圖板”上。日本投降時,共有370人左右的女子通信隊員。
按中國的說法,這些女子通信隊員,不就是典型的女通信兵嗎?但在當時的日本,不是。在對士兵身份看得十分重,對在士兵身份的給予十分吝嗇的日本軍隊中,這些“女子通信隊員”同樣也不是女兵。她們也穿統一的制服,但那同樣不是軍服,自然也沒有軍銜。這些女子通信隊員,都只服務于日本國內,并沒有來到侵華戰場。
總之一句話,侵華日軍中沒有女兵。日本軍隊中有不少女性,但那都是不穿軍裝也不佩軍銜更不佩戰刀的“軍屬”,不是女兵。
(摘自“豆瓣閱讀”圖/傅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