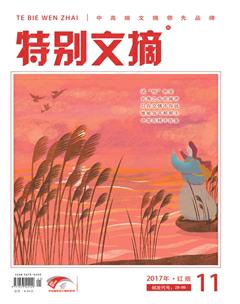甕與缸
2018-01-13 19:30:51馬未都
特別文摘 2017年21期
關鍵詞:歷史
我對史實認知有如下觀點: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我最怕有歷史老師或學者信誓旦旦地告訴我一個“歷史真相”,誤人子弟往往就從“真相”開始。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后人對它可以有一個主觀判斷,這個判斷如果除去看客心態,可以稱其“史觀”。
舉例說明:司馬光砸缸。這個故事自宋以后婦孺皆知,只能說明司馬光天賦異稟,處理危機能力過人。我從小學聽此故事未曾懷疑過它的真偽,也和常人一樣欣賞著故事的傳奇。
可后來讀《宋史·司馬光傳》,才知道宋史由元末蒙古學者蔑里乞·脫脫主編,此時北宋的司馬光已故去近三百年了,做個比喻,間隔時間大約如同我今天寫《雍正傳》。《司馬光傳》開篇有一句話很重要:“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就是說司馬光七歲之時已是一副令人敬畏的姿態,人格端正。我們雖沒見過司馬光,但都見過七歲(虛歲)的孩子,這“凜然如成人”之句顯然溢美。關于“砸缸”文字如下:“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文字洗練清晰,說“甕”未說“缸”,中國文字嚴謹,缸與甕區別明顯。
收口為甕,敞口為缸。戰國至西漢已有陶制大甕;陶瓷燒造有許多技術難題,你千萬別小看器口的一收一敞,敞口深腹大缸完全燒造成功是明末之事,比收口大陶甕要晚上兩千年。所以你聽不見有關缸的成語,而請君入甕,甕中捉鱉,甕牖繩樞等成語都耳熟能詳。
司馬光破甕到司馬光砸缸,從證據學角度有許多商榷之處,細節決定成敗,學者信誓旦旦告訴你的故事可能只是個影子,捕風捉影不是學術態度。至于外行與內行之間,永遠有一條鴻溝天塹,不辯為上策。
(摘自“馬未都新浪博客”)
猜你喜歡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2年2期)2022-03-30 11:38:17
環球時報(2022-03-16)2022-03-16 12:17:18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19年8期)2019-09-09 07:34:21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小天使·四年級語數英綜合(2016年9期)2016-10-09 22:40:45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9期)2015-09-22 07:36:52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7期)2015-07-25 07:42:53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5期)2015-05-26 07: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