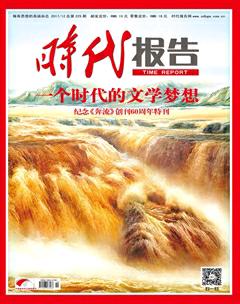我與《奔流》60年
韓樹俊

一
江蘇省蘇州市第十中學(xué),因了這所名校,因了這所學(xué)校藏書頗豐的“長達(dá)圖書館”,我有幸在少年時(shí)代就讀到過《奔流》雜志。
楊絳、費(fèi)孝通、何澤慧、彭子剛曾經(jīng)是這所學(xué)校的學(xué)生,章太炎、蔡元培、葉圣陶曾經(jīng)在這所學(xué)校講過學(xué),蘇雪林曾經(jīng)是這所學(xué)校的國文老師。這樣的學(xué)校才會(huì)在《奔流》文學(xué)雜志剛創(chuàng)刊時(shí)就訂閱上架。
我是學(xué)校圖書館的學(xué)生管理員,課余時(shí)間幫助圖書館修補(bǔ)舊書、整理圖書上架、閱覽室值班。圖書館的老師見我服務(wù)認(rèn)真細(xì)心,喜歡看書,破例給了我一些“特權(quán)”,以資獎(jiǎng)勵(lì),那就是周六放學(xué),我可以借一到兩本新到的雜志帶回家讀,周一一早歸還。于是,周六放學(xué),我的書包里會(huì)有一本《奔流》。
記得美術(shù)老師帶領(lǐng)我們美術(shù)興趣小組的同學(xué)上街去畫壁畫,我要畫大躍進(jìn)民歌《社員堆稻上了天》:“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湊上太陽吸袋煙!”一接到任務(wù),便去圖書館找參考資料,一眼看到一本《奔流》雜志,封底正好是一首大躍進(jìn)民歌的詩配畫。“鼓足干勁驚天地,桂英自甘拜下風(fēng)”,大意是打破天門陣的穆桂英怎能比得上當(dāng)今女礦工。畫面上是兩個(gè)頭戴礦工帽、身穿工作服手握鉆頭機(jī)正在鉆煤的女礦工。于是,我畫了高高的稻堆、稻堆上抽著桿煙的老農(nóng),背景是白云和紅太陽。
就這樣,從1957年起,13歲的我,似懂非懂地讀著里邊的文字,初二開始,《奔流》逐漸替代了我曾經(jīng)愛不釋手的《少年文藝》。我在這所學(xué)校一直讀到高中畢業(yè),我不能說是《奔流》讓我選擇了中文系,但我要說,《奔流》這類文學(xué)雜志是我的文學(xué)啟蒙。
二
大學(xué)讀的是中文系。學(xué)校在徐州,緊鄰河南,《奔流》作品的豫地背景、民風(fēng)民俗與徐州很相似,去閱覽室,《奔流》是我的必讀。當(dāng)代文學(xué)作業(yè)我選擇了讀柳青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評(píng)析主人公梁生寶這個(gè)人物。我做了兩種卡片,一是全書中有關(guān)梁生寶語言和行動(dòng)的相關(guān)文字,一是報(bào)刊雜志發(fā)表的評(píng)論文章中關(guān)于《創(chuàng)業(yè)史》尤其是梁生寶這個(gè)人物形象的分析。在后者的大量卡片中,有一些摘自《奔流》雜志。在我的印象中,《奔流》發(fā)表農(nóng)村題材的作品較多,也有一些相關(guān)評(píng)析,于我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梁生寶有很大的啟發(fā)和借鑒作用。
在上世紀(jì)60年代初期,我與《奔流》同步,留下了追求文學(xué)大浪最初的足跡:一個(gè)是把文學(xué)作為專業(yè)的中文系大學(xué)生,學(xué)寫一些詩文,60年代中期的《徐州日?qǐng)?bào)》《新華日?qǐng)?bào)》留下了我最初的文字;一個(gè)是一本嶄露頭角的文學(xué)雜志,為承繼魯迅文學(xué)精神、培養(yǎng)新人作出了最初的努力。
大學(xué)畢業(yè)分配回到母校,又踏進(jìn)了“長達(dá)圖書館”。在復(fù)刊后的《奔流》第二期上,讀到了上大學(xué)時(shí)教我們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吳奔星老師撰寫的《讀<天安門詩抄>》,尤感親切。這段時(shí)間,我在《奔流》讀到了牛漢、郭小川、蘇金傘、王懷讓、葉延濱的詩,劉再復(fù)、管用和、劉章、王幅明的散文詩,周同賓、卞卡、王劍冰的散文,賈平凹、葉文玲、劉心武、梅子涵、陳忠實(shí)、王小鷹、王安憶、范小青、黃蓓佳的小說,理由、李佩甫的報(bào)告文學(xué),吳功正、楊匡漢、魯樞元、陳遼、王先霈的文學(xué)評(píng)論。回望這樣耳熟能詳?shù)拿郑屛矣忠娺@些大家當(dāng)年青春的腳步,也彰顯了《奔流》培養(yǎng)文學(xué)新人不可磨滅的光輝業(yè)績。而于讀者而言,則從《奔流》汲取了文學(xué)的營養(yǎng),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熏陶。
是的,作為一個(gè)青年語文老師,得益于《奔流》的閱讀,促進(jìn)了教學(xué)的改革,將雜志上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作為補(bǔ)充教材,引進(jìn)時(shí)代的活水,搞活語文教學(xué)。不用說在《周總理,你在哪里》詩歌的備課中直接得益于蘇金傘的詩《周總理的腳步》(刊1978年第1期《奔流》),單說這段時(shí)間我教學(xué)之余編輯出版了《少年晨讀365》(與楊九俊合作)、《晨讀365》(與秦兆基合作)、《中國校園詩100首》(與楊新合作)等書,均有直接或間接來自于閱讀《奔流》的得益。我編選的《晨讀》系列出版物中,曾經(jīng)是《奔流》的作者,可以列出長長的名錄(排列不分先后):邵燕祥、吳奔星、蘇金傘、劉再復(fù)、李耕、劉章、管用和、葉慶瑞、劉增山、桂興華、閆妮、丁一、趙麗宏……我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晨讀365》獲得了中南六省區(qū)優(yōu)秀教育讀物一等獎(jiǎng)。
正當(dāng)我?guī)W(xué)校振華文學(xué)社,組織學(xué)生編輯《牙牙語》時(shí),讀到《奔流》1981年8月大學(xué)生作品專號(hào),這一期專號(hào)上有梁左、王小妮、趙翼如學(xué)生時(shí)期的作品;而這一時(shí)期我的學(xué)生楊新的習(xí)作,也從《牙牙語》走出,走上華東六省一市中學(xué)生作文比賽一等獎(jiǎng)的領(lǐng)獎(jiǎng)臺(tái),走上《新華文摘》,一個(gè)13歲的女孩清秀的文章被全國幾十家文學(xué)報(bào)刊同時(shí)轉(zhuǎn)載,被白樺等老一輩作家看好并向小作者寫信鼓勵(lì),女孩的文章上了《新華文摘》,振華文學(xué)社一批文學(xué)青年正在茁壯成長。作為文學(xué)社指導(dǎo)老師的我,正學(xué)著《奔流》栽培新人為發(fā)掘文學(xué)新苗努力耕耘。
三
1990年初,我為出版《報(bào)刊議論文選評(píng)》一書赴鄭州與文心出版社洽談。我?guī)チ藭澹瑤チ酥逃矣阡衾蠋燁}詞:“引進(jìn)時(shí)代活水”。當(dāng)文心出版社的領(lǐng)導(dǎo)和編輯陪同我站在滔滔東流的黃河邊時(shí),一絲愁緒掠過我的心頭,我在尋找《奔流》,我在呼喚《奔流》;而此刻,中原大地的《奔流》雜志已經(jīng)因多種原因被迫停刊。我的內(nèi)心向著奔騰的黃河水呼喊,什么時(shí)候,《奔流》再次急流勇進(jìn),成為時(shí)代的活水,在文學(xué)的長河里奔流不息!
四
退休后,擺脫了繁忙的教務(wù),終于有時(shí)間可以隨心所欲地寫一些東西,也發(fā)表了一些詩文。我兼任蘇州高新區(qū)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后,除了自己努力創(chuàng)作外,總是設(shè)法尋找一些機(jī)會(huì),與高新區(qū)的作家朋友共同發(fā)展。在協(xié)助《西部散文選刊》編輯“蘇州高新區(qū)作家散文專輯”后,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發(fā)現(xiàn)復(fù)刊后的《奔流》雜志有“地域方陣”這個(gè)欄目,在與編輯電話聯(lián)系中得知雜志還辦改稿班。
放下電話,我便給《奔流》投稿。想到今年7月是“七七事變”80周年,便發(fā)了《西南聯(lián)大舊址》組詩,7月號(hào)全文刊登。接著,8月號(hào)又刊發(fā)了我寫老舍青島故居的《黃縣路12號(hào)》和楊絳蘇州故居的《廟堂巷16號(hào)》兩首詩。我也終于躋身在《奔流》作者隊(duì)伍之中了。尤為高興的是,我的一位15歲的女學(xué)生,她的組詩《從此刻開始》也刊登上了《奔流》雜志,“從此刻開始”,《奔流》雜志讓15歲的小詩人優(yōu)美的文字展開了飛翔的翅膀!
這個(gè)夏天,我有幸?guī)Я宋业膶W(xué)生一起參加首屆奔流文學(xué)獎(jiǎng)?lì)C獎(jiǎng)典禮暨第四屆奔流作家研修班。難忘青龍峽研修班上單占生、王劍冰等名家的講學(xué)和與學(xué)員的互動(dòng),難忘《奔流》總編張富領(lǐng)、常務(wù)副總編鄭旺盛等領(lǐng)導(dǎo)和一些洋溢著青春氣息的編輯們自始至終的陪伴,難忘學(xué)員們真誠的交流和勉勵(lì),這是一個(gè)有溫度的文學(xué)大家庭。研修班回來得知,有4位加入了中國作協(xié),有多位學(xué)員出版了長篇小說、中篇小說集、散文集。這是一個(gè)有檔次的研修班。
我與《奔流》雜志的總編、編輯、各個(gè)時(shí)期的作者多有交集,每每回顧,暖人心懷。我珍藏的知名作家贈(zèng)我的墨寶與簽名中,有不少曾經(jīng)是《奔流》的作者(排列不分先后):賈平凹、郭風(fēng)、邵燕祥、趙麗宏、王幅明、王劍冰、單占生、范小青……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他們?cè)凇侗剂鳌妨粝铝饲啻旱淖阌。侗剂鳌肥谴蠹页砷L的沃土。
今年我相繼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散文詩集《姑蘇十二娘》和《風(fēng)潤江南》。著名詩人、詩評(píng)家小海在《風(fēng)潤江南》一書的序中,說我“至今還保持著資深文青的理想主義與人文情懷本色”。說我的教學(xué)“從解放孩子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性入手”“讓孩子們解套了放開思路去撒野”“關(guān)鍵是,他本人還身體力行加入寫散文詩的隊(duì)伍,和學(xué)生們一起撒野。”這不,這個(gè)冬季,我又要帶上一位文學(xué)少年,同赴駐馬店市老樂山,去歡樂,去“撒野”,去見證《奔流》創(chuàng)刊60周年的盛大慶典,去參加第五屆《奔流》作家研修班。
.一個(gè)刊物被紀(jì)念,這個(gè)刊物一定具有存在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意義,一定會(huì)有與讀者的情緣。從一個(gè)13歲的讀者,到一個(gè)73歲的作者,到一個(gè)遵循《奔流》“繁榮文學(xué),培養(yǎng)新人”宗旨不斷引薦文學(xué)少年的忠實(shí)讀者,一個(gè)甲子,有《奔流》陪伴,這是文學(xué)的追求,文學(xué)的攜手,文學(xué)的情緣,也是一個(gè)普通讀者與《奔流》結(jié)緣的一段佳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