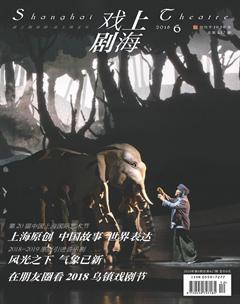有關愛的理念與意義
劉芊玥
三百年前,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鬼故事,講的是狐女的枕席自薦與古代書生的幸福生活;三百年后,林奕華的舞臺劇《聊齋》也講“鬼故事”。
這個鬼故事不僅是指劇中蒲先生的那些鬼話,還有他死后的回魂和他設定的“胡小姐”,以及酒店里那些光怪陸離的妖精般的服務員,還有曖昧模糊的時空。《聊齋》是一部通過戲里角色和觀眾的“聊天”,來探討話題、引發思考的作品。
鬼話的連篇,詭異的時空
《聊齋》的英文名是Why We Chat?說起聊天,必然夾雜著大量對話。古代書生的“齋”是書房,今天現代人的“齋”是手機,它幾乎成為人與人情感連接的最重要的紐帶。能把信息量巨大的聊天融化在臺詞里,并使之節奏得當、層層推進,這是考驗編劇和導演功力的。
《聊齋》再次展示了導演林奕華高超的時空調度手法。在演出空間上,舞臺上的旅館代表的是陰陽的相隔、燈光也是陰陽的相隔。一條無形的漫長的樓梯、一開一關的燈光,悄然劃分出不同的空間。明明晃晃、昏昏暗暗的燈光和舞臺設計,分明是同一個時空,細看之下,哪還有剛才時空的影子?又哪里還有剛才尚在眼前的人?
在故事結構上,不僅有平行時空中人物故事線索多種可能性的并存或展開,亦有同一時空中人物的“復調”出場,來組成人物關系的多聲部。故事一開場,蒲先生是一個已經死掉的人,胡小姐則是上半場未曾在場的“在場”,她或者是蒲先生在手機里設定的理想型聊天對象,或者是平行時空中可能性里的胡小姐,與蒲先生這短暫的一生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觀眾在這樣一種跳躍、回旋、假定的空間里慢慢拼湊完整蒲先生前半生的故事,他所歷經的感情、種種事件、他的心態。下半場開始則以胡小姐的敘事視角為主,她結婚、夭折了孩子、離婚、與情人調情、暗暗營救蒲先生卻又不得不與之不見,以至再也不見。張艾嘉和王耀慶的表演爐火純青,兩人的自戀、互相閃躲、互相憐惜都拿捏得恰到好處。
探討婚姻,也探討出軌
這是兩個玩世不恭墜入愛河火速結婚又火速離婚的男女——蒲先生與胡小姐,在另組家庭后發現彼此是今生最愛的人卻無法在一起,在死后彼此深情思念的故事。
蒲先生是一個浪蕩、喜歡玩的大男生,他人生字典里還沒有“承擔”這兩個字。他與女記者鬼混完急忙擺脫,又與胡小姐墜入愛河,緊接著還出軌他人。與胡小姐的結婚除了孩子這個變數推動以外,還有胡小姐的那句“姐罩你”。“姐罩你”這句話,意味著無時無刻的安全感和可以允許的犯錯。未出世便夭折的孩子是推進胡小姐和蒲先生結婚的變數,也是結束婚姻的變數。胡小姐是清醒的,蒲先生是慌亂的,這種亂和慌亂后的竭力爭取不僅是因為愛情,還因為一種類乎母性的安全感的消失,以后他沒有人可以依靠了,他要獨自面對一切了,他不想長大、不要迷茫。
除了男人的不想長大,故事里還有女人的不想長大,比如女記者。她愛得熱烈極致,愛到沒有自己,她理所當然地認為愛就是得到。她和胡小姐形成鮮明的對比,她執著于自己的小情感,到最后都沒有學會放下自己去看一看生活的真實是怎樣、世界的全貌是怎樣。
胡小姐向蒲先生求婚的時候,說了一句十分“動人”的話“結婚有很多好處的。結了婚以后,你可以有婚外情”。林奕華的《聊齋》在探討愛情的同時,也在戲謔中探討了出軌。
“出軌”在這里與道德和倫理不再對立。在18世紀以前,婚姻就像生意結盟,愛情實與婚姻矛盾。資產階級興起以后,愛情與婚姻才逐漸化為同義詞,不再與體制沖撞而成為體制本身。既然婚姻體制和社會秩序互生互構,愛情規范化為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那么任何溢出婚姻體制的欲望和擾亂愛情規范的反抗,都可以被視為反社會秩序的藝術行動和政治革命。有學者將外遇比作藝術實驗,因為它顛覆了規范,模糊了邊界,使單偶關系化為三角結構,是對伴侶制度的重組,也是對親密關系的即興創作。不過,外遇與愛情體制并非二元對立,很多時候一段摧毀愛情神話的外遇,同時造就和鞏固了另一段愛情神話。正如《聊齋》里蒲先生和胡小姐的故事。
蒲先生這一生總在問胡小姐:“你為什么總說我不懂?”多年后的胡小姐告訴他:“我懂了。你不懂,可是沒有關系。”對于胡小姐來說,愛不僅是可以拿起、承擔和放下的勇敢,也是即使我不見你、不能和你在一起,你依然是我最愛、最重要的人。你不懂,可是沒有關系。
我們都渴望一生永恒不變的愛,但是林奕華偏偏要講的是愛的復雜性與人的多變性。這個“多變”不僅是世事無常,也包括人的成長。眾生說,真愛就像鬼故事,聽過的人多、遇過的人少;在《聊齋》里,說的是迷惘的人、執著的鬼與善變的狐,鬼代表過去,狐代表未來,迷惘的人被卡在了中間。時空的沉浮,人、鬼、狐的殊途,還在講一個有關“缺失”和“溝通”的問題。人的迷惘源于缺失,是不敢去愛、不敢去問、不敢承認、不敢離開,以及,不敢一個人。蒲先生和胡小姐可以既放肆又優雅地與別人調情和曖昧,但又讓每一個觀眾都覺得兩人并不為了攻城拔寨,他們的浮華之中自有一種落寞,深入骨髓。胡小姐對蒲先生說,人總是懂得太晚了。于是,很多遺憾化為命中注定和一聲嘆息。正如三百年前的某個書生,在讀唐詩時讀到了一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青峰”。
林奕華喜歡在他的戲劇中拋出問題來引發觀眾的思考,因為不喜歡給予答案,不喜歡只有一種解讀,他希望每位觀眾都能從中找到映照自己的難題。《心之偵探》是,《機場無真愛》是,《聊齋》亦如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聊齋》是成功的,它一如既往地延續了林奕華“成長”的主題以及當代人的困境。你理解了多少,你便得到了多少。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