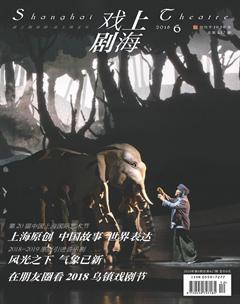離開環莎的艾瑪·萊斯
夢珂
在2016年1月的時候,英國導演艾瑪·萊斯被任命為莎士比亞環球劇場的第三任藝術總監,也是該劇場首位女藝術總監。然而當她4月正式接任后僅僅半年不到,在2016年10月的時候,劇場的董事會就宣布她將在2018年4月卸任。相比第一任和第二任都同時擔當了10年,萊斯或許是環球劇場史上最“短命”的藝術總監。
這其間所發生的事,雙方各執一詞,似乎誰也說服不了誰。在環莎董事會一方看來,這是個不得已的痛苦決定。原因在于,2016年環莎的夏日演出季中,萊斯安裝了霓虹燈和擴音器,并且在2016年夏日演出季的每一部劇作、每一場演出,都必須使用擴音器。這跟環球劇場的訴求背道而馳,因為環球劇場建立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原汁原味”。所謂的原汁原味,指的并不是僅僅是還原當時的演出情景,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頗為簡陋的舞臺——包括沒有擴音器、沒有效果燈、沒有聚光燈——去再度發掘文本。比起“當下的我們怎么看莎士比亞的文本”,環球劇場更想要問的問題是“為什么莎士比亞的文本是這樣的,他為什么這么寫”。這20年來環球幾乎每一部劇的制作,不僅只是公開售票的演出,也同時承擔著幫助研究者去回答后面那個問題的作用。
而艾瑪·萊斯顯然不是那么在意這一點。在她剛上任成為環莎第三任藝術總監的時候,她就直言“對莎士比亞毫無興趣,他的劇絕大多數的時候都顯得太長了,我也讀不太懂”,但這不是她和環莎矛盾的根源,甚至可能恰好是當初她被選中的原因。選中艾瑪·萊斯,意味著環莎也想要尋求改變和突破。她在環莎的作品有人激賞為大膽顛覆,也有人貶為迪斯科舞廳。筆者則在觀看了她的首秀《仲夏夜之夢》之后,就察覺到了根本原因,在于她的訴求和環莎的首要訴求之間是不和諧的。果不其然這導火索最終燃成熊熊大火,變成了萊斯和環球劇場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環球劇場在關于萊斯卸任的公告里說,他們希望能恢復到“自然光”(Shared light)的表演方式。而在萊斯看來,這只是表面的說辭,環莎董事會的行為本質上是粗暴的干涉,她的意愿和她的藝術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且作為藝術總監的她被排除在了“做決定的房間”之外。在萊斯看來,這根本不是霓虹燈和擴音器的事,而是她的藝術自由受到了侵犯。“在環莎,是由他們來告訴我什么是莎士比亞,并非我自己。如果我繼續留在這里,意味著要犧牲我的藝術自由作為代價。我尊重了環莎,但他們顯然并沒有尊重我。他們沒有理解我的感受,也沒有理解我和我的同僚們、我的觀眾們所創造出來的一切。”在《衛報》的采訪中,萊斯如此說道。
在外界的看客們看來,這場矛盾是“傳統”和“實驗”之間的斗爭,是白人男性手持的“莎士比亞”特權和民主的“大家的莎士比亞”之間的斗爭。然而筆者在環莎的圖書館泡了半年,觀看了他們數十部DVD錄像和舞臺提示本,筆者必須說,環球劇場這個項目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它是每一個觀眾和演員關于什么才是“正統性”(authenticity)的思考與體驗。在這場思考與體驗中,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然光的作用與意義。自然光意味著舞臺與觀眾席之間的平等,更意味著對于導演中心制的顛覆。對演員而言,在臺上可以看清每一張觀眾的臉絕非易事,因為演員會比平時更害怕、更加脆弱。“我要怎么吸引這些吵吵鬧鬧的觀眾?這些購買五鎊站票的游客?這些根本是不怎么聽得懂莎士比亞優美詩句的人?”演員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讓他們安靜下來,所以他們開始試著直接對觀眾說話,并期待他們的回應。比如馬克·里朗斯教伊桑·霍克在表演“生存還是死亡”這段最著名的臺詞的時候,要盯著觀眾看。一旦盯著的時間夠長,觀眾必然開始發笑。他們只要一發笑,霍克就能擺脫“經典”的包袱,自在表演了。伊桑·霍克聽了里朗斯的話,他的表演也獲得了保羅·斯科菲爾德的首肯。這種觀眾的笑聲,在光影分明的鏡框式舞臺下,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同時,正因為沒有刻意設計的舞臺燈光,劇場的焦點也會顯得分散,舞臺和演員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成分混雜的觀眾,或晴或雨或大風的天氣,偶爾降落舞臺的鴿子,泰晤士河邊長鳴的海鷗,頭頂呼嘯的直升機,都成為了“表演”的一部分。這些充滿不確定性的表演,也正是自然光所帶來的魅力。
萊斯的前任藝術總監多米尼克·德洛姆戈爾在關于艾瑪·萊斯卸任的公開信中,也表達了他對環莎的理解和認同。他認為,環莎的根基與核心,一方面在于五鎊的站票,另一方面,恰恰在于它的自然光。“對我而言,自然光意味著一個民主的戲劇空間,在其間展開的故事成為了演員和觀眾一同盡情去想象的旅程。在我看來,沒有自然光,并不是什么大膽的變革,相反,沒有自然光的環球劇場才是墨守成規的。每個劇場都有擴音器和燈光設計,環球劇場沒有。它的獨一無二性對我而言很重要,我希望你,萊斯之后的繼任者,也能存留這一點。”在給萊斯的繼任者的一封公開信中,德洛姆戈爾這么寫道。
但與此同時,德洛姆戈爾也表示了對萊斯的充分支持,以及對環球劇場董事會的不滿。無論他再怎么視自然光為環球劇場最珍貴的特性,那也只是他的藝術觀點,并非萊斯的。“一個戲劇場所的藝術政策只有藝術總監可以制定,董事會不行,任何小團體也不行。”從劇場運營公認的道德準則來看,確實如此。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莎士比亞自己,可以聲稱擁有“莎士比亞”。誠然環球劇場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還原“原汁原味”,但原汁原味并不自動就擁有了對“莎士比亞”的最終解釋權。所以盡管筆者了解環球劇場建立的歷史,也非常理解其除了戲劇表演以外的、研究與教育的目的,筆者還是無法贊同、無法尊敬董事會的行為。但或許,這次“分手”,對萊斯而言,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它逼迫萊斯去思考自己和莎士比亞的關系。而今年秋天,通過在老維克劇院上演的《聰明的孩子》(Wise Children),萊斯交出了她的答案。
《聰明的孩子》原著講述的是一對雙胞胎姐妹諾拉和朵拉作為戲劇演員的一生。故事始于兩姐妹75歲的生日,那天也正好是莎士比亞的生日——4月23日。朵拉開始回憶起她和諾拉的過去:她們的生父梅爾基奧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了著名的莎劇演員,卻拒絕承認自己就是姐倆的父親;于是她們的叔父佩爾格林則成了她們名義上的父親,她們也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了父愛。后來,她倆被交予她們的祖母撫養,在那里,朵拉假扮自己是諾拉,和諾拉的情人發生了關系,也第一次體會到流產的痛苦。后來她們的生父找上了她們,與她們共同合作《仲夏夜之夢》,在戲劇的舞臺上,通過莎士比亞,她們第一次能夠與生父溝通,第一次得到了他的認同。不幸的是,在二戰中,她們摯愛的祖母因為貪酒,死于一場空襲。
本劇的下半部劇情線就更為雜亂,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原作中涉及到家庭倫理和不倫戀愛的部分就不少,頗為“狗血”。比如,二人生父的第二任妻子亞特蘭塔,被自己的兩個女兒推下樓梯導致半身不遂,雙胞胎姐妹發現了她,后來,她們就生活在了一起。更為“狗血”的,則發生在最后一幕:諾拉與朵拉去參加了梅爾基奧的100歲生日宴。在生日宴上,亞特蘭塔坦誠她的雙胞胎女兒其實并非梅爾基奧的骨肉,而是佩爾格林的孩子。而朵拉則控訴,早在她還全身心信任著佩爾格林的時候,佩爾格林就利用自己的特權性侵了她。朵拉不得不把這視為“愛”,因為不這么做,她將無法繼續正常生活。最后,伴隨著諾拉和朵拉抱著和她們沒有血緣關系的路人的孩子,傳達的訊息是:父親只是一個概念,而母親是事實。即使互相沒有血緣關系,女性社群的融合,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家庭”。
艾瑪·萊斯將這個故事作為她離開環球劇場后的首秀,其間深意非比尋常。從故事內容上看,她似是借用《聰明的孩子》,質疑了所謂莎士比亞的正統性。諾拉和朵拉的生母在扮演哈姆雷特的時候意外懷上她倆,她們的生父在扮演李爾的時候和扮演考狄莉婭的女演員有染……盡管這些在演藝界本身屢見不鮮,但大著肚子的哈姆雷特和亂倫的李爾,在模糊了戲里與戲外的界限的同時,也對“莎士比亞”作為英國文化中近乎國寶一般神圣的存在,進行了解構和嘲諷。
然而,與此同時,本劇的戲劇結構本身又充滿了莎士比亞式的互文:尤其是一對又一對的雙胞胎,朵拉假扮諾拉去與諾拉的情人發生關系的情節等這些戲劇手法,無不充滿了莎劇的烙印。甚至在演員的選角上,萊斯非常推崇的性別模糊(gender blind)選角方式本身也是莎士比亞式的性別視角的一種延續,莎劇所尤其擅長的,(由男性演員扮演的)女性角色扮裝為男性再偽裝為女性,本就已經模糊了性別的界限。
可以說,《聰明的孩子》十分莎士比亞又十分不莎士比亞。而艾瑪·萊斯的導演風格作為一抹鮮明而強烈的色彩加入進來,讓莎士比亞也只得為她讓路。依然是亮麗鮮明的色彩,依然所有演員個個唱得好跳得更好,依然是她鮮明的音樂劇風格,在對原作“歌唱、舞蹈與表演給演員自身帶來的愉悅”表達充分贊同與肯定的同時,更為本作賦予了尖銳強烈的女性賦權的視角。
不需要再被環球劇場對自然光與正統性的執念所束縛,這個酷酷的特立獨行的導演,終于找到了她的莎士比亞。這無關乎莎士比亞還在神壇與否,而是對艾瑪·萊斯來說,莎士比亞不是她的研究對象,甚至也并不是她怎么看莎士比亞。相反,重要的是,她如何利用莎士比亞去進行自我表達。莎劇只是手段,她自身才是目的。“聰明的孩子”不僅僅只是一部劇作,它同時也是她自己的戲劇公司的名字。自由溫暖,活力充沛,絕不言棄,絕不妥協——是艾瑪·萊斯對環球劇場董事會的回應,也是她的,嶄新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