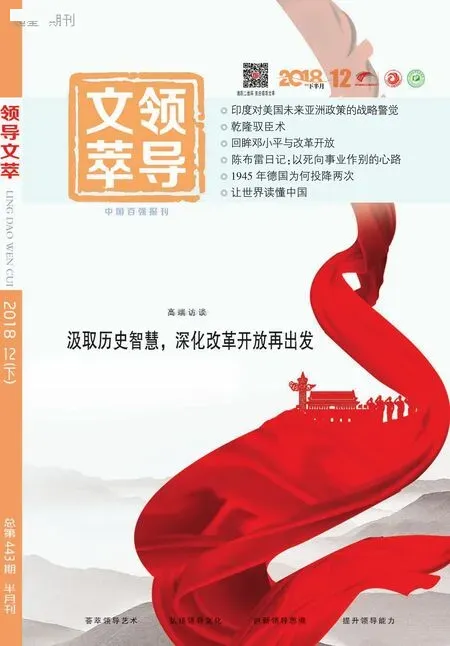李敖和金庸: 才子的兩種類型
六神磊磊
一
中國頂尖的才子,一般就是兩種類型:李敖型和金庸型。基本沒有例外。只不過有的是八成李敖、兩成金庸;或者反過來,八成金庸,兩成李敖而已。
一個叫“敖”,狂蕩也,游樂也,喧嘩也,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一個叫“庸”,平凡也,駑鈍也,謙退也,樂哉開后覺,乞我一中庸。
一個極致地張揚,一個習慣性地謙抑。
都是辦刊出文集,一個叫“千秋評論”“萬歲評論”,中指比千秋;一個叫三劍樓隨筆、明窗小札,自說都是些“隨筆”“小札”、小玩意,微小的貢獻。
寫詩,一個風行水上,說“只愛一點點”“我的愛情淺”;一個字斟句酌,吭哧吭哧,說“聆群國士宣精辟,策我庸駑竭愚誠”。
一個說自己五百年白話第一人,一個口頭上總說“無論如何不敢當”“我不是寫得最好的”。
二
很多人眼里,李敖似《世說新語》上人,金庸似《經濟名臣傳》上人。
李敖沒有做完人的壓力和包袱,而金庸有。李敖可以痛快罵人,隨便開車,大膽超速,他的人設是張狂才子。金庸極少罵人,罕有開炮,他的人設是彬彬書生。
他公開講話,措辭委婉,面面俱到,“王八蛋”之類的詞絕不輕易出口,受訪不懟記者,評點別人時,經常是客套地“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錯的”。揶揄幾句臺灣武俠小說同行,說張藝謀《十面埋伏》評價不好,說別人拍電視劇亂改他的書,就算是厲害的了。
好玩的是,沒有完人包袱、到處罵人的,容易被叫作“性情”。而面面俱到、努力做完人,又或對他人感受考慮太多的,則容易被說成是乏味、圓滑、世故。
所以李敖盡管無比貪財,卻還可以指責金庸貪財——不做完人,就不用處處設防;要做完人,則任何一點都可以被攻擊。
做完人不值。最好的是把自己放到樓底,向樓上隨便罵。
三
李敖無秘密,風月、親子關系、吃喝拉撒,都被自己或他人各種宣之于眾,本人還勤奮寫自傳。無秘密的人,容易讓人覺得親切。
金庸如城堡,心事深藏。
他不寫自傳,不談隱秘私事,今天大眾能拿來八卦的,不過一個朦朦朧朧、不知是耶非耶的夏夢梗而已。
有了天大的傷痛,金庸也自己找佛經化解,不愛對人傾訴。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很保守的,痛苦快樂,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哪怕痛裂心扉,對外也不過一句: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在女人方面,不同程度地,兩個人都虧負前任。
這種才子,在女人問題上是交不出圓滿的人生答卷的,千古只有那么幾個杜甫、王績而已,還得特窮。
對前任,李敖一直不依不饒嗆嗆嗆、損損損,金庸則總說愧疚,愧疚。但事實是,前者似乎并未因此承受更多詈罵。
世人愛看才子狂浪,卻不愛看大款休妻。金庸的故事,被人自動代入了第二種情境而已。
四
李敖“性情”,其實相當精明。什么人能罵到什么程度,拿捏得頗準。
金庸“圓熟”,其實骨子里桀驁。“我這生最大的脾氣,就是人家指揮我什么事情都不聽的。”所以,小時候他總被開除,讀中學也開除,讀大學也開除。后來到了左派的報紙也待不下去。
李敖讓你感覺不停在推翻自己,而金庸自從成長為一個自稱的“保守主義者”之后,在政見上沒有反悔過,大致就是一句話:“我個人主張循序漸進,不喜歡一下子天翻地覆”。可結果是,兩個人都得罪人。
李敖的作品,禁作等身,號稱一百部里禁了九十六,甚至沒寫完就禁。
金庸的書一樣被禁,當時一度內地禁,臺灣也禁,“射雕英雄傳”還得改成“大漠英雄傳”。因為反對左,金庸被狂熱分子人身威脅,要暗殺,被寄炸彈。
可見頂級的才子,只要識見的底線仍在,不管你怎么為人處事,都是得罪人的。
晚年,當他們一生的敵人和對手漸漸消失、成為歷史之后,兩個人其實不同程度地都有點無措。
李敖更明顯一點,金庸其實也有。
激發他們靈感的癲狂時代漸遠了,奔涌的才思蟄伏了,文筆的鋒芒消失了。
李敖是不見芒,只見瘋;金庸是不見鋒,只見忙。
人間最完滿事,大概就是李敖不瘋,金庸不忙。
(摘自《閱讀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