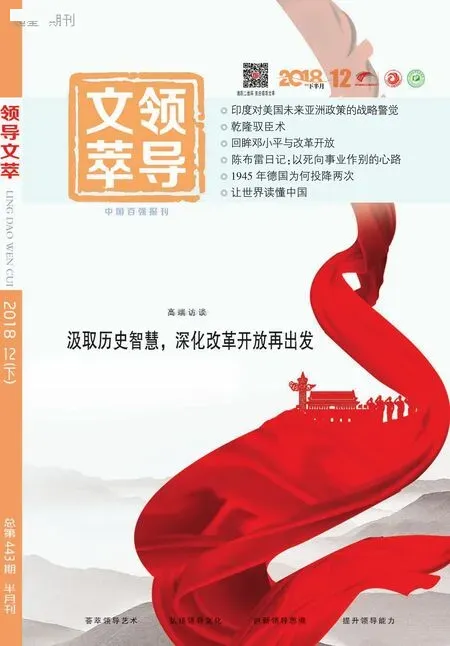歷史上有名的托孤大臣, 結局都怎樣?
佚名
周 公
托孤中比較早的,且一直為人稱道的,想必就是周公輔成王了。周公旦,姓姬,名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武王平定殷商之后就英年早逝了,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武王安排周公托孤,一部分是因為周公治國才能出色。另一方面是因為周公是武王的同母弟,武王選擇周公托孤和至親不無關系。
周公成功完成了武王的托孤任務,輔佐了年幼的成王,將剛剛建立的周朝的形勢穩定下來,他創立的一系列措施不僅使周朝傳世800年(水分有點大),也對后世影響巨大。
托孤重臣,手握大權,代行皇權,受到非議難以避免。周公也如此,周公旦攝政6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還政于成王。歷史上最完美的托孤,莫過于此。
霍 光
當漢武帝多年培養的太子因為巫蠱案遇害后,他決定傳位于鉤弋夫人之子劉弗陵。其實早在漢武帝將鉤弋夫人的居所命名為舜母宮時,他估計就有這個念頭。劉弗陵年僅8歲登基,為了防止出現呂后專政的情況,漢武帝還賜死了鉤弋夫人。劉徹把小皇帝和天下托付給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以及桑弘羊這幾個人。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從郎官擢升上去的;金日磾是匈奴降人,從養馬的位置混上去;上官桀是從羽林郎與未央廄令混上去的;桑弘羊是武帝鹽鐵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武帝托孤之后,經過一系列政治動蕩,最后霍光大權獨攬。霍光廢一帝,立一帝,手中權勢不亞于后代的任何一位權臣。但江山畢竟沒有易主,還是劉家天下。除了最后霍光死后霍光家族被族滅,這次托孤大致算是完美。
諸葛亮
歷來爭議最多,談論最多的當屬劉備的白帝城托孤。“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這幾句話是否出自劉備真心,被后人爭論了多年。有一點和《三國演義》上不同的是, 劉禪當時并不在場。
拋開這句話是否出自劉備真心,從劉備托孤的一系列措施來看,他并不是僅僅將政權托付給忠心的諸葛亮,而是讓李嚴和諸葛亮共同輔政,這些措施保證了此后的蜀漢并未易主。托孤從來不是將幼主托付給重臣就完事,而是一系列保證政權交替的措施組合,劉備的這次托孤,從后來諸葛亮兢兢業業服務蜀漢,出師未捷病死漢中來看,是最感人、最深情,最能體現君臣情誼的一次托孤。
張 昭
對比東漢末年和三國的其他幾次托孤,另一次成功的托孤是孫策將幼弟托付給張昭。孫策剛剛去世,孫權非常悲傷。張昭勸孫權說:“夫為人后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他親自扶孫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后眾人才服從了孫權。此后張昭一直效忠孫權,直到81歲高齡去世。 托孤重臣從來都是安享天年者少,死于政局者多,孫策托孤張昭,的確讓人嘆服。
長孫無忌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 太宗病危,急召長孫無忌到含風殿,太宗臥在床上,伸手摸著長孫無忌的腮,長孫無忌失聲痛哭,不能自已。二十六日,太宗又召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入自己的臥室內,太宗說:“太子仁孝,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今后望能善加輔佐教導。”又對太子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兩位忠臣在,你就不用為天下的事過分擔憂。”又對褚遂良說:“長孫無忌對我可謂竭盡忠智,朕之所以能夠擁有大唐江山,長孫無忌出力最多,我死了以后,不要被小人讒言而進行挑撥離間。危難之時,你一定要挺身保護長孫無忌。”說完,即命褚遂良草擬遺詔書,過了不久,太宗駕崩。
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即位,史稱高宗皇帝。初十,高宗拜舅父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掌管尚書及門下二省事務。長孫無忌知其權位太重,故請求辭去尚書省及門下省的掌管權,高宗同意了他的請求。但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顯慶四年(659年),在武則天的授意下,許敬宗等人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了一樁朋黨案,進行政治陷害,誣奏長孫無忌伺機謀反。唐高宗竟然不與長孫無忌對質(或者他需要不進行對質),就下詔削去了長孫無忌的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長孫無忌的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或殺。三個月后,高宗又令許敬宗等人復合此案,許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長孫無忌自殺。就這樣,這個風光一時的托孤大臣以這樣一種極不體面的方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張居正
隆慶元年(1566),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死后,其子裕王朱載垕即位,是為隆慶皇帝明穆宗。張居正以裕王舊臣和親信的身份,擢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此時的他,并沒有忘記自己早在13歲時所寫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現在他終于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隆慶六年(1572),明穆宗病逝,其長子朱翊鈞登基,是為萬歷皇帝明神宗。明穆宗在病榻前鄭重托孤,指定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取代高拱為首輔,輔佐新君,位極人臣。當時張居正的學生明神宗還只有幾歲,年幼無知,一切軍政大事即均由老師張居正主持裁決。直到萬歷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內閣首輔、太師、太傅、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卒,他在首輔高位上一直干了整整10個春秋!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張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盡其官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尸。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后萬歷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
(摘自《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