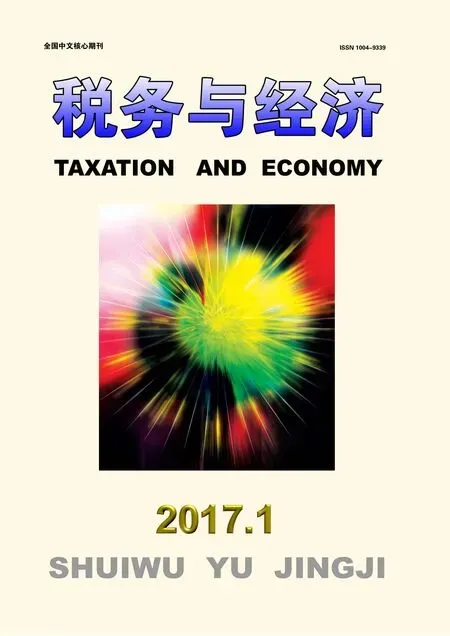財政激勵、政府競爭與企業(yè)投資
張 明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142)
一、引 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已經(jīng)持續(xù)了近40年,這種增長績效一直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許多學者將這種“增長奇跡”歸因于中國式的治理模式激發(fā)了地方政府的活力,使得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張軍,2005)。[1]許多研究表明,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競爭。傅勇和張晏(2007)[2]、李濤和周業(yè)安(2009)[3]、尹恒和朱虹(2011)[4]、李永友(2015)[5]的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省級政府、地市級政府和縣級政府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財政支出競爭策略關(guān)系;而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6]、李永友和沈坤榮(2008)[7]、郭杰和李濤(2009)[8]、龍小寧等(2014)[9]、謝貞發(fā)和范子英(2015)[10]的實證研究則發(fā)現(xiàn),我國各級政府之間存在著稅收競爭策略關(guān)系。
國外關(guān)于地方政府競爭的研究一般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激勵來自于兩種不同的機制。第一,“仁慈的政府(benevolent government)”假設(shè)認為,地方選民的“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機制使得地方政府為了追求連任而以轄區(qū)居民福利作為效用最大化目標而展開競爭(Oates,1972[11];Wilson,1986[12];Zodrow和Mieszkowski,1986[13])。第二,“利維坦式政府(revenue-maximizing Leviathans)”假設(shè)認為,地方政府在任期內(nèi)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將最大化財政收入作為目標而展開競爭(Brennan和Buchanan,1980)[14]。然而,已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地方政府的競爭激勵與國外明顯不同。首先,由于中國的戶籍限制,“用腳投票”機制在中國難以實現(xiàn);其次,在中國現(xiàn)行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制度下,選民“用手投票”機制也難以得到體現(xiàn)。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競爭激勵主要來自于財政激勵和政治激勵。在財政激勵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財政分權(quán)改革增強了地方政府官員推動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動力(Montinola等,1995[15];Qian和Weingast,1997[16];Qian和Roland,1998[17];Jin和Zou,2005[18])。在政治激勵方面, 一些研究認為,中央政府建立的以GDP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晉升錦標賽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獲得政治晉升展開了以GDP增長為目標的競爭(周黎安,2004[19];周黎安,2007[20];Li和Zhou,2005[21];Chen等,2005[22];張軍等,2007[23])。
關(guān)于財政激勵對地方政府財政競爭的實證研究文獻十分豐富。一些研究以財政分權(quán)度作為地方政府經(jīng)濟激勵的衡量指標研究財政分權(quán)對地方政府支出行為的影響,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財政分權(quán)程度的增加會導致地方政府增加生產(chǎn)性支出,減少民生性支出(喬寶云等,2005[24];傅勇、張晏,2007[2];傅勇,2010[25];張宇,2013[26])。Jin等(2005)[27]利用地方政府的財政留存比例來衡量財政激勵的大小,發(fā)現(xiàn)財政激勵對非公經(jīng)濟的增長是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的。王小龍、方金金(2015)[28]關(guān)注了財政“省直管縣”改革所帶來的財政激勵的變化對地方政府稅收競爭行為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財政“省直管縣”改革提高了縣級政府的稅收分成,從而加強了改革縣(市)稅收競爭動機,降低了所得稅實際稅率。呂冰洋等(2016)[29]研究了我國省級以下增值稅和所得稅分成比例對企業(yè)實際稅率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市縣級政府面臨的企業(yè)所得稅和增值稅分成比例上升會加強地方政府稅收征管的意愿,從而導致企業(yè)避稅減少和實際稅率上升。
本文的研究關(guān)注財政激勵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以往的研究認為,財政激勵是導致地方政府展開競爭的直接原因,財政激勵的加強會使得地方政府放松稅收征管、降低實際稅率,增加生產(chǎn)性支出,以提高企業(yè)的投資回報率,吸引資本流入。但是呂冰洋等(2016)[29]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財政激勵的加強也具有激勵地方政府努力征稅的作用。他們用理論模型研究發(fā)現(xiàn),稅收分成率的下降使稅收增長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好處減弱,地方政府征稅積極性降低,從而導致實際稅率下降;反之,稅收分成率的提高使得放松稅收征管的機會成本增加,從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征稅的積極性,導致實際稅率上升。以往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證方面都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稅收分成率的增加會使得地方政府為了擴大稅基、發(fā)展經(jīng)濟而想方設(shè)法促進企業(yè)發(fā)展,吸引投資;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稅收分成率的增加會提高地方政府放松稅收征管的機會成本,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努力征稅,而不利于吸引企業(yè)投資。本文認為,稅收分成率對地方政府會產(chǎn)生兩種激勵作用,即稅收分成率的提高同時會增加政府為擴大稅基而吸引投資的動機,也會提高地方政府為增加稅收收入而努力征稅的動機,而最終的效應(yīng)取決于這兩種作用的相對大小。具體講,財政激勵如何影響政府的行為取決于財政激勵所帶來的稅收收入增加的邊際效應(yīng)與因征稅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的相對大小。即當分成率較低時,增加稅收征管所能帶來的邊際財政收入的增加很小,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相對較大,此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對企業(yè)的征稅意愿,從而有利于吸引企業(yè)投資;當分成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時,增加稅收征管所能帶來的邊際財政收入的增加很大,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相對較小,地方政府繼續(xù)加強征稅會使得資本外流,從而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此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很大程度上增加政府對企業(yè)的征稅意愿,從而不利于吸引企業(yè)投資。因此,本文認為稅收分成率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實證檢驗財政激勵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工業(yè)企業(yè)上交的主要稅種為增值稅和所得稅。本文利用增值稅分成率作為衡量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指標,通過回歸分析實證檢驗增值稅分成率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以揭示財政激勵在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中發(fā)揮的作用。本文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稅收分成率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即當分成率較低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加強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增加了企業(yè)投資;當分成率較高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削弱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企業(yè)投資。
二、實證研究設(shè)計
(一)計量模型

(1)

根據(jù)本文的理論預期,β1應(yīng)當顯著大于0,而β2應(yīng)顯著小于0。在實證檢驗中,本文分別檢驗了增值稅分成率與企業(yè)投資之間是否存在線性關(guān)系和“U型”關(guān)系。實證結(jié)果支持本文的理論預期,研究發(fā)現(xiàn),在回歸中僅加入增值稅分成率一次項時,其回歸系數(shù)不顯著,而分別加入其一次方項和二次方項時,β1顯著大于0,而β2顯著小于0,說明增值稅分成率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
(二)數(shù)據(jù)來源與樣本處理
本文使用的數(shù)據(jù)包括2000~2007年中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和縣級財政數(shù)據(jù) 。其中,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來自2000~2007年的中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增值稅分成率數(shù)據(jù)來自2000~2007年《全國地市縣財政統(tǒng)計資料》。中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是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其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口徑與《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工業(yè)統(tǒng)計口徑一致。該數(shù)據(jù)庫涵蓋了中國工業(yè)行業(yè)中90%以上的企業(yè),是國內(nèi)能夠獲得的覆蓋范圍最廣泛的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由于該數(shù)據(jù)庫具有數(shù)據(jù)量大、指標豐富等顯著優(yōu)點,因而被國內(nèi)外學者廣泛使用。不過,由于該數(shù)據(jù)庫并不是專門的學術(shù)研究數(shù)據(jù)庫,在使用之前需要對其進行相應(yīng)的處理。而且,由于統(tǒng)計局僅公布了1998~2009年的數(shù)據(jù)庫,且2008和2009年的數(shù)據(jù)質(zhì)量較差,一般研究都將數(shù)據(jù)庫時間限定在1998~2007年之間(聶輝華等,2012)。[30]由于《全國地市縣財政統(tǒng)計資料》自2000年開始統(tǒng)計,因此本文的研究樣本時間限定在2000~2007年。
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按照Brandt等(2012)[31]的做法對樣本進行了處理和匹配,并剔除了不符合常理的觀測值。具體的做法如下:(1)按照Brandt等的處理方法,根據(jù)企業(yè)的法人代碼等信息將1998~2007年的數(shù)據(jù)合并成面板數(shù)據(jù)。(2)剔除缺失總資產(chǎn)、職工人數(shù)等重要指標的企業(yè)樣本,剔除總資產(chǎn)小于固定資產(chǎn)等存在明顯錯誤的企業(yè)樣本,剔除銷售額小于500萬、固定資產(chǎn)原值小于100萬、總資產(chǎn)小于100萬和職工人數(shù)小于8人的樣本。(3)根據(jù)Brandt等所提供的方法,計算企業(yè)的實際資本存量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額度,并按照其提供的價格指數(shù)對所有指標進行消脹處理。(4)為了避免異常值對估計結(jié)果的干擾,本文對樣本進行了截尾處理,刪除了各指標上下各0.5%的樣本。最終,本文得到了1998~2007年來自303 837家企業(yè),共994 385次觀測值的樣本數(shù)據(jù)。
(三)變量定義與統(tǒng)計描述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在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中并沒有企業(yè)當年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數(shù)據(jù),需要根據(jù)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存量進行計算。但是,由于企業(yè)在進行財務(wù)核算時,并不是按照固定資產(chǎn)購買的實際值進行核算,而是按照當年的購買價格進行核算,直接將往年價格的固定資產(chǎn)凈值與當年價格的固定資產(chǎn)購買值進行了加總。因此在計算企業(yè)固定資產(chǎn)投資時,一個關(guān)鍵的核心就是對固定資產(chǎn)名義值進行消脹處理。本文按照Brandt等的方法對固定資產(chǎn)進行了消脹處理,計算了企業(yè)當年的固定資產(chǎn)凈值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變量。Brandt等(2012)[31]的處理方法為,首先估計企業(yè)在樣本庫中首次出現(xiàn)時的實際資本存量數(shù)據(jù)。以企業(yè)的出現(xiàn)時間為1998年為例,其估計方法為,使用1993年的年度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在兩位數(shù)行業(yè)中計算1993~1998年的年度資本投資增長率,之后結(jié)合企業(yè)年齡信息計算企業(yè)的年度實際資本投資額度,最后根據(jù)永續(xù)盤存法計算企業(yè)當年的實際資本存量值。在計算資本存量和投資時本文使用Brandt-Rawski deflator資本存量價格平減指數(shù)。按照這一處理方法,本文最終能夠得到企業(yè)當年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額度的實際值,之后使用企業(yè)的總資產(chǎn)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了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invest)。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縣域的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全國地市縣財政統(tǒng)計資料》中分別統(tǒng)計了縣域的增值稅收入和增值稅的75%兩個指標,其中增值稅收入為縣域分得的增值稅收入部分,而增值稅的75%為縣域征收的增值稅總額度的75%。因此,使用增值稅的75%除以0.75即可得到縣域征收的增值稅總額,而繼續(xù)使用縣域增值稅留成收入除以縣域征收的增值稅總額即可獲得縣域的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由于中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中的企業(yè)主要屬于第二產(chǎn)業(yè),其繳納的主要稅種為增值稅,因此本文以增值稅分成率作為衡量縣域財政激勵的核心變量。當然,所得稅分成率在影響縣域財政激勵方面也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統(tǒng)計年鑒中并未公布縣域征收的所得稅總額,無法計算出縣域所得稅的分成率。不過,使用增值稅分成率進行實證檢驗已經(jīng)能夠說明財政激勵對于企業(yè)投資的作用機制。
3.控制變量
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對數(shù)值(lnsize)、企業(yè)年齡對數(shù)值(lnage)、資本密集度(perk)、資產(chǎn)負債率(leverage)、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own)、省虛擬變量(pro)、時間虛擬變量(year)和產(chǎn)業(yè)虛擬變量(io)。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年齡、資本密集度、資產(chǎn)負債率等因素會通過影響企業(yè)的經(jīng)營狀況而影響企業(yè)的投資水平。而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的企業(yè)也具有不同的投資偏好,本文根據(jù)企業(yè)的注冊類型將企業(yè)分為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港澳臺資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并設(shè)置了相應(yīng)的虛擬變量,回歸中以國有企業(yè)為標準,檢驗其他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企業(yè)的投資是否顯著異于國有企業(yè)。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統(tǒng)計
表1中對主要的變量進行了統(tǒng)計描述。其中企業(yè)固定資產(chǎn)投資(invest)的均值為0.139,方差為0.209;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的均值為0.215,方差為0.072,且絕大多數(shù)縣的增值稅分成率為25%;資本密集度(perk)的均值為84.38,方差為109.58;資產(chǎn)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578,方差為0.299;企業(yè)總資產(chǎn)對數(shù)值(lnsize)的均值為9.832,方差為1.214;企業(yè)年齡對數(shù)值(lnage)的均值為1.857,方差為0.935。
三、基本回歸結(jié)果
表2是本文的基本回歸結(jié)果。為了節(jié)省篇幅,表中僅列示了核心解釋變量和主要控制變量的系數(shù)及顯著性。表2第(1)列中僅加入了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未控制省份虛擬變量、行業(yè)虛擬變量、時間虛擬變量及企業(yè)特征控制變量。第(2)列在第(1)列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省份虛擬變量、行業(yè)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第(3)列在第(2)列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企業(yè)特征變量。第(4)列則僅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了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以檢驗增值稅分成率和企業(yè)投資之間是否存在線性關(guān)系。第(4)列中控制了省份虛擬變量、行業(yè)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但未控制企業(yè)特征變量。第(5)列在第(4)列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企業(yè)特征控制變量。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為縣級層面變量,所有結(jié)果均將標準誤聚類到縣級層面。
分別來看表2中各列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第(1)列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的系數(shù)為0.134,增值稅分成率的二次方項(VATshare2)的系數(shù)為-0.145,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第(2)列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的系數(shù)為0.0625,增值稅分成率的二次方項(VATshare2)的系數(shù)為-0.0861,也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相比第(1)列回歸結(jié)果,控制了省份虛擬變量、行業(yè)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之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shù)絕對值有所減小,但沒有改變核心解釋變量的符號及顯著性。第(3)列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的系數(shù)為0.0673,增值稅分成率的二次方項(VATshare2)的系數(shù)為-0.0903,也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相比第(2)列回歸結(jié)果,控制了企業(yè)特征變量之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shù)絕對值、符號及顯著性均未發(fā)生很大的變化。表2第(4)列回歸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的系數(shù)為0.0120,但并不顯著。第(5)列回歸中增值稅分成率的一次方項(VATshare)的系數(shù)為0.0143,也不顯著。表2第(1)~(5)列的回歸結(jié)果表明,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而不是簡單的線性關(guān)系。
表2中企業(yè)特征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也符合本文的理論預期。在第(3)和(5)列中,資本密集度(perk)的回歸系數(shù)約為0.0000775左右,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資本密集的企業(yè)會因加速折舊而增加投資額度。資產(chǎn)負債率(leverage)的回歸系數(shù)為-0.0195,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負債過高會阻礙企業(yè)的投資。企業(yè)規(guī)模(lnsize)的回歸系數(shù)為0.0120,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規(guī)模越大的企業(yè)投資額度越高。企業(yè)年齡(lnage)的回歸系數(shù)為-0.0218,也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注冊時間越久的企業(yè)投資水平越低。可能的原因是新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并不完備,需要進行更多的投資,而老企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已經(jīng)比較完備。比較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可以發(fā)現(xiàn),集體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港澳臺資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均顯著大于0,說明相比國有企業(yè),其他企業(yè)的投資水平更高。
表2的回歸結(jié)果表明,增值稅分成率(VATshare)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這印證了本文的理論假說,即當分成率較低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加強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增加了企業(yè)投資;當分成率較高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削弱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企業(yè)投資。
注:表2中括號外為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括號內(nèi)為t檢驗統(tǒng)計量,*、**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縣級層面變量,所有結(jié)果均將標準誤聚類到縣級層面。N表示樣本數(shù),R2為調(diào)整的擬合優(yōu)度。所有回歸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及時間固定效應(yīng)。
四、異質(zhì)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佐證本文基本回歸結(jié)果的正確性,本文從兩個方面考察了財政激勵對企業(yè)投資影響的異質(zhì)性。首先,企業(yè)流動性會對回歸結(jié)果產(chǎn)生影響。根據(jù)稅收競爭理論,地方政府放松稅收征管是為了吸引流動性資本。因此,當財政激勵發(fā)生變化時,地方政府會更多地改變對流動性強的企業(yè)的干預,以吸引流動性資本,因此流動性強的企業(yè)對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敏感程度應(yīng)當更強。第二,地方稟賦也會對結(jié)果產(chǎn)生影響。根據(jù)Cai和Treisman(2005)[32]的研究,地方稟賦會影響地方政府參與競爭的意愿,稟賦較好的地區(qū)會選擇積極參與競爭,吸引資本,促進經(jīng)濟增長;而稟賦較差地區(qū)即使積極參與競爭也無法吸引到企業(yè),因此會選擇放棄競爭。如此,當財政激勵發(fā)生變化時,稟賦越好地區(qū)的地方政府對企業(yè)的干預力度越強,即稟賦越好地區(qū)的企業(yè)對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敏感程度越強。本文將從以上兩個方面對回歸結(jié)果進行異質(zhì)性檢驗,如果回歸結(jié)果與本文的理論假說相符,則可以進一步說明本文基本回歸結(jié)果的可信性。
(一)企業(yè)流動性對結(jié)果的影響
本文根據(jù)企業(yè)的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來區(qū)分企業(yè)的流動性。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一般為地方政府注資,歸地方所有,其很難流動到其他轄區(qū),流動性較差,而私營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和港澳臺資企業(yè)則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流動性更強。我們可以根據(jù)回歸結(jié)果中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來判斷企業(yè)投資對增值稅分成率的敏感程度,企業(yè)投資對增值稅分成率越敏感,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應(yīng)當越大(即U型越陡峭)。根據(jù)本文的理論分析,我們推測,相比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港澳臺資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的投資水平應(yīng)當對增值稅分成率更敏感。

表3 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企業(yè)的估計結(jié)果
注:表3中括號外為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括號內(nèi)為t檢驗統(tǒng)計量,*、**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縣級層面變量,所有結(jié)果均將標準誤聚類到縣級層面。N表示樣本數(shù),R2為調(diào)整的擬合優(yōu)度。所有回歸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及時間固定效應(yīng)。
表3為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企業(yè)的分組回歸結(jié)果,為了節(jié)省篇幅,表中僅列示了核心解釋變量和主要控制變量的系數(shù)及顯著性。表3中所有結(jié)果使用表2中第(3)列的模型進行估計,均控制了企業(yè)特征變量、省份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及時間固定效應(yīng)。表3中第(1)列為國有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第(2)列為集體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第(3)列為私營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第(4)列為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第(5)列為港澳臺資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第(6)列為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回歸結(jié)果。
比較表3第(1)~(6)列中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我們發(fā)現(xiàn)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的值最大,其他依次為港澳臺資企業(yè)、私營企業(yè)、外商投資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各列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shù)均較為接近10%的顯著性水平,造成某些列系數(shù)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樣本量較少。各列回歸中企業(yè)特征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與基本回歸保持一致。表3的回歸結(jié)果與本文的預期保持一致,相比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私營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港澳臺資企業(yè)和外商投資企業(yè)的投資水平應(yīng)當對增值稅分成率更敏感,即流動性越強的企業(yè)對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敏感程度應(yīng)當越強。
(二)地區(qū)稟賦對結(jié)果的影響
表4實證檢驗了地區(qū)稟賦對估計結(jié)果的影響。表4中分別使用縣域人均GDP和城鎮(zhèn)化率衡量了地方稟賦的好壞,并按照這兩個指標將樣本分為三組。其中第(1)~(3)列為按照人均GDP進行分組的回歸結(jié)果,第(1)列為人均GDP排位在0%~33%的企業(yè)樣本,第(2)列為人均GDP排位在33%~66%的企業(yè)樣本,第(3)列為人均GDP排位在66%~100%的企業(yè)樣本。第(4)~(6)列為按照城鎮(zhèn)化率進行分組的回歸結(jié)果,第(4)列為城鎮(zhèn)化率排位在0%~33%的企業(yè)樣本,第(5)列為城鎮(zhèn)化率排位在33%~66%的企業(yè)樣本,第(6)列為城鎮(zhèn)化率排位在66%~100%的企業(yè)樣本。根據(jù)本文的理論,稟賦越好地區(qū)企業(yè)的投資應(yīng)當對增值稅分成率越敏感,即其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應(yīng)當更大。

表4 不同稟賦地區(qū)企業(yè)的估計結(jié)果
注:表4中括號外為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括號內(nèi)為t檢驗統(tǒng)計量,*、**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縣級層面變量,所有結(jié)果均將標準誤聚類到縣級層面。N表示樣本數(shù),R2為調(diào)整的擬合優(yōu)度。所有回歸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及時間固定效應(yīng)。
表4為不同稟賦地區(qū)企業(yè)的估計結(jié)果,回歸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時間固定效應(yīng)及企業(yè)特征變量,為了節(jié)省篇幅,表4中僅匯報了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比較表4第(1)~(6)列中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按照人均GDP進行分組,還是按照城鎮(zhèn)化率進行分組,稟賦越好地區(qū)的增值稅分成率一次方項(VATshare)和二次方項(VATshare2)回歸系數(shù)絕對值越大,且僅第(3)和(6)列回歸的核心解釋變量顯著。各列回歸中企業(yè)特征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與基本回歸保持一致。表4的回歸結(jié)果與本文的預期保持一致,稟賦越好地區(qū)企業(yè)的投資應(yīng)當對增值稅分成率越敏感。
表3和表4從兩個方面對回歸結(jié)果進行異質(zhì)性檢驗,回歸結(jié)果與本文的理論假說相符,進一步說明了本文基本回歸結(jié)果的可信性。
五、研究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已經(jīng)持續(xù)了近40年,這種增長績效一直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許多學者將這種“增長奇跡”歸因于中國式的治理模式激發(fā)了地方政府的活力,使得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在中國式財政分權(quán)體制下,財政激勵被認為是增強地方政府官員推動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本文的研究關(guān)注財政激勵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理論上,財政激勵如何影響政府的行為取決于財政激勵所帶來的稅收收入增加的邊際效應(yīng)與因征稅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的相對大小。當分成率較低時,增加稅收征管所能帶來的邊際財政收入的增加很小,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相對較大,此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對企業(yè)的征稅意愿,從而有利于吸引企業(yè)投資;當分成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時,增加稅收征管所能帶來的邊際財政收入的增加很大,而抑制企業(yè)投資邊際效應(yīng)相對較小,地方政府繼續(xù)加強征稅會使得資本外流,從而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此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很大程度上增加政府對企業(yè)的征稅意愿,從而不利于吸引企業(yè)投資。由此,本文認為財政激勵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并利用增值稅分成率作為衡量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指標,通過回歸分析實證檢驗了增值稅分成率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以揭示財政激勵在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中發(fā)揮的作用。本文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
(1)稅收分成率與企業(yè)投資之間存在“倒U型”關(guān)系,即當分成率較低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加強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增加了企業(yè)投資;當分成率較高時,稅收分成率的提高會削弱地方政府為吸引資本而展開競爭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企業(yè)投資。
(2)稅收分成率對企業(yè)投資的影響存在異質(zhì)性,且符合地方政府的競爭策略。本文的分組回歸研究發(fā)現(xiàn),流動性越強的企業(yè)對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敏感程度越強,而稟賦越好地區(qū)企業(yè)的投資對財政激勵的變化反應(yīng)越敏感。
本文的研究發(fā)現(xiàn),稅收分成率的變化能夠改變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程度,影響地方政府的競爭策略,從而影響企業(yè)的投資水平。隨著 “營改增”的完成,在中國式稅收制度結(jié)構(gòu)中,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這三大主體稅種均實行稅收分成辦法,由此產(chǎn)生的財政激勵效應(yīng)更加值得政策制定部門的關(guān)注。本文認為,在中國未來的分稅制改革中,應(yīng)當更加重視分稅制所帶來的財政激勵效應(yīng),權(quán)衡利弊,努力實現(xiàn)稅收收入的穩(wěn)定增長和經(jīng)濟的平穩(wěn)發(fā)展。
[1]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為增長而競爭[J].世界經(jīng)濟文匯,2005,(Z1):101-105.
[2]傅勇,張晏.中國式分權(quán)與財政支出結(jié)構(gòu)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管理世界,2007,(3):4-12.
[3]李濤,周業(yè)安.中國地方政府間支出競爭研究——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的經(jīng)驗證據(jù)[J].管理世界,2009,(2):12-22.
[4]尹恒,朱虹.縣級財政生產(chǎn)性支出偏向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1,(1):88-101.
[5]李永友.轉(zhuǎn)移支付與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J].中國社會科學,2015,(10):114-133.
[6]沈坤榮,付文林.稅收競爭、地區(qū)博弈及其增長績效[J].經(jīng)濟研究,2006,(6):16-26.
[7]李永友,沈坤榮.轄區(qū)間競爭、策略性財政政策與FDI增長績效的區(qū)域特征[J].經(jīng)濟研究,2008,(5):58-69.
[8]郭杰,李濤.中國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研究——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的經(jīng)驗證據(jù)[J].管理世界,2009,(11):54-64,73.
[9]龍小寧,等.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中國縣級政府間稅收競爭的實證分析[J].經(jīng)濟研究,2014,(8):41-53.
[10]謝貞發(fā),范子英.中國式分稅制、中央稅收征管權(quán)集中與稅收競爭[J].經(jīng)濟研究,2015,(4):92-106.
[11]Oates, W.. 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12]Wilson J D. A Theory of 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6,19(3):296-315.
[13]Zodrow G R, Mieszkowski P. Pigou, Tiebout,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6,19(3):356-370.
[14]Brennan G.,Buchanan J M..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5]Montinola G,Qian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J].World Politics,1995,48(1):50-81.
[16]Qian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11(4):83-92.
[17]Qian Y,Roland 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
[18]Jin J, Zou 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signments, and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5,16(6):1047-1064.
[19]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shè)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經(jīng)濟研究,2004,(6):33-40.
[20]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jīng)濟研究,2007,(7):36-50.
[21]Li H, Zhou L A.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743-1762.
[22]Chen Y, Li H, Zhou L A.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J].Economics Letters,2005,88(3):421-425.
[23張軍,等.中國為什么擁有了良好的基礎(chǔ)設(shè)施?[J].經(jīng)濟研究,2007,(3):4-19.
[24]喬寶云,等.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與小學義務(wù)教育[J].中國社會科學,2005,(6):37-46.
[25]傅勇.財政分權(quán)、政府治理與非經(jīng)濟性公共物品供給[J].經(jīng)濟研究,2010,(8):4-15.
[26]張宇.財政分權(quán)與政府財政支出結(jié)構(gòu)偏異——中國政府為何偏好生產(chǎn)性支出[J].南開經(jīng)濟研究,2013,(3):35-50.
[27]Jin H, Qian Y, Weingast B R.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 89(9):1719-1742.
[28]王小龍,方金金.財政“省直管縣”改革與基層政府稅收競爭[J].經(jīng)濟研究,2015,(11):79-93.
[29]呂冰洋,等.分稅與稅率:從政府到企業(yè)[J].經(jīng)濟研究,2016,(7): 13-28.
[30]聶輝華,等.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現(xiàn)狀和潛在問題[J].世界經(jīng)濟,2012,(5):142-158.
[31]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and Yifan Zhang.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97:339-351.
[32]Cai H, Treisman D.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 817-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