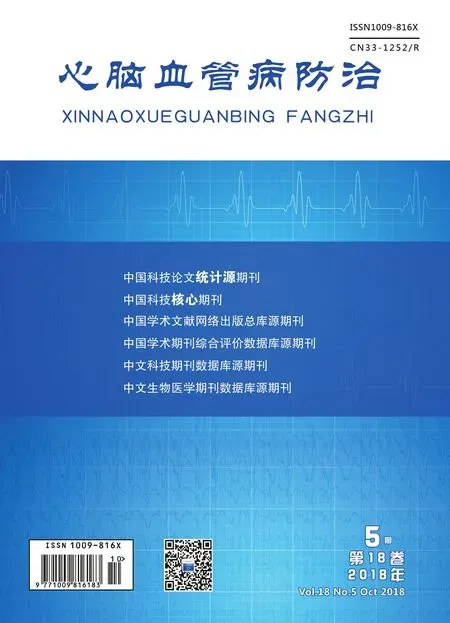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在膿毒性心肌病診斷中的研究進展
袁佳輝,蔡國龍
膿毒癥是感染引起的宿主反應失調所導致的致命性器官功能障礙,嚴重時可發展為膿毒性休克,具有很高的死亡率[1]。心臟是膿毒癥最容易受損的靶器官之一,膿毒性心肌病(sepsis_induced cardiomyopathy,SIC)可表現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使病死率增加70%以上,因此需要緊急識別和及時治療[2]。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和肌鈣蛋白(Troponin)及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等心臟生物學指標已被應用于SIC的早期診斷,但敏感度和特異度均有局限性,可能不是反映膿毒癥患者心肌功能障礙的可靠指標,與預后的相關性也存在爭議,目前在臨床實踐應用中面臨挑戰[3]。二維斑點追蹤成像技術(two_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2D_STI)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新技術,可以準確評價心肌整體和局部的功能[4]。應用2D_STI測量左心室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能發現亞臨床狀態下的心肌運動異常,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發生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5],其在SIC的早期診斷,對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評估研究中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本文將就GLS在SIC診斷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簡要綜述。
1 SIC在診斷面臨的挑戰
SIC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可能存在線粒體功能障礙、細胞因子釋放、氧化應激、炎癥反應等多種原因[3]。1984 年 Parker等[6]在研究中首次提出SIC的概念,研究發現大約一半的膿毒性休克患者LVEF基線嚴重降低,矛盾的是幸存者平均LVEF較低;通過使用放射性核素攝影發現幸存者的左心室明顯擴張。目前SIC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多數臨床研究對其定義僅基于患者在沒有任何基礎心臟疾病的情況下,LVEF低于45%至50%,且出現可逆性的緩解,但這并不嚴謹[7,8]。有文獻認為診斷應包括以下三個特點:左心室擴張,伴有正常或偏低的充盈壓;LVEF的下降;通常改變是可逆的,能在7~10天內恢復正常[2]。現有的診斷方法主要集中在LVEF和Troponin及BNP等心臟生物學指標,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Troponin和BNP通常在膿毒癥患者中普遍升高[9],似乎只是反映了病情的危重程度并不特異于 SIC[10,11]。事實上包括右心室超負荷,兒茶酚胺類藥物的治療和細胞因子產生增加在內的許多因素都可能導致膿毒癥期間BNP的釋放[10]。而Troponin升高的確切病因尚不清楚,可能歸因于炎性介質導致心肌細胞膜通透性的增加,因為病理解剖并沒有發現SIC有心肌組織結構壞死或細胞死亡的證據[11]。伴隨著重癥超聲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其因無創性、床旁操作的便攜性等優勢已經逐漸代替了其他手段而成為診斷SIC的主要工具。目前最常用的指標是LVEF,它是不依賴于心肌收縮功能的負荷依賴指數,主要反映了左心室的圓周方向縮短,因此沒有考慮縱向排列的心內膜下心肌纖維比周圍排列的心肌纖維更早出現局部缺血和纖維化[6]。LVEF是心室功能的整體指標,對局部心肌異常不敏感,可能不是反映膿毒癥患者心肌功能障礙的可靠指標,與預后的相關性也存在爭議。首先LVEF反映的是左心室收縮和左心室后負荷偶聯疊加的結果。換句話說,盡管左心室心肌內在收縮力嚴重降低,但當后負荷嚴重受損時,仍可觀察到正常的LVEF;相反,患者血管張力的保存和恢復可能會揭示LVEF的實際減少[12]。其次 Vieillard_Baron等[13]研究認為膿毒癥患者低LVEF所定義的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評估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率會進一步上升,從第1天至第3天,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從約40%上升至約60%。有研究顯示膿毒癥患者低LVEF具有較好的預后,且不增加長期心力衰竭結局的風險[14]。但近年來有些相互沖突矛盾的數據開始出現。一項來自14項研究包括700多名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支持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的幸存者具有較低的LVEF[7]。另一項薈萃分析提示低LVEF與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患者30天死亡率并無相關性[8]。因此對于SIC的治療尋求更有價值的診斷和評估預后的指標具有非常重要的臨床意義。
2 GLS在SIC中的臨床應用
膿毒癥導致的進行性心肌功能障礙與射血分數無法敏感準確的發現心肌異常變化之間的這種對比,可以通過更復雜、更先進的測量方法如心肌應變來解決。2D_STI是一種非侵入性、無角度依賴的新技術,通過追蹤心肌中超聲斑點的運動,評估不同層心肌纖維的變形,更好地展現了心臟生理學和力學結構的改變,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4]。其中最常用的檢查參數是應變,定義為收縮末期心肌纖維長度與舒張末期原始長度相比的變化,以百分比表示。應變可以在縱向、徑向和圓周方向測量。心肌長軸方向的整體縱向應變,表示各節段室壁在心臟長軸、沿心肌縱行纖維方向上的平均應變值,在收縮期心肌節段室壁縮短時為負值,舒張期伸長時為正值。GLS被認為優于大多數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能敏感地發現心肌功能的細微變化并能評估預后。已有文獻指出GLS可在LVEF正常的高齡、高血壓、糖尿病、穩定型心絞痛、腎功能不全和肥胖等患者中出現異常改變,對LVEF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預后評估具有潛在價值[15]。Williams等[16]研究指出左心室縱向收縮主要由心內膜下縱向排列的心肌纖維完成,而心內膜下心肌纖維對心肌缺血及心肌間質纖維化較為敏感,因此在心功能不全早期左心室縱向應變即可改變,而心室壁中層環形排列的心肌纖維受間質纖維化及缺血影響較晚,左心室圓周向收縮力可代償減低的縱向收縮力,因而射血分數值得以保持正常,然而此時心肌收縮功能實際上已受損。雖然目前沒有證據支持SIC冠狀動脈血流的減少,但微血管的改變可能與局灶性缺血有關[17],這可能解釋了為什么在膿毒癥患者中心肌整體縱向功能更容易受到影響。GLS能敏感的發現心肌運動的異常改變,其在SIC的早期診斷,對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評估研究中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
2.1 GLS在SIC診斷中的作用:Orde等[18]對60例收入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療的膿毒癥患者進行研究發現,若以LVEF≤55%定義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則有33%的患者存在異常,但使用 GLS≥ -17%定義時則為69%。Boissier等[19]對132例膿毒性休克患者研究發現,多于70%的患者GLS存在異常(包括所有LVEF≤45%的患者)。Dalla等[20]發現在LVEF正常的膿毒癥患者(n=48)中有50%的患者 GLS出現異常(GLS≥ -15%),與LVEF正常的重癥創傷非膿毒癥患者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GLS(P <0.05)。Geer等[21]在研究中發現,膿毒性休克患者的GLS與LVEF、二尖瓣環運動速度和N末端腦利鈉肽前體(N_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_proBNP)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但是GLS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善,這可能表明GLS比其他指標更能代表膿毒性休克時心肌微妙的異常變化,甚至在臨床恢復后仍可存在異常。其他的研究也指出GLS比低LVEF所定義的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更有助于 SIC的早期識別診斷[22~25]。SIC可表現出氧輸送(oxygen delivery,DO2)與氧消耗(oxygen consumption,VO2)之間的不平衡并且可導致低的中心靜脈血氧飽和度(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ScvO2)和乳酸水平升高,臨床醫生通常依靠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和 ScvO2來指導治療以改善DO2,這些參數通常需要中心靜脈導管的存在,但這增加了包括感染在內的并發癥風險[1]。除了放置導管風險增加之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CVP和ScvO2用于指導治療是有問題的[1]。與CVP或ScvO2的獲取需要侵入性導管相反,2D_STI的操作具有無創、簡單快捷等優點,可能是評估膿毒性休克患者 DO2有吸引力的工具。Lanspa等[26]發現GLS與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患者的低ScvO2、高乳酸血癥相關,在LVEF正常的患者中有60%的患者存在應變異常(GLS≥-17%),16%的患者存在嚴重應變異常(GLS≥-10%),GLS與低ScvO2有關(r= -1.05,P<0.01;比值比(OR)=1.23 for ScvO2<60%,P<0.01),嚴重應變異常患者的ScvO2顯著降低(56.1%vs 67.5%,P<0.01),乳酸明顯升高(2.7 vs 1.9mmol/dl,P <0.05),GLS可能是非侵入性的氧輸送的替代性指標,對早期發現SIC導致的氧代謝異常有重要意義。膿毒癥患者的心動過速與臨床結局惡化有關,然而高超能狀態下的心動過速原因尚不明確,可能是SIC導致的心動過速,也可能是心臟對低前負荷的適應性反應,因此心動過速可能不是簡單的評估疾病嚴重程度增加的替代指標[27]。一項包括452例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患者的最新研究發現,54%的患者出現應變異常(GLS>-17%),應變異常的患者有更高的心率(100 vs 93次/分鐘,P<0.01),GLS與心率有關(r=0.05,P<0.01),這種相關性在高前負荷患者(r=-0.22,P<0.01)和休克患者(r=0.07,P<0.01)中持續存在,但在低前負荷患者中不存在[28]。因此當控制心臟前負荷時,GLS作為敏感的心肌功能障礙指標可能就是心動過速有用的替代指標,為識別SIC導致的心動過速提供有效的證明。
2.2 GLS在膿毒癥危險分層和預后評估中的作用:很大一部分膿毒癥患者最初是在急診室管理的,這是一個非常繁忙的環境。對膿毒癥患者進行合理的危險分層可能有助于及早發現高危患者,合理分配醫療資源,保障患者的有效治療。Ng等[22]研究發現,膿毒性休克患者和膿毒癥患者的GLS有統計學意義(-14.5%vs-18.3%,P<0.01),對于能在72h內停用升壓藥物的膿毒性休克患者,GLS存在前后差異(-14.6%vs-16.0%,P<0.05),但非幸存者則無統計學意義(-15.3%vs -15.8%,P>0.05),Ng認為這支持了目前對于SIC存在可逆性的認知。Shahul等[29]研究顯示,在24h內膿毒性休克組的GLS明顯惡化(-15.08%vs-12.67%,P<0.01),而膿毒癥組的 GLS無變化(-16.66% vs -15.74%,P >0.05)。Palmieri等[23]的研究發現 GLS與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患者的28天死亡率有關(P=0.05),并且GLS在LVEF正常的膿毒性休克患者中有很大的差異性,特別是對于那些可能被誤認為保留了心肌收縮功能的患者,這為GLS成為判斷病情嚴重程度的潛在工具提供了合理性。在膿毒癥診治過程中,依據病情嚴重程度及早采取預措施,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患者的預后。楊菲等[30]在研究中發現,與健康對照組比較,膿毒性休克組GLS明顯增加[(-17.72±1.35%)vs(-22.07±1.95%),P<0.01],并且是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逐漸增加;在膿毒性休克組中,非幸存者與幸存者相比,GLS在治療第3天時就出現差異[(-14.44±0.92)%vs(-16.36±1.00)%,P<0.05],而 LVEF于治療第7天才明顯低于幸存者,因此GLS的異常提示病情的進一步加重,加強對GLS的關注可避免錯失早期治療心肌抑制的時機,從而降低死亡率。目前針對膿毒癥患者的個體化治療,特別是在短期內需要更多準確的指標評估預后,以便對臨床治療管理產生有利影響。序貫器官衰竭估計評分(sepsis_related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已被用于膿毒癥患者的預后分層,在大型的隊列研究中表現出中等程度的預測院內死亡率的能力[1]。Innocenti等[24]通過對 147 例膿毒癥患者研究發現,GLS會隨著SOFA評分的升高、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的發生而明顯增加;兩者對膿毒癥患者短期預后價值的比較顯示,GLS在7天病死率的預測價值明顯優于SOFA評分(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UC)=0.73 vs 0.635),將GLS納入SOFA評分體系中可能有助于預后評估。Chang等[25]研究顯示,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II)和GLS是膿毒性休克患者在ICU和醫院內死亡的獨立預測指標。GLS截斷值為-13%時預測死亡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6%和82%,AUC為0.79。GLS≥-13%的患者表現出更高的ICU和住院死亡率(風險比(HR)=4.34,P <0.01和HR=4.21,P <0.01),將 GLS信息添加至APACHE II可進一步提高預后判斷的價值。不同的是,Orde等[18]對60例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患者的研究發現,GLS在第30天和第180天的隨訪中并未被發現是全因死亡的獨立預測因子,但右室游離壁應變(right ventricular longitudinal strain free wall,RVLS-(FW))與患者 6 個月死亡率(OR=1.1,95%CI=1.02 ~1.26,P=0.02,AUC=0.68)適度相關。在Zaky等[31]的研究中,GLS與膿毒性休克患者的機械通氣持續時間、醫院或ICU總住院時間或死亡率無關,但基底部前段的縱向應變增加與死亡率相關(P<0.01)。因此GLS或其他應變指標在膿毒癥患者中的應用及預后價值還需要在大規模多中心的臨床研究中進一步確認。
3 不足
GLS也存在一些缺點,限制了它在膿毒癥患者上的臨床應用。首先2D_STI技術本身存在局限性[4],采用過高的幀頻會導致空間分辨率的降低影響追蹤質量,而過低的幀頻使斑點過快移出追蹤平面導致追蹤質量不佳;GLS存在圖像依賴性,而高質量的掃查常常受到機械通氣、不理想的患者體位等干擾,影像質量會欠理想,影像的解讀也變得復雜,因此必須密切結合臨床。其次膿毒癥患者往往會接受持續的多模式重癥監護治療包括鎮靜、機械通氣、液體復蘇、血管活性藥物治療以及腎臟替代治療等,因此必須考慮這些治療方式本身可能影響心肌功能的可能性。正如Franchi等[32]已經研究證實機械通氣對應變存在干擾,高水平的呼氣末正壓通氣(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PEEP)會使應變值降低。最后對于GLS的臨床應用,標準值的定義是至關重要的。基于最新公布的指南[4]左心室GLS的標準值≤-15%,但目前各項臨床研究[9,18~21,24,25,29]的應變值缺乏統一,不同設備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分析軟件頻繁升級會導致參考值的改變,最終會影響其在臨床的進一步應用。
4 展望
2016拯救膿毒癥運動指南[1]建議早期識別和治療膿毒癥引起的心肌功能障礙,好處在于及時通過優化冠狀動脈血流灌注,實施液體復蘇,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并可能使用β受體阻滯劑等各種治療手段來保護心臟降低死亡率。GLS有助于SIC的早期診斷,對膿毒癥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也有一定的評估價值,具有臨床應用普及的可行性。對于危重疾病研究而言,長期結果越來越重要,膿毒癥患者的后期發病率和死亡率持續存在,至少部分原因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增加[33]。這些是否與SIC有關尚不得而知。因此,通過GLS對SIC的后續跟蹤是重要的研究和臨床優先事項。未來的研究重點還可放在2D_STI的其他指標,如組織二尖瓣環位移(tissue mitral annular displacement,TMAD)、RVLS-(FW)已經在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診斷、進展和治療中顯示了重要的臨床價值[4]。此外,技術創新也是必不可少的,隨著實時三維超聲技術的發展和完善,三維斑點追蹤成像技術(three_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3D_STI)比2D_STI更能真實的反映心肌的運動和變形,未來可應用于SIC發現潛在的臨床價值[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