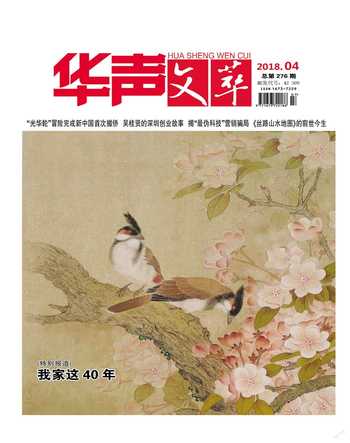小家巨變
1998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之際,我出版了70萬字的《鄧小平改變中國》。如今,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的時候,這本書又在重印之中。當年,我滿懷激情寫出這部長篇報告文學是因為對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著切身的感受。
我收到了第一筆稿費
在“文革”中,雖然我出版了10本著作,每次出書只是收到出版社寄來的50本樣書,并無稿酬。那時候“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我“上有老,下有小”,僅靠菲薄的工資時常捉襟見肘。
“文革”結束之后,稿酬制度的恢復,使我走出了多年來經濟拮據的窘境。記得當時我收到的第一筆稿費,是《化學與農業》一書的增補稿費。
《化學與農業》是一本科普讀物,從1963年5月初版時的6萬字,到1975年2月再版擴充到8萬字,以及后來擴充至16萬字。“文革”結束,這本書的新版本在1977年2月印出,我以為仍然沒有稿費。誰知過了一段時間,忽然收到出版社通知,說是恢復稿費制。由于新版本比第二版增加了8萬字,按照當時每干字4元人民幣的稿費標準,人民出版社寄來320元稿費。這筆稿費解決了我家經濟上的燃眉之急。我一收到,第一件事就是給兩個兒子買了新書包,給妻子買了一套新衣服。
此后,隨著我的一大批新著問世,我家在經濟上翻了身。
分了一套房
1979年6月,我所在的上海科教電影廠通知我,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一套4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新房子給我,以改善我的居住條件。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后來我才知道,上海市政府是根據國務院副總理方毅1979年1月6日的批示,給我分配新居的。方毅批示說:“調查一下,如屬實,應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葉永烈同志的工作條件。”
方毅副總理怎么會知道我的工作條件很差呢?原來,那是《光明日報》記者謝軍到我家采訪之后,曾寫了一份內參(后來在1979年2月15日發表于《光明日報》頭版),內中寫道:“他創作條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歲,小孩8歲)擠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無光,竹片編墻,夏熱冬涼,門口對著一家茶館,喧鬧嘈雜。每年酷暑季節,他就是在這樣的斗室里,不顧蚊蟲叮咬堅持揮汗寫作”。
拿到房門鑰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出版不久的《小靈通漫游未來》放進了新居。她說,“我們家第一個住進新房子的是小靈通!”《小靈通漫游未來》是我在1961年寫的。當時連飯都吃不飽,像這樣描寫美好未來世界的書理所當然遭到退稿。“文革”中,我被抄家時,《小靈通漫游未來》手稿差一點毀于劫難。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春風吹拂下,這顆被遺棄的種子發芽了,一下子印了300萬冊,成了超級暢銷書。這本書直至今日仍在不斷印刷。
如今我的家不僅擁有私家游泳池,而且擁有50平方米的客廳,與當年的小屋有著天壤之別了。
第一次在家接待外國記者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實行對外開放,打開了國門。我在上海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美國、日本、英國作家。最初,國門開而家門閉。我當時擔任上海市科協常委,談話總是在科學會堂的外賓接待室里進行,宴請也都是“公宴”。位于上海南昌路的科學會堂原本是法租界的法國總會,典雅而華麗。
1982年,英國記者房義安要求采訪我。按照“慣例”,請他到上海科學會堂。但他卻說:“何必在辦公室談話?我希望看一看中國作家的家。”我趕緊請示領導,“家門”能否開放?領導指示折中一下,于是我在上海和平飯店會見了那位英國記者。
不料,在與他會面之后,他又提出上我家采訪。我不得不向領導再次請示。“好吧,就讓他上你家。”領導同意了,關照我把家里的內部文件收好,打掃一下,干干凈凈接待外賓。這樣,我的家門頭一回對外“開放”。那位英國記者來了。當他拿出錄音機時,我在旁邊也放了我的錄音機——因為第一次在家里接待外賓,萬一這位大胡子記者對外亂寫報道,我有錄音帶作證,以免“麻煩”。經歷過“文革”苦難的我,不得不多加小心。
后來才知道,那位英國記者非要上我家不可,純屬好奇之心。因為他聽我說出過好多書,尤其是《十萬個為什么》印了近億冊,很想來我家看個究竟。進門之后他哈哈大笑:“我以為你家有私人飛機呢。原來,中國作家的家,也普普通通!”
自從那位英國記者來了之后,我家也就對外開放了。日本作家來了,美國作家來了,聯邦德國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和夫人來了,我也都在家里接待并設宴款待……一位日本朋友來過多次,熟了,甚至像老朋友似的,敲敲門就進來了,事先連招呼也不打(那時候我家只有傳呼公用電話,沒有“宅電”)。
蘇聯作家博布洛夫也來我家作客
不過,那時候我跟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卻一直沒有交往。只有捷克的一家雜志刊載了我的小說之后,來過信,說是來華時定前來拜訪,但沒有成行。
中蘇關系的冰河終于漸漸解凍。于是,我家迎來了稀客——蘇聯哈薩克斯坦作家協會的作家博布洛夫·阿里克薩德爾·阿里克薩德洛維奇。
那天下午2時,我家門鈴響了。我用俄語說:“您好,博布洛夫同志!”他呢,也稱我和妻為“同志”。我發覺,跟蘇聯同行聊天,共同的話題比西方同行更多。談斯大林的功過,談赫魯曉夫的是非……他很有興趣地翻閱著我的書架上的《戈爾巴喬夫傳》以及戈氏《改革與新思維》中譯本。
在家里,我們用上海菜招待遠方的來客。有上海茭白、炒鱔絲,還有螃蟹。博布洛夫學著我們的樣子,掰開螃蟹,猶猶豫豫地咬了一口,馬上笑起來說:“味道好極了!”
吃罷,他若有所思地進行了一番比較:“蘇聯人跟上海人的不同是,蘇聯人第一道菜是湯,而上海人則最后一道菜是湯。不過,這只是個順序問題,我們的共同點是都愛喝湯!”說完,他又歡快地笑了起來。
這笑聲使我想起那位英國記者頭一回來我家訪問時我們的拘謹、緊張。過去了,都過去了。國運盛而家運昌,我小小的家門,是在國門開放的年代里逐漸打開的……
兩個兒子都赴美國留學
中國敞開了國門,出國成了潮流,人稱“出國潮”。“出國潮”也沖擊著我的家。
學好英語,考好“托福”,成為當時中國年輕人前往美國留學的必經之路。我的兩個兒子都加入了考“托福”的隊伍。長子白天在大學里讀專業課程,入夜則到夜校進修英語,啃“托福”課本。啃完“托福”,接著又啃“GK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他買了張美國地圖,貼在他的書桌前天天看,對美國的五十個州了若指掌。
長子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國營企業里工作。那家企業里有許多外國專家,領導得知他的英語很好,就讓他擔任英語翻譯。不過,就在他擔任英語翻譯的時候,人事科科長調侃地對他說:“哦,你是我們廠的第八任英語翻譯。前面七任都已經到美國去了,我看你很快也會去美國!”人事科科長的話沒錯。經過“托福”考試,我的長子收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那時候,在上海烏魯木齊路,飄著星條旗的美國駐滬領事館門前,入夜便排起簽證長隊。我的長子也加入了這支隊伍。上午8時多,這支隊伍開始蠕動。從大門里出來的人,只消看一下臉色,便知道“晴雨”。我的長子板著面孔走了出來,不言而喻,被美國人拒簽了——原因是他雖然被美國大學錄取了研究生,但沒有獲得獎學金。那時候,光是被美國大學錄取卻沒有獎學金,通常是會被拒簽的。好在長子是個很開朗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再考“托福”和"GKE"。功夫不負有心人。當他又收到一封美國來信時,忽地歡呼雀躍起來——美國一所大學給了他全額獎學金。
身邊的榜樣最有力量。老二見哥哥去了美國,也加緊學習英語。兩年之后,他也坐上飛往美國的飛機。
我和妻子首牽手,游全球
緊接著,1993年11月30日,我和妻子開始第一次美國之行。我剛剛抵達洛杉磯,連東南西北都還沒弄清楚,就被美國聯邦影視集團電視臺接去,在那里接受專訪。圣誕節前夕,我和妻從洛杉磯飛往匹茲堡,長子開著他在美國買的的二手車,駕車帶領我們去他弟弟那里,我們全家終于在美國團聚。
從那以后,我和妻10次去美國,兩個兒子都在美國成了家。我和妻“手牽手,游全球”。我游歷一個個國家,注重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去觀察。在我看來,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歷史是人類的腳印。只有以文化和歷史這“雙筒望遠鏡”觀察世界,才能撩開瑰麗多彩的表象輕紗,深層次地揭示豐富深邃的內涵。我把我的所見、所聞、所記、所思凝聚筆端,寫出一部又一部“行走文學”作品。我還拍攝了大量精美的照片,作為書的插圖。如今,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葉永烈看世界”叢書,已達22部。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以小見大。我的小家巨變,見證了40年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