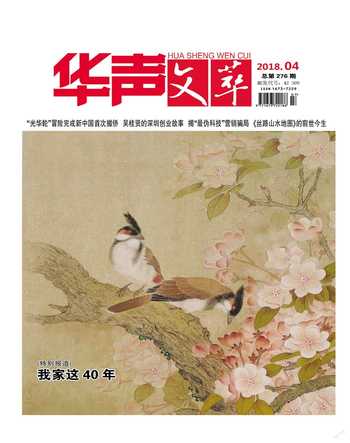“車”的變遷:伴我走過美好時光
1980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家鄉所在縣唯一的一所重點高中。我家住在鄉下,離縣城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那時候的交通條件落后,只好選擇住校。每個月我都需要回一次家取些東西和生活費。班里只有幾個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同學有自行車,我家里條件一般,每次往返四十多里的路程主要靠步行,只是偶爾才向同學借輛自行車用。那時最大的渴望是能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
經過兩年的苦讀,我終于如愿考上了一所國內知名大學,成了“文革”后村子里的第一個大學生。記得赴大學報到那天,父親和哥哥坐著生產大隊的拖拉機,將我送上了開往大學所在城市的火車,從此踏上了我漫長的求學之路。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沈陽郊外的一家單位工作。那時候沈陽郊區的交通還不很便利,只有一條郊區公交線路通達市里,并且要隔上一個多小時才會有一班車發出。這條線配備的車都是些老得快掉牙了的舊車,一跑起來就冒濃濃的黑煙,開起來慢騰騰的,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要開將近兩個小時。那時候我與妻尚處在戀愛階段,所以每個周日(那時候沒有大禮拜,每周只在周日休息一天)的早晨,我都要早早擠上那班車去城里。
后來我們結婚了,由于暫時沒有住房,只好將小家安置在單位院內的一間宿舍里。妻子工作單位在市里,每天需要早早起來趕這趟公交車去城里的單位上班。我們的小家到公交車站要走三十多分鐘,妻子堅持了一個月就叫苦不迭,于是我們商量買輛自行車。那時我剛畢業不久,工資82元,而一輛普通的自行車就要將近兩百多元,我們既無外援也無內援,要買輛自行車相當吃力。于是我們厲行節約,苦苦攢了四個月才湊夠了錢,買了輛沈陽自行車廠產的“白山牌”自行車。
有了這輛車,的確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便利,比如每天早晚我可以用它接送妻子上下班、家里買米、買菜、換煤氣等也方便了很多。有了兒子后,我又用它接送兒子去托兒所。周末時,我騎著車,前面坐著兒子,后面馱著妻子,一家人其樂融融去公園玩。
上世紀90年代,沈陽的公共交通得到了很大的改觀,出門乘坐公交車也比以前要便利得多了。另外,隨著家庭收入水平不斷增加,我們家庭的出行方式也逐漸在改善,打車出行也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上世紀90年代沈陽流行騎摩托車,我們小家也添置了一輛“雅馬哈100”摩托車。這輛摩托車是我們家庭“劃時代”的標志,是我們的家庭第一次步入“機械化”的時代。
2000年后,私家車悄然進入尋常百姓家,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買了車。妻子和兒子強烈要求我們的小家也應該盡快進入汽車時代。他們倆時不時的就去汽車行和網上收集各種車的資料,然后很專業地進行討論分析。我看母子倆整日喋喋不休地爭論,就不失時機地建議,為什么不考慮一下我們自己的民族品牌呢?比如我們沈陽生產的中華牌轎車。我給出了選擇中華車的三條理由:其一,中華車銷量不錯且已走出國門,品牌的知名度與日俱增;其二,外形不失尊貴價格相對又低;其三,本地產的維修保養也方便,同時中華車還是中國第一款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國產車,支持國貨,支持民族品牌。我的三大理由得到了母子倆人的一致贊同,于是不久一輛嶄新的中華車開了回來,我們的小家庭也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里,和很多人一樣走入了家庭的汽車時代。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的城市在變得日新月異,我們的生活在變得越來越美好。步行、自行車、摩托車、汽車、公交車、出租車、地鐵……四十年來,我分別借助不同的交通工具走過了人生中一段段美好的時光,讓我從一個鄉野孩童成為一名大學教授,這些變化不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