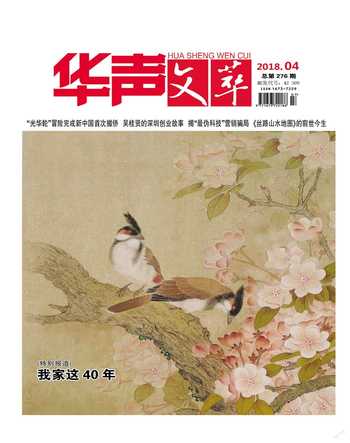她為新中國捐了一個博物館
王悅陽
還記得央視《國家寶藏》嗎?節(jié)目中,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大克鼎無疑是一大亮點。它是青銅轉(zhuǎn)變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與大盂鼎、毛公鼎并稱為“海內(nèi)三寶”。說起這件國寶,離不開蘇州潘家藏鼎、護鼎、捐鼎的動人故事,更離不開潘家的女護寶人潘達于。
盂克二鼎齊聚潘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僅24歲的潘世恩進京趕考,一舉奪魁中了狀元,以后在京師官運亨通達50余載。潘世恩共有五個兒子,嫡系孫輩中有一支為潘祖蔭、潘祖年兩兄弟。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陜西岐山禮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紳宋金鑒購得,后來輾轉(zhuǎn)到清朝大臣左宗棠的手里。咸豐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咸豐皇帝力保左宗棠,左才獲脫免。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之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而大克鼎出土于陜西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態(tài)買下,潘祖蔭又用重金從柯氏手里購得,成為大克鼎的主人。于是,二鼎團圓,兩件周朝時期最大的青銅器齊聚潘府,成為當時京城的一大新聞。
潘祖蔭一直無后,他在北京去世后,遺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后由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運回故鄉(xiāng),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潘家舊宅中。隨后,潘祖年把兩個兒子過繼給潘祖蔭,但也相繼早夭。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鏡被過繼過來,成為潘祖蔭和潘祖年兩家的孫子。
然而,潘承鏡過繼給潘祖蔭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個新婚僅三個月的妻子潘達于,沒有留下子嗣。因此,剛過門不久的潘達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門戶的重任,守著大量珍貴文物借住在蘇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舊宅里。
潘家寡婦艱辛護寶
潘家式微之后,覬覦寶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來。清末權臣端方就曾對潘家人百般糾纏,想要“借”走兩尊寶鼎。幸運的是,時值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政府在內(nèi)憂外患中垮臺,端方成了斷頭鬼,潘家寶鼎才得以存留。
此后,有一位酷愛中國青銅器的美國人漂洋過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資外加一幢洋樓來換取盂、克二鼎,但年輕的潘達于不為所動,一口回絕。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國民黨當局在蘇州新建一幢大樓。某大員突發(fā)奇想,要在大樓落成后以紀念為名辦一場展覽會,邀潘家以大鼎參展。然而此拙劣伎倆被潘氏識破,婉言拒絕了參展。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后,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抵臨蘇州騷擾轟炸。八月十八、十九兩天,情急之中的潘達于打定主意要密藏這批寶物。她叫來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個結(jié)實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圓木直接釘牢,然后在夜間,撬開住處的地面方磚掘個坑,先放人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對角慢慢放進箱子,空當里塞進一些小件青銅器及金銀物件,隨后蓋好箱蓋平整泥土,按原樣鋪好方磚。
書畫和部分古董則放進了夾弄里的三間隔房“三間頭”。當時潘家的藏書有十幾個大櫥,不好搬動,潘達于請來姐夫潘博山,把書畫按宋元明清朝代分類,放到書箱里,裝了三十來箱,以及卷軸、銅器等等,搬進“三間頭”,小門關嚴,外面用舊家具堆沒,收拾得隨隨便便,外人一點也看不出端倪。
日本人攻陷蘇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達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絲毫都沒有動搖。日軍前后七次闖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雖然財物損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間頭”一直都沒有被發(fā)現(xiàn)。
國寶歸公只留獎狀
1949年5月,蘇州、上海相繼解放。同年8月,上海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頒布了保護文物的法令和政策。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坎坷,潘達于認識到,單憑她一家人的力量,根本無力保護好這兩只寶鼎,只有交給人民政府才能妥善保護好它們。當即將要成立上海博物館的消息傳到老人耳中,潘達于決定要把“失蹤”的寶鼎捐出去,給全國人民看看。
剛剛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以隆重的授獎典禮表彰潘氏捐獻之舉。按理說,當時兩尊寶鼎的市值已是天價,對一下子就獻出兩寶的潘達于,政府自然也相當重視,決定給她發(fā)一筆數(shù)目不小的獎金。可當時并不富裕的潘達于卻拒絕了這筆獎金,直接把它捐到了抗美援朝的戰(zhàn)場上,只留了表彰獎狀在自己的臥室,繼續(xù)她普通的勞動者生活。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二鼎如愿入館,使國人第一次飽覽了這聞名半個多世紀的“國之重器”。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開館,大盂鼎等125件珍貴文物應征北上。兩件巨鼎自此各鎮(zhèn)一方。大克鼎則當之無愧地成為上博的鎮(zhèn)館之寶。
繼獻鼎之后,在潘家后人的支持下,潘達于又陸續(xù)分批向國家捐獻了大量文物,現(xiàn)在還保存于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捐獻字畫九十九件:1957年捐獻字畫一百五十件;1959年捐獻一百六十一件文物。另外還捐獻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畫,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冊》、沈周的《西湖名勝圖冊》等,可以說捐獻了一個博物館。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