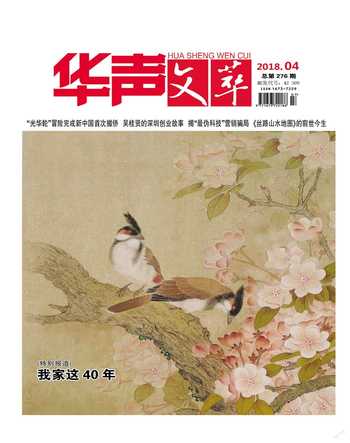海納百川為何成海納“萬污”
崔慧瑩
在北起遼寧鴨綠江,南至廣西北侖河口,綿延1.8萬公里的中國海岸線上,2018年1月,國家海洋局首次披露,有9600個陸源入海污染源(7500個人海排污口,余為人海河流、排澇口等)正向大海吐出污水,平均每2公里海岸線就有一個。而結合海洋督察發現,全國審批的入海排污口570余個,僅占入海排污口總數的8%。
福爾摩斯般的尋蹤
“問題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熟悉海洋環保的人都知道這句話。
追蹤海邊的污染源,往往得具備福爾摩斯一般的臨場觀察、分析、判斷的技巧,因為一些企業把偷排管道埋在地下。
大量設在海岸的排污口被劃進工廠廠區難以到達,在沒有道路標記的工業區和圍填海新造的海灘,手機導航軟件時常一片空白,能查看地面路況的衛星地圖也經常失靈。“想靠近海岸,得走魚塘旁、鹽灘邊的小路,有時路斷了車過不去,有時根本就是死胡同。”環保組織“天津綠領”的調查員張國兵說。
對監管部門來說,即使拿到規劃圖紙和數據資料,排查工作同樣舉步維艱。有些圖紙上的排污口位置已遷移或關閉,有些明管、暗管鋪設得很長,沒有任何標記也看不出到底來自哪家企業。
潮汐也會掩蓋排污口。有的排污口只有在低潮位時才能顯現,實地排查要根據潮汐時間來安排。
即使是在低潮位時,有的排污口也難觀測到。浙江一家從事環境檢測的公司副總工程師王顯海說:“有一次,我們看到海面下涌出氣泡,但原始資料中并無記錄。”根據經驗,王顯海他們判斷這個隱蔽的出水口仍深藏在海面之下,最后,他們對岸上可能的污染源逐一查看,才追查出一家水產養殖場的排污管道。
入海排污口大清查
國家海洋局在2017年對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開展了陸源人海污染排查,2018年1月結果公布,全國共排查出9600個污染源。
這已經是個不小的數字,但多位專業人士均表示,實際的陸源污染源恐怕還要更多——僅寧波市一地就排查出了1 131個人海排污口。在龐大的污染源底數中,更可怕的是,相當部分是監管的真空地帶,其中尤以養殖污染為重頭。在國家海洋局的通報中,有2900余個養殖排污口環保、漁業和海洋部門均未實施有效監管。
一位寧波市環保局工作人員介紹,他們排查的結果中,涉及養殖的人海碶閘有503個,占全市人海排污口總量的40%以上,且排放超標現象較為嚴重。“養殖池里魚、蝦的密度很大,投放的飼料吃不完,和糞便一起沉積在池塘底會惡化水質,就需要經常換水,進行底水排污處理。而這些發黑發臭的污水中往往還伴隨一些化學藥品成分,如未經處理直排入海,污染量也不小。”
已完成的六省海洋環保督查也對近海排污進行了嚴厲通報:福建省各類陸源入海排污源2678個,環保部門僅提供了68個入海排污口的情況;在遼寧省環保部門提供的211個人海排污口中,有68個未嚴格履行法定程序批準設置;廣西陸源人海污染源453個,依法經批準設置的29個,達標排放率僅為41.7%……
割據式管理是污染源失控的根源
誰能解決排污口問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志愿者楊振華打過市長熱線,找過省里的環保部門,也跟化工園區管委會的領導打過交道。很多投訴者都感受過“病急亂投醫”的無助。王顯海也感到,排查工作中很顯著的困難就是協調有關部門。
借調城市排污管道原始圖紙要找城管部門:有些排污口埋設在企業內部、涉外港口、保稅區內,需要反復協調;污染源由環保、市政還是海洋水利部門審批,相關手續是否合規,都是比技術性排查更難完成的調研工作。
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海洋學院教授王亞民告訴記者,工業及市政排污一般會集中到污水處理廠,經環保部門批準,處理達標后集中排海;而養殖類污染歸農業部門分管,排污問題尚未制定詳細的管理標準;排污河涉及水利部門。但從整體來看,岸上的排污口歸環保部管,海上排污工程則屬于海洋局。
多位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類似“海洋部門不上岸、環保部門不下海”的割據式管理,是造成大量陸源污染長期處于監管“真空狀態”的癥結所在。
此外,除了中央部門多頭監管帶來的尷尬外,“環保給GDP讓位”的老故事時有發生。
楊振華所在的灌云縣偏居蘇北,此前一直是全省的經濟“洼地”。灌云縣將“環境容量大”寫進招商口號,吸引到外地化工、高污染企業紛紛落戶此地。
借海洋之便,灌云縣在脫貧路上搭了“沖鋒快艇”,“寧可毒死、不可窮死”的口號一直在當地流傳。被中央環保督察組點名批評之后,當地的副市長、縣委書記、副書記等領導均被記過或黨內警告。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