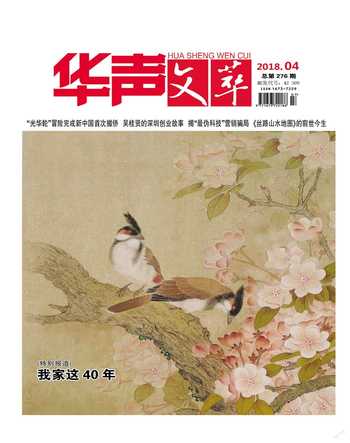為什么我喜歡的全是小說
孟非
小時候看過兩本表現(xiàn)革命英雄主義的書,對我影響很大,當(dāng)時就像有一團(tuán)火在我胸中燃燒,要燒出生命的價值。一本是《牛虻》,一本是《斯巴達(dá)克斯》。牛虻能忍人所不能忍的個性讓我很觸動,尤其是他回歸之后,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應(yīng)該具備的品質(zhì)。很多年后回想起來,我才知道它打動我的就是對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堅持,以及為了這個信念而表現(xiàn)出的堅韌不拔。
工作最初的一段時間,基本沒讀書,多掙一百塊錢比什么都強。那時候在印刷廠當(dāng)臨時工,生活渾渾噩噩,沒有什么信念支撐。就是有點不甘心,覺得自己和別人還有點不一樣。于是就去考學(xué)歷。上著班讀書很難,廠里就我一個人干這事。工友們下班除了打麻將,也沒什么娛樂,萬一打麻將輸了,下個月還活不活了?讀書又便宜又省錢,還能打發(fā)時間。
我看的書全是小說,功能性的、理論性、心理學(xué)之類的書籍,極少極少看。寫小說特別需要才華,看一遍小說,等于把人家的生活過了一遍。劉震云、莫言、馬爾克斯這些人很了不起,怎樣體驗他們的人生呢?就是閱讀他們的書。
我對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評價最高。這個寓言式的小說有點像中國版《百年孤獨》,很多人看前50頁是看不下去的,上部“出延津記”,下部“回延津記”,有點像《出埃及記》。整本書有100多個有名有姓的人物,那么多的線索,那么多故事,鋪墊了那么長,當(dāng)你看到后半部時,所有線索都連上了。我很驚訝,他寫作時腦子里得有多大的一盤棋啊?我看時默默地覺得,這本書體現(xiàn)了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最高的成就。
有些作品對后世的作家影響特別大。比如《百年孤獨》。你可以在很多中國作家的書里看到《百年孤獨》的影子,比如我喜歡的劉震云。另一個是《萬歷十五年》。當(dāng)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一套七本,就有黃仁宇的影子。我看完第一卷就知道,這哥兒們一定非常喜歡《萬歷十五年》。
有人說,看小說有什么用?它能解決什么問題?我很不贊同這樣的觀念,我們不能抱著解決問題的態(tài)度去閱讀,閱讀本身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如果我們把閱讀功能化或者功利化,那我建議你就別看了。
碰到什么問題,你應(yīng)該想辦法找人!比如說洗衣機壞了,與其看一本《如何修家電》,不如打電話讓修理工上門,給他200塊錢把洗衣機修好。也不用看什么《股票操作實例》,你應(yīng)該委托一個基金經(jīng)理,給他10%的傭金,讓他替你炒,炒不好就換一個人。這不就完了嗎?
(摘自《新周刊》)
京劇又叫“皮黃”的緣由
“皮黃”又作“皮簧”,是西皮和二黃(簧)的簡稱,它們是京劇的兩大主要聲腔,所以早年的京劇也被稱為“皮黃”或“皮簧”戲。《中國京劇史》中說:“京劇的前身是徽戲(微調(diào))、漢戲(楚調(diào))、昆曲、秦腔、京腔,并受到民間俗曲的影響。”特別是徽戲和漢戲的聲腔對京劇的形成影響最大。自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開始,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為名,先后有“三慶”“四喜”“春臺”“和春”等徽班來到北京演出,史稱“四大徽班”,先后到京的漢戲藝人多搭徽班演唱。二黃(簧)是徽戲的主要聲腔之一,而漢戲聲腔以西皮和漢戲二黃(簧)為主,它是皮、簧合奏的。隨著徽戲、漢戲進(jìn)京演出,使得西皮、二黃(簧)聲腔進(jìn)一步融合,迅速發(fā)展,形成豐富的旋律和完整的板式。多數(shù)人認(rèn)為,“二黃(簧)”之說來自地名,即湖北的黃岡、黃陂二縣,楊靜亭著《都門紀(jì)略》就是這種說法。其他說法還有很多,莫衷一是。至于“西皮”,初稱“襄陽調(diào)”,有來源于中國西部的音樂成分,而湖北人稱“唱”為“皮”,故名“西皮”。
(摘自《百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