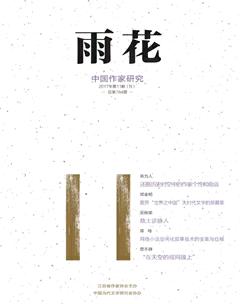木心文學(xué)觀念的考察
康建強(qiáng)
木心,一個(gè)被遺忘的作家,正逐漸走進(jìn)讀者和研究者的視野,不論是捧還是棒①,他的被接受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的一個(gè)文化現(xiàn)象。他的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藝術(shù)觀都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本文主要就木心的文學(xué)藝術(shù)觀進(jìn)行探討。
木心的《文學(xué)回憶錄》集中表述了他的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回憶錄》并不是他的關(guān)于文學(xué)理論和藝術(shù)理論的專(zhuān)著,而是陳丹青整理的木心講授世界文學(xué)史的課堂講義,由于課堂流動(dòng),聽(tīng)者亦沒(méi)有出勤考核,且不隸屬于任何教育系統(tǒng),故這份講義就極靈活而且充滿(mǎn)了木心先生的個(gè)性。木心在講述評(píng)論古今中外的文學(xué)家時(shí)或直接或婉轉(zhuǎn)地將他的文學(xué)觀念體現(xiàn)出來(lái)。本文以為木心最核心的文學(xué)觀可以用他在評(píng)價(jià)陶淵明時(shí)所用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來(lái)概括。
木心的這“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為什么值得拈出來(lái)探討呢?因?yàn)檫@一觀念絕不僅僅是他的文學(xué)觀,更是他的生命觀,更是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摯愛(ài)文學(xué)藝術(shù),渴望人格獨(dú)立,渴望在文學(xué)中伸張生命永恒意義的人的生命藝術(shù)觀。所以他的這文學(xué)觀就不再是那么十足理論味、單純藝術(shù)味。這文學(xué)觀承載了他和他身后一批人對(duì)生命、藝術(shù)、永恒等終極問(wèn)題的思考。因而他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就是一個(gè)沉甸甸的包含了頭腦、滲透著血液、流動(dòng)著氣息的試圖建立生命價(jià)值的命題。因此對(duì)木心“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這一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就絕不僅僅限于只是一種學(xué)術(shù)概念的探討,同時(shí)也不僅只是對(duì)一個(gè)閑居于象牙塔的藝術(shù)家的生命觀、藝術(shù)觀的個(gè)案考察,這一梳理和分析實(shí)在有助于我們?nèi)フJ(rèn)知上個(gè)世紀(jì)里的一批人的獨(dú)特的生命思考。
木心在《文學(xué)回憶錄》講解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中陶淵明的時(shí)候,情不自禁地興奮起來(lái)。他說(shuō):“陶詩(shī)的境界、意象,在現(xiàn)代人看來(lái),還是簡(jiǎn)單的,但陶詩(shī)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我衷心喜愛(ài)……他不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過(guò)的,還要走下去的,就是這樣的意象和境界。”②綜合全書(shū)看,木心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所鐘情者不多,但對(duì)屈原、嵇康、陶淵明、杜甫、曹雪芹等幾位作家是非常推崇的,他對(duì)陶淵明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的贊賞,實(shí)則也是他自己藝術(shù)觀念的表達(dá),而這也非常符合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家“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傳統(tǒng)。當(dāng)然考察木心的其他各類(lèi)作品,他似乎并沒(méi)有非常刻意地去把這一觀念衍伸擴(kuò)充成為一個(gè)文學(xué)的理論,因?yàn)樗遣皇麦w系的一個(gè)藝術(shù)家。③所以本文在這里對(duì)他的這一觀點(diǎn)進(jìn)行分析時(shí)也難免支離,如果還有所謂的內(nèi)在邏輯的話,也是從他的諸多的雜語(yǔ)感想中梳理發(fā)掘出來(lái)的,木心并沒(méi)有這樣的建構(gòu)理論體系的野心。
總覽全部《文學(xué)回憶錄》,可以依稀辨別出他的“文學(xué)本體性高妙”論的一些內(nèi)涵,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部分:其一,文學(xué)的尊嚴(yán);其二,藝術(shù)與生命的合一性;其三,文學(xué)的使命④。下面分述之。
一、文學(xué)的尊嚴(yán)
在《文學(xué)回憶錄》中,木心常常會(huì)在講完某個(gè)具體作家或者作品后發(fā)表自己的非常個(gè)性的即時(shí)評(píng)論,在這些評(píng)論中有一點(diǎn)很集中,就是木心在爭(zhēng)藝術(shù)的尊嚴(yán),文學(xué)的尊嚴(yán)和藝術(shù)家的尊嚴(yán)。木心所爭(zhēng)藝術(shù)的尊嚴(yán)乃是有針對(duì)性的,其針對(duì)者有三,一是宗教,二是政治(或曰強(qiáng)權(quán)),三是各種物質(zhì)主義。他以為文學(xué)的尊嚴(yán)在于能從這三者中超越出來(lái),只有獲得了這種獨(dú)立,文學(xué)才能具備永恒的價(jià)值。
文學(xué)藝術(shù)和宗教的關(guān)系自來(lái)就很復(fù)雜,很難理得清,從現(xiàn)在的認(rèn)知論看,起初他們是合在一起的。而且起初時(shí),藝術(shù)是從屬于宗教的。藝術(shù)家被看做是俳優(yōu),而宗教家則被視為天意的解釋者。后來(lái)才分了家。木心爭(zhēng)文學(xué)的獨(dú)立與尊嚴(yán)夠徹底,他直接從釋迦摩尼和耶穌那里爭(zhēng)。這樣就使文學(xué)藝術(shù)從一開(kāi)始就有了與宗教同等的角色定位。他說(shuō):“耶穌是天才的詩(shī)人,他的襟懷情懷不是希臘文、希伯來(lái)文所能限制的,他的布道充滿(mǎn)靈感,比喻巧妙,象征的意義似淺實(shí)深,他的人格力量充沛到萬(wàn)世放射不盡。所以他是眾人的基督,更是文學(xué)的基督。”在這里他非要把耶穌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而且是最偉大的詩(shī)人來(lái)看,他說(shuō)耶穌“是眾人的基督,更是文學(xué)的基督”,那么什么是文學(xué)的基督呢?就是木心以為“《新約》彌漫著耶穌的偉大人格。他的氣質(zhì)、他的性情、他博大的襟懷、他強(qiáng)烈的熱情,感動(dòng)了全世界”,木心以為這種心腸是能拯救文學(xué)的。文學(xué)失去了這種善、這種愛(ài),將只能墮落。木心把基督教神學(xué)中耶穌的神人二性論進(jìn)行分解,只留下了耶穌的人性,因此他自覺(jué)地稱(chēng)“我的文學(xué)引導(dǎo)之路,就是耶穌”。但他卻并沒(méi)有成為一個(gè)基督徒。他站在理性的角度得出結(jié)論“宗教總是從情理開(kāi)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虛作假”,又說(shuō)“宗教是要把人類(lèi)變成天上的神的家畜,人再也回不到原來(lái)野生的狀態(tài)。家畜成為人類(lèi)的犧牲品,人類(lèi)成為自己的犧牲品”。他教導(dǎo)學(xué)生說(shuō):“希望大家重視宗教藝術(shù),要把含在宗教里的藝術(shù),含在藝術(shù)里的宗教,細(xì)細(xì)分開(kāi)來(lái)。”木心看到了宗教形式對(duì)人類(lèi)的一些惡意,因而他明確地說(shuō)要把藝術(shù)家與宗教家分開(kāi)。他在否定宗教之后,忽然又提出疑問(wèn),“如果不憑借宗教,藝術(shù)能達(dá)到飽和崇高的境界嗎?藝術(shù)這么偉大,為什么要依附宗教?宗教衰亡了,藝術(shù)自由了,獨(dú)立了,藝術(shù)是否更偉大?”從這些疑問(wèn)中可以看出來(lái),木心以為文學(xué)應(yīng)當(dāng)從宗教中獨(dú)立出來(lái),但是文學(xué)的心腸和宗教的心腸卻又是相通的,不能分割的。文學(xué)作品中一定要有的就是像耶穌、釋迦摩尼一樣的心腸,有了這種心腸,才能有智慧,才能有格局,才能有恒久的價(jià)值。
木心之爭(zhēng)文學(xué)的尊嚴(yán),本體性的高妙,第二是針對(duì)政治對(duì)文學(xué)的干預(yù)。
過(guò)去,再偉大的藝術(shù)家都自卑,直到貝多芬,才自覺(jué)地說(shuō)“藝術(shù)家高于帝王”,這是木心借別的藝術(shù)家來(lái)表達(dá)自己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尊嚴(yán)的見(jiàn)解。文學(xué)藝術(shù)在獨(dú)立于宗教之外的同時(shí),更要與政治相對(duì)疏遠(yuǎn)些,尤其不能被強(qiáng)權(quán)所奴役。在這一點(diǎn)上,木心是自覺(jué)地繼承嵇康、陶淵明的精神的。嵇康和陶淵明都是自覺(jué)地與當(dāng)時(shí)的政治保持一段距離。只有保持一段距離,文學(xué)才能不至于被利用、被奴役。而這種藝術(shù)獨(dú)立的自覺(jué),其實(shí)和清末民初中國(guó)知識(shí)界追求學(xué)術(shù)獨(dú)立的精神又是呼應(yīng)的。梁?jiǎn)⒊凇肚宕鷮W(xué)術(shù)概論》中倡導(dǎo)的學(xué)術(shù)獨(dú)立,學(xué)術(shù)的超功利性,陳寅恪在撰寫(xiě)《王國(guó)維先生紀(jì)念碑銘》時(shí)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獨(dú)立之人格”,這些都可以看作是木心這個(gè)觀念的先驅(qū)。在講日本明治維新時(shí)期的文學(xué)時(shí),木心有感而發(fā)說(shuō)到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文學(xué)“三是革命和愚民。文學(xué)藝術(shù)在極權(quán)下成了丫頭,一邊歌功頌德,一邊長(zhǎng)期愚民”。在回顧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文學(xué)界的“為藝術(shù)”“為人生”之爭(zhēng)時(shí),他說(shuō)“中國(guó)的所謂反‘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主‘為人生而藝術(shù),是既沒(méi)有‘為藝術(shù),也沒(méi)有‘為人生——是政治掛帥,為一個(gè)人,為獨(dú)裁”。不難看出,木心的爭(zhēng)文學(xué)獨(dú)立與梁、陳等人爭(zhēng)學(xué)術(shù)獨(dú)立在精神上是一致的。endprint
木心之爭(zhēng)文學(xué)尊嚴(yán),還有一層用意即是要用藝術(shù)來(lái)與功利主義、物質(zhì)主義抗衡。藝術(shù)家要有一種精神即被藝術(shù)所占有,在藝術(shù)世界中一個(gè)人能找到價(jià)值的依歸,找到自處于宇宙、歷史、社會(huì)的根基。藝術(shù)家不可被物質(zhì)功利所奴役,否則藝術(shù)家生命里的藝術(shù)精神就會(huì)消失。他用福樓拜的話表達(dá):我甘愿為藝術(shù)占有。當(dāng)代文明倡導(dǎo)的功利主義物質(zhì)主義對(duì)藝術(shù)是極大的戕害,他在講葉慈的思想時(shí),將自己對(duì)當(dāng)代文明的看法表露出來(lái),“我只是想說(shuō),商業(yè)社會(huì),不是文化,也不是文明。我們?cè)诿绹?guó),美國(guó)治國(guó)大計(jì),是實(shí)用主義理論,最有名杜威,還有皮爾士、詹姆斯——這種哲學(xué)是沒(méi)有遠(yuǎn)見(jiàn)的庸人哲學(xué)”“所以在痛恨商品文化上,我和葉慈一致”代表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的實(shí)用主義理論使藝術(shù)失去獨(dú)立性,使藝術(shù)在脫離宗教,擺脫政治強(qiáng)權(quán)之后,又淪為物質(zhì)主義的附庸,所以藝術(shù)家為了藝術(shù)的獨(dú)立需要作出犧牲,需要主動(dòng)地與這個(gè)太過(guò)功利的世界疏遠(yuǎn),來(lái)做一個(gè)夢(mèng),“藝術(shù)本來(lái)也只是一個(gè)夢(mèng),不過(guò)比權(quán)勢(shì)的夢(mèng)、財(cái)富的夢(mèng)、情欲的夢(mèng),更美一些,更持久些,藝術(shù),是個(gè)最好的夢(mèng)”。
為了獲得文學(xué)藝術(shù)的獨(dú)立與尊嚴(yán),文學(xué)家需要與世俗世界保持適當(dāng)?shù)木嚯x,即一定程度的疏離,甚至是文學(xué)家的逃離。有距離才能遠(yuǎn)遠(yuǎn)地觀,而遠(yuǎn)觀是客觀的一個(gè)很重要的條件。但遠(yuǎn)觀又不意味著不理解,不投入。而是既可以入乎其中,又可以出乎其外。他舉陶淵明為例,他說(shuō)陶淵明是“雙重的隱士,實(shí)際生活是退歸田園,隱掉了……陶淵明不在中國(guó)文學(xué)的塔內(nèi),他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塔外人”。這種隱士的態(tài)度實(shí)際上就是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主流的生活方式、價(jià)值觀念的疏遠(yuǎn),甚至是與當(dāng)時(shí)主導(dǎo)的文學(xué)風(fēng)格的疏遠(yuǎn),正是因?yàn)樘諟Y明的這種主動(dòng)疏離,成就了他文學(xué)的獨(dú)立與尊嚴(yán)。他講莎士比亞時(shí)說(shuō)“人間百態(tài),莎士比亞退得很開(kāi)。退得最遠(yuǎn)最開(kāi)的是上帝。莎士比亞,是僅次于上帝的人”。他又用自己的經(jīng)歷來(lái)說(shuō)明這種疏離的重要性。在解放初,木心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執(zhí)教,待遇相當(dāng)不錯(cuò),但是為了讓自己與世界保持距離,他“雇人挑了書(shū)、電唱機(jī)、畫(huà)畫(huà)工具,走上莫干山”,主動(dòng)讓自己過(guò)凄清、孤獨(dú)、單調(diào)的生活。木心自道說(shuō)這是遵循了他的老師福樓拜的教導(dǎo)。這里的文學(xué)家與現(xiàn)實(shí)保持距離,不是說(shuō)讓作家不關(guān)心社會(huì),而是要求作家不能與時(shí)俯仰,隨波逐流,曲學(xué)阿世,而能保持自己獨(dú)立的思考和視角,來(lái)審視他所處的時(shí)代,藝術(shù)家應(yīng)該始終保持這樣一種既關(guān)注又不陷入的態(tài)度。⑤
總之,木心以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始終在為文學(xué)藝術(shù)爭(zhēng)地位,爭(zhēng)尊嚴(yán),之所以爭(zhēng),是因?yàn)橐呀?jīng)失去。因?yàn)樵谀拘乃畹臅r(shí)代,藝術(shù)已經(jīng)或被宗教、被強(qiáng)權(quán)、被物質(zhì)主義所俘虜,所以他要為藝術(shù)爭(zhēng)一個(gè)體面的尊嚴(yán)。“本來(lái)站不直,靠藝術(shù)才站站好,怎能跌倒?”
二、藝術(shù)與生命的合一性
木心最為推崇的文學(xué)藝術(shù)都是藝術(shù)形式與生命深度完美融合的典范。在中國(guó)文學(xué)中他所推崇的屈原、司馬遷、嵇康、陶淵明、杜甫、曹雪芹等,在外國(guó)文學(xué)他最為推崇的《圣經(jīng)》、莎士比亞、尼采、紀(jì)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他認(rèn)為這些偉大的作家都做到了文學(xué)藝術(shù)與生命的合一。在這種合一論里,木心既尊重了文學(xué)特有的藝術(shù)形式之美,又深信追求形式之美的藝術(shù)家必須與他全部生命的合一才能達(dá)到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
木心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特有的形式美報(bào)以巨大的尊重。他看重杜甫晚年律詩(shī)的謹(jǐn)嚴(yán)⑥,他喜歡李商隱詩(shī)歌中的朦朧美,他欣賞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他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質(zhì)樸的小說(shuō)語(yǔ)言風(fēng)格,他對(duì)普希金的詩(shī)歌的簡(jiǎn)潔大加推崇。在諸多的屬于形式美的要素中,木心尤其看重的是簡(jiǎn)約和樸素。木心以《圣經(jīng)》為例,以陶淵明為例,一再地說(shuō)明“文學(xué)本體性高妙”的一個(gè)特質(zhì)就是形式的簡(jiǎn)約與語(yǔ)言的樸素。而形式的簡(jiǎn)約則源于內(nèi)心的真誠(chéng)。“我少年時(shí)一觸及《圣經(jīng)》,就被這種靈感和氣氛吸引住。文字的簡(jiǎn)練來(lái)自?xún)?nèi)心的真誠(chéng)。”他在推崇陶淵明時(shí)說(shuō)“讀陶詩(shī),是享受,寫(xiě)得真樸素,真精致。”樸素的語(yǔ)言是豐富心靈的最好外衣。
當(dāng)然木心沒(méi)有陷于藝術(shù)形式至上的新批評(píng)派的文學(xué)本體論中,在整個(gè)《文學(xué)回憶錄》中木心推崇的偉大作家都做到了藝術(shù)與生命的合一。在這種合一中,除了訴諸于文字的形式,他更多強(qiáng)調(diào)的是隱藏于文字之下的作家豐富的生命。“我認(rèn)為,魏晉風(fēng)度,就在那些高士藝術(shù)與人生的一元論。”在論述莎士比亞時(shí),他更闡釋這種觀點(diǎn),他說(shuō)“藝術(shù)品是他公開(kāi)的一部分,另有更大的部分,他不公開(kāi)。不公開(kāi)的部分與公開(kāi)的部分,比例愈大,作品的深度愈大。我愛(ài)藝術(shù),愛(ài)藝術(shù)家,是因?yàn)樗囆g(shù)見(jiàn)一二,而藝術(shù)家是見(jiàn)七八。”“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讓人看出還有許多東西,這就是藝術(shù)家的深度”。可見(jiàn)的藝術(shù)品是藝術(shù)家豐富生命的部分展示,當(dāng)一個(gè)藝術(shù)家具備了生命的深度和廣度時(shí),他的作品才會(huì)耐人尋味。而連接藝術(shù)家生命與作品的紐帶則是真誠(chéng)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精神。在一次接受訪問(wèn)時(shí),采訪者問(wèn)“您認(rèn)為作為一個(gè)作家最重要的條件是什么”,他回答“誠(chéng)吧”。當(dāng)然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見(jiàn)解,這是古今中外偉大藝術(shù)家都認(rèn)可的最重要的素質(zhì)。比如他推崇的陶淵明,蘇軾就說(shuō)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mén)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⑦。蘇軾這里推崇陶淵明的“真”,和木心所言的作家的“誠(chéng)”,不謀而合地道出了作品與作家真正合一的途徑。
木心并沒(méi)有止步于此,他對(duì)藝術(shù)家心靈的要求更高更具體。“文學(xué)家,固然要文字高超,最后還得靠‘神智器識(shí)統(tǒng)攝技巧。神智器識(shí),可以姑且解作‘世界觀。世界觀,意味著上有宇宙觀,下有人生觀的這么一種‘觀。”“寫(xiě)長(zhǎng)篇,要靠強(qiáng)大的人格力量,極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斯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在哲學(xué)、史學(xué)、文學(xué)上的修養(yǎng),深刻啦!”也就是說(shuō)他看到了偉大的作品的背后是一個(gè)作家完整的世界,包括他的心腸、思想、情感等等全部的內(nèi)涵。在諸要素中,心腸又是占最重要地位的。一個(gè)作家要有一顆熱愛(ài)世界,熱愛(ài)人間的心。如果失去了這個(gè)熱心腸,那么作品就會(huì)淡然無(wú)味,或者顯得矯情。以木心認(rèn)為的“天才的詩(shī)人”“文學(xué)的基督”耶穌為例,他講耶穌時(shí)說(shuō)“他已超越哲學(xué)、宗教,就是一片愛(ài),一片感嘆”,又講“知是哲學(xué),愛(ài)是藝術(shù)”。在講到另一位他非常推崇的文學(xué)家時(shí),他說(shuō)“在世界可知的歷史中,最打動(dòng)我的兩顆心,一是耶穌,二是陀氏”。若要作品偉大而且有味,那么作家必須有這種愛(ài)心,這種慈悲心,這種憐憫心,有了這種自覺(jué)的對(duì)人類(lèi)生存苦難的理解的同情,作家的作品才是能夠與永恒結(jié)盟的作品。endprint
在木心看來(lái),文學(xué)家要達(dá)到“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就必須將形式的簡(jiǎn)約樸素與愛(ài)的心腸真誠(chéng)的結(jié)合,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有味的作品,才是藝術(shù)與生命合一的有尊嚴(yán)的作品。
三、文學(xué)的使命
因著文學(xué)藝術(shù)有了獨(dú)立的地位,有了當(dāng)有的尊嚴(yán),它才能擔(dān)得起它的使命。所以這里的使命與那些匍匐在宗教偶像面前的,屈膝在政治強(qiáng)權(quán)面前的,搔首弄姿于物質(zhì)主義面前的藝術(shù)無(wú)涉。作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木心對(duì)藝術(shù)的使命非常自覺(jué),他對(duì)藝術(shù)家的尊嚴(yán)也非常自信。他認(rèn)為“藝術(shù)可以拯救人類(lèi)”。他認(rèn)為藝術(shù)家是“僅次于上帝的人”。文學(xué)家可以“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救出自己”。基督教認(rèn)為神就是愛(ài),在愛(ài)里沒(méi)有恐懼,木心用藝術(shù)的形式取代基督教的形式,用藝術(shù)家的心取代耶穌的心,而其內(nèi)核卻是同一的。即木心欲用文學(xué)藝術(shù)中蘊(yùn)藏著的愛(ài)來(lái)抵抗虛無(wú)的世界、冷漠的物質(zhì)文明。在木心看來(lái)藝術(shù)起到了宗教想要承擔(dān)的使命。世界各個(gè)民族的宗教無(wú)一不是欲將人救拔于苦海之外,但它們幾乎都做不到。如前文所引“宗教總是從情理開(kāi)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虛作假”,所以他對(duì)宗教失望,他一再說(shuō)只有藝術(shù)才能拯救人類(lèi)。但他有時(shí)又不會(huì)這么堅(jiān)定,他又說(shuō)藝術(shù)本來(lái)也只是一個(gè)夢(mèng),是個(gè)最好的夢(mèng),在這兩種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木心認(rèn)識(shí)論中的矛盾。一方面他認(rèn)為作為愛(ài)的代表,藝術(shù)可以拯救人類(lèi),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文學(xué)藝術(shù)的脆弱,文學(xué)藝術(shù)常常成為宗教、政治、商業(yè)文明的附庸,常常喪失自己的藝術(shù)品格,藝術(shù)于是就成了藝術(shù)家的夢(mèng),而夢(mèng)是虛幻的,它也就不在那么有力地成為拯救的力量。文學(xué)的使命就這樣搖擺著,木心的生命的也就這樣搖擺著。
四、對(duì)木心文學(xué)觀念產(chǎn)生原因探討
木心沒(méi)有像很多中國(guó)傳統(tǒng)知識(shí)分子一樣走向佛教或者棲身于玄學(xué),也沒(méi)有像現(xiàn)代的絕大多數(shù)知識(shí)分子在唯物主義中安然,他一直在尋找讓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他把藝術(shù)宗教化,認(rèn)為藝術(shù)可以拯救人類(lèi),認(rèn)為個(gè)體的人可以通過(guò)藝術(shù)達(dá)于永恒。這種文藝觀一方面來(lái)源于他認(rèn)識(shí)論的困境,一方面來(lái)源于時(shí)代的影響。
首先看木心的認(rèn)識(shí)論。木心不是一個(gè)只會(huì)用藝術(shù)語(yǔ)言思考表達(dá)生命的人,他認(rèn)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觀和他整個(gè)的宇宙觀、世界觀和人生觀是相聯(lián)系的。于是他拓寬自己的視野,他豐富自己的認(rèn)識(shí),他試圖用新的科學(xué)知識(shí)來(lái)理解人類(lèi)的物理處境。他自言:“我好藝術(shù),曾輕視科學(xué),但后來(lái)想到現(xiàn)代文明、文化,科學(xué)、藝術(shù)各為一翅,不能缺一,所以花了十多年功夫補(bǔ)天文、物理科學(xué)等事。”但是這些現(xiàn)代的科學(xué)知識(shí)并沒(méi)有給他提供更加確定的力量,反而讓他意識(shí)到“科學(xué)知識(shí)足夠埋葬神學(xué),接下來(lái)還要結(jié)束哲學(xué)”,最終會(huì)導(dǎo)致“無(wú)真理論”。不但如此,現(xiàn)代科學(xué)不斷揭示人類(lèi)存在的偶然性,于是容易引起人的悲觀,木心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他說(shuō)“世界這只大船根本沒(méi)有船長(zhǎng),有人毀壞,有人修補(bǔ),但不問(wèn)這船究竟航向哪里。可以預(yù)見(jiàn),這船會(huì)爆炸,會(huì)沉沒(méi),沉沒(méi)在宇宙里”,“我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生命在宇宙中是偶然的,是反宇宙的。其傾向是毀滅自己,不是進(jìn)化,而是惡化。所以,康德說(shuō):對(duì)于宇宙的沒(méi)有目的,感到恐怖”。這些觀點(diǎn)和思想都一再表明木心對(duì)人類(lèi)未來(lái)的絕望。面對(duì)浩瀚無(wú)垠的宇宙,面對(duì)生命可能只是一種偶然的理論,面對(duì)真理可能只是暫時(shí)的托辭的困境,很多現(xiàn)代人逃到宗教中去尋找安慰。木心也試圖找到足以讓他信賴(lài)的“神”,他也曾被自然界的奇妙和自覺(jué)所震撼,認(rèn)為可能有一個(gè)創(chuàng)造者存在,但是科學(xué)的觀念使他至終無(wú)法進(jìn)入宗教的神學(xué)中,使他只能成為一個(gè)“很不好意思的無(wú)神論者”。但正是這種悲觀的認(rèn)識(shí)論才激發(fā)木心思考人該用什么來(lái)抵擋這無(wú)邊的失望甚至是絕望,他思考得出的一個(gè)出路就是靠藝術(shù)家、藝術(shù)來(lái)抗?fàn)帯K囆g(shù)家不能躲在宗教提供的避難所里,否則就失去了藝術(shù)家當(dāng)有的深度,“藝術(shù)家純粹是人間的,不是天堂地獄的,天堂地獄,沒(méi)有深度……要?jiǎng)澐郑郎洗笏囆g(shù)家都是在絕望中求永生”。也就是說(shuō)藝術(shù)家是認(rèn)識(shí)到人生荒誕、生命虛無(wú),但絕不妥協(xié),絕不躲避,而要在絕望中抗?fàn)幍娜耍@里,藝術(shù)家代表著人類(lèi)尋找生的根據(jù)、生的意義。其實(shí)木心生命中的這種抗?fàn)帲瑥那詠?lái)就在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中延續(xù)著,到了近代則是由陳寅恪、王國(guó)維、梁?jiǎn)⒊Ⅳ斞浮⑼粼鳌㈠X(qián)鐘書(shū)等人繼續(xù)著⑧。“到了說(shuō)沒(méi)有真理,人,真正站起來(lái)了”,當(dāng)人類(lèi)不再需要“神”“真理”作避難所時(shí),人類(lèi)怎么站起來(lái)呢?或者靠麻木,或者靠盲目,或者靠冷靜的抗?fàn)帲拘倪x擇了靠藝術(shù)來(lái)站立。
其次我們從木心所處的時(shí)代來(lái)看他的這種文學(xué)觀念形成的原因。木心沒(méi)有像同時(shí)代的很多知識(shí)分子那樣及早地選擇了自己的陣營(yíng)(不論是政治的,還是學(xué)術(shù)的,還是藝術(shù)的)。他一邊成長(zhǎng)一邊探索,青少年時(shí)接受了來(lái)自家庭的中西結(jié)合的教育,后來(lái)又經(jīng)歷了新中國(guó)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與文化運(yùn)動(dòng),文革后又選擇移居美國(guó),在生命的晚年(2006年)才又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烏鎮(zhèn)。這樣的經(jīng)歷,正印證了他自己在《文學(xué)回憶錄》中所講的藝術(shù)家當(dāng)走一條主動(dòng)疏遠(yuǎn),甚至是逃亡的路。時(shí)代的潮流沖擊著他,但是他卻倔強(qiáng)地不被潮流沖走,可以說(shuō)時(shí)代是在反作用著他。他在時(shí)代動(dòng)亂時(shí),用藝術(shù)來(lái)支撐起生命的信仰,在美國(guó)紐約時(shí),同樣用藝術(shù)來(lái)對(duì)抗著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對(duì)藝術(shù)的瓦解。正是在這種與時(shí)代的拒斥過(guò)程中,他的藝術(shù)觀才越發(fā)堅(jiān)定起來(lái)。因?yàn)樗窟@“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來(lái)拯救自己,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藝術(shù)的自救。
五、結(jié)語(yǔ)
木心的同鄉(xiāng)豐子愷曾在“我與弘一法師”一文中寫(xiě)到:“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zhì)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zhì)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xué)術(shù)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gè)三層樓……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qiáng),腳力很大,對(duì)二層樓還不滿(mǎn)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⑨木心先生也是要從第二層樓上到第三層樓的人,只是他通過(guò)他的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的藝術(shù)觀試圖合并第二第三層樓,如前文所引證,他不愿成為宗教徒,他認(rèn)為藝術(shù)誠(chéng)然可以承擔(dān)宗教的使命,藝術(shù)可以拯救人類(lèi),文學(xué)家可以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救出自己,因此不必舍筏登岸,在筏上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尊嚴(yán)與滿(mǎn)足又何必登岸呢?由此看來(lái)木心的文學(xué)藝術(shù)觀絕不只是他對(duì)藝術(shù)的理解,更是他對(duì)生命如何自處于世界宇宙的思考總結(jié)。endprint
注釋?zhuān)?/p>
①在陳丹青力薦木心的作品,尤其是《文學(xué)回憶錄》后,很多讀者和研究者都給予木心非常高的評(píng)價(jià)。如《中華讀書(shū)報(bào)》文化周刊在木心的《文學(xué)回憶錄》出版(2013)不久后,就刊登馬宇輝的《文學(xué)史里看木心》(2013年5月15日),對(duì)木心在此書(shū)中體現(xiàn)的學(xué)識(shí)給予很高評(píng)價(jià)。陳丹青也在《文學(xué)報(bào)》2013年4月18日再次發(fā)文《時(shí)代的封藏——木心和他的時(shí)代》來(lái)回應(yīng)廣大讀者對(duì)木心先生的好評(píng)。與此同時(shí),也有一些學(xué)者持不同態(tài)度,認(rèn)為木心是被高估的文學(xué)大師。如《羊城晚報(bào)》2013年3月11日的一篇專(zhuān)訪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張檸的文章,就是認(rèn)為現(xiàn)在對(duì)木心的評(píng)價(jià)過(guò)高,文章這樣說(shuō)“他的隨想有很多對(duì)先賢哲人觀點(diǎn)的轉(zhuǎn)述和零星點(diǎn)評(píng),尼采的轉(zhuǎn)一點(diǎn),蒙田的轉(zhuǎn)一點(diǎn),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像是生命感悟的‘串燒,名人觀點(diǎn)的‘串燒。這種串燒再加上他比較清晰干凈的文字,讀者很快就能理解和接受。因此他有可讀性,有市場(chǎng),但這不代表他有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木心的作品不能滿(mǎn)足對(duì)文學(xué)閱讀要求稍高的讀者。”
②木心講述,陳丹青整理:《文學(xué)回憶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240頁(yè)。
③木心在《文學(xué)回憶錄》及其他評(píng)論性的創(chuàng)作中不止一次地重申他不喜歡體系,“從事體系就是不誠(chéng)懇”,他非常贊同尼采的這一說(shuō)法。
④木心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與新批評(píng)派的“文學(xué)本體論”顯然不是一回事,木心這里借用了“本體”這一哲學(xué)概念,但他的“文學(xué)本體性的高妙”和蘭色姆在《詩(shī)歌:本體論札記》《新批評(píng)》等文中的文學(xué)本體論概念絕沒(méi)有繼承性。
⑤木心在《文學(xué)回憶錄》中不斷地強(qiáng)調(diào)作家與他所處的時(shí)代,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都要保持一段距離。又如他在評(píng)價(jià)他所欣賞的普希金時(shí)說(shuō):現(xiàn)實(shí)的歸現(xiàn)實(shí),藝術(shù)的歸藝術(shù)。藝術(shù)不能跟現(xiàn)實(shí)走,藝術(shù)也不可能領(lǐng)著現(xiàn)實(shí)走。
⑥“讀杜詩(shī),要全面,不能單看他憂時(shí)、懷君、記事、刺史那幾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義的很多面。”《文學(xué)回憶錄》第70頁(yè)。
⑦《蘇軾文集》卷六十八,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6年,第2148頁(yè)。
⑧可以參閱解志熙《生的執(zhí)著》中對(duì)魯迅、錢(qián)鐘書(shū)和汪曾祺的生命探討。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⑨豐子愷:《緣緣堂隨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頁(yè)。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xué)院文學(xué)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