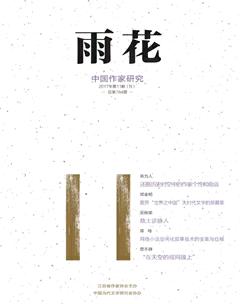還原歷史時(shí)空中的作家個性和命運(yùn)
已經(jīng)開過了難以數(shù)計(jì)的關(guān)于趙樹理的研討會。
為什么要一次次地花費(fèi)人力物力去召開呢?如果就是炒餿飯舊調(diào)重彈人云亦云老生常談吃別人嚼過的饃,那樣有什么必要和意義呢!
我們說一個時(shí)代標(biāo)志性的作家,必然與他所處的時(shí)代有著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與交結(jié),這是一種盤根錯節(jié)的聯(lián)系。正是因?yàn)檫@種復(fù)雜化的關(guān)系,使得后人能夠常讀常新,不斷從他身上發(fā)現(xiàn)作家個性與命運(yùn)的時(shí)代根源,社會原因,以及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局限。當(dāng)然,這不是配合當(dāng)下政治形勢的“與時(shí)俱進(jìn)”,而是把一個作家還原到他生存的特定歷史時(shí)空中,做出更加符合人物真實(shí)面目的界定。
2011年8月,廣東人民出版社作為“新史學(xué)叢書”中的一家,推出我撰寫的趙樹理傳記。動筆之始,意在筆先,我想:僅自己目力所及,已經(jīng)看到過十幾部趙樹理的傳記,還需要我畫蛇添足抑或狗尾續(xù)貂地再來寫一部趙樹理的傳記嗎?
我把趙樹理的傳記命名為《插錯“搭子”的一張牌》(趙樹理自己的命名,由此可見趙樹理對自己文學(xué)史上的定位是心存迷惘的),因此而引出我的副標(biāo)題——“重新解讀趙樹理”。
書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壇的關(guān)注和反響。廈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謝泳評價(jià)說:“趙樹理研究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中是相對成熟的,但本書在材料的搜集和事實(shí)的敘述方面還是多有新意,特別是作者與研究對象可能涉及的歷史比較熟悉,所以在分析和判斷方面較以往的研究更有啟發(fā)。另外本書吸收了近三十年來趙樹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自己的新觀點(diǎn),是近年來趙樹理研究的一個重要收獲。”趙樹理的兒子趙二湖在看過本書后說:“出過很多種趙樹理的評傳了,因此有了很多個面目各異的趙樹理。我不是專家,無從評論這些專著的好壞,作為兒子我只能評判像與不像。感謝陳為人先生寫了這么一本好書,還原了一個我熟悉的父親形象。”
錢理群先生在《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最讓我感到驚心動魄的,是本書《尾聲》所講述的趙樹理的當(dāng)下命運(yùn):他的形象“與時(shí)俱進(jìn)”,卻“面目全非”;他被安置在殿堂、廣場,以至熒幕,供人瞻仰;“毫不相干,強(qiáng)加給他的塑像”竟有八處之多,他的兒子也只能自嘲而無奈地說:“人家說他是我爹”。——在這樣的氛圍下,被呼喚而出的“后趙樹理寫作”,會是什么模樣,實(shí)在令人擔(dān)憂……而在我看來,提供這樣一個模糊的,難以作出簡單、明確判斷的趙樹理,而且引發(fā)我們許多想不清楚的思考:關(guān)于趙樹理,關(guān)于毛澤東,中國共產(chǎn)黨,關(guān)于中國的知識分子,農(nóng)民,關(guān)于趙樹理生活的、以及今天我們生活的時(shí)代,國家,民族……最后所有這些思考,都會歸于對歷史,對人的命運(yùn)、存在的追問,卻又沒有結(jié)論:這正是本書的真正價(jià)值與貢獻(xiàn)。
錢理群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寫道:“陳為人先生:前一段一直在趕寫一篇文章,這兩天才開始拜讀大作,確實(shí)受到了震動,也引發(fā)了許多思考,但一時(shí)無法理清楚,只能趕寫出這篇《讀后》……我原來有一個寫‘1949年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大的寫作計(jì)劃,我趕寫的文章,就是寫胡風(fēng)與舒蕪的(還沒有寫完),趙樹理也是我想寫的。讀了大作,更激發(fā)了我寫作的沖動,許多方面,大作已經(jīng)寫得很好了,我再要寫,可能就是《讀后》里提到的趙樹理引發(fā)的思考……”
2014年10月,我正在上海陪伴已經(jīng)九十三歲高齡的父母,錢理群先生給我發(fā)來一封電子郵件:“我寫了關(guān)于趙樹理的七萬多言的文章,從大作中多有吸取,特致謝意,也很想聽聽你的意見。”于是我得以先睹為快,看到了錢理群先生關(guān)于趙樹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趙樹理身份的三重性與曖昧性——趙樹理建國后的處境,心境與命運(yùn)》。錢理群先生在文章中寫道:
其實(shí),這也是我自己的,包括本書(《歲月滄桑:1949——1976知識分子精神史》)寫作的追求:寫出一個又一個的“難以作出簡單、明確判斷”的大時(shí)代里的個體生命史,以激發(fā)“對歷史,對人的命運(yùn)、存在的追問,卻又沒有結(jié)論……我在1998年即十六年前第一次研究趙樹理時(shí),就注意到了他的“雙重身份”:“趙樹理把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追求歸結(jié)為‘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正是表明了他的雙重身份、雙重立場。一方面,他是中國革命者,中國共產(chǎn)黨員,要自覺地維護(hù)黨的利益,他寫的作品必須‘在政治上起(到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農(nóng)民的兒子,要自覺地代表和維護(hù)農(nóng)民的利益,他的創(chuàng)作必須滿足農(nóng)民的要求,‘老百姓喜歡看。”正確地理解趙樹理的這兩重性是準(zhǔn)確地把握趙樹理及其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
現(xiàn)在有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趙樹理的學(xué)者,都刻意指出趙樹理與其他“山藥蛋派”的不同,其實(shí),在配合黨的中心工作,自覺做黨的宣傳員這一點(diǎn)上,他們都走在同一條《講話》指引的“金光大道”上。
馬烽在某次創(chuàng)作談中,關(guān)于一個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現(xiàn)實(shí)中曾發(fā)生過的真實(shí)事,就可以不加選擇地寫時(shí),說過這樣一番話:“有的題材要自覺地不去寫,因?yàn)閷懗鰜頉]有好處,沒有用。除了使人們看到社會上一片黑暗之外,沒有其他作用。有些題材不能寫,如涉及到國家機(jī)密的問題就不能寫。也有些題材當(dāng)時(shí)不能寫,現(xiàn)在能寫。如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shí)期的黨的地下工作,當(dāng)時(shí)不能寫,一寫就暴露給敵人,但現(xiàn)在能寫。所以不是什么題材都可以寫的,要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
趙樹理在一篇《若干問題的解答——寫戲、改戲的標(biāo)準(zhǔn)》的創(chuàng)作談中也說了一番與馬烽類似的話:“有的戲,有時(shí)能演,有時(shí)就不能演,這是怎么回事呢?這要看具體情況。假如到災(zāi)區(qū)慰問演出,我們演的是因天災(zāi)人禍而引起暴動的戲,這戲?qū)?zāi)區(qū)農(nóng)民有什么好處呢?對人民對革命負(fù)的什么責(zé)呢?又如,在歡送新兵時(shí)演出《四郎探母》,這又起什么作用呢?問題在于是自己對農(nóng)村、對革命負(fù)責(zé)了,自己就會發(fā)現(xiàn),并進(jìn)行批判。”
把趙樹理與馬烽的話比照著讀,不是正深刻揭示出了共和國文學(xué)中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嗎?
在1947年召開的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藝座談會上,趙樹理被確認(rèn)為是貫徹執(zhí)行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方向。陳荒煤在評價(jià)到“趙樹理方向”的政治意義時(shí),一針見血地指明:“趙樹理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深刻認(rèn)識,最集中地表現(xiàn)在他說的‘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兩句話上。這兩句話是對毛主席文藝方針最本質(zhì)的認(rèn)識,也應(yīng)該是我們實(shí)踐毛主席文藝方針最樸素的想法,最具體的作法。”endprint
趙樹理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他說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而從《萬象樓》起始,我們從趙樹理的一系列作品中,都能感受到趙樹理創(chuàng)作觀中配合政治任務(wù)的傾向。
馬烽與我談起過他對趙樹理的記憶:“我認(rèn)識趙樹理,是在全國解放初期,那時(shí)候我們都到了北京,雖然不在一個單位,但常常見面,工作上也有一些往來。那時(shí)北京市成立了一個業(yè)余的‘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會,主要任務(wù)是團(tuán)結(jié)一些過去寫章回小說的作者以及曲藝界的朋友們,共同學(xué)習(xí),共同提高。‘研究會還創(chuàng)辦了一個叫《說說唱唱》的通俗刊物,主編是老舍,趙樹理是副主編,我是編委之一。……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夏天,正是大力宣傳婚姻法的時(shí)候,刊物急需發(fā)表反映這一題材的作品,但編輯部卻沒有這方面的稿子。編委會決定自己動手寫。誰寫呢?推來推去,最后這一任務(wù)就落到了老趙頭上。這是命題作文章,也叫‘趕任務(wù)。一般的說來是趕不出什么好作品來的。老趙卻很快‘趕出了一篇評書體的短篇小說《登記》。這篇小說曾轟動一時(shí),很快被改編為戲曲,改名為《羅漢錢》,搬上了戲劇舞臺。……我當(dāng)時(shí)曾這樣想過:如果這任務(wù)落在我的頭上,即使給我半年時(shí)間專門去搜集材料,也不可能寫出這樣動人的作品來。”
趙樹理對于配合政治形勢,配合黨的中心工作有著高度的自覺性。趙樹理在《談“趕任務(wù)”》一文中,就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積極主動自覺自愿地去配合政治的態(tài)度說得更為明確:
每當(dāng)一個事件或運(yùn)動來了之后,會有新的任務(wù)擺在作家們面前,就是平常所說的要“趕任務(wù)”……
“趕臨時(shí)任務(wù)”這個名詞本身已經(jīng)不妥當(dāng)。……如果本身生活與政治不脫離,就不會說臨時(shí)任務(wù)妨礙了創(chuàng)作。因?yàn)槿嗣耖L遠(yuǎn)的利益以及當(dāng)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只是帶著應(yīng)差拉夫的心情去“趕”,而是把它當(dāng)作長期性的任務(wù)去完成。情緒與工作統(tǒng)一起來,不是隨隨便便的應(yīng)付。
認(rèn)為臨時(shí)任務(wù)一來,妨礙創(chuàng)作,原來大作就永遠(yuǎn)不能完成了,這種錯誤觀點(diǎn)的產(chǎn)生,基本上就是因?yàn)樯钆c政治不能密切配合,政治水平還不夠高。所以當(dāng)上級已將任務(wù)總結(jié)指出之后,應(yīng)該是感激才對,因?yàn)樽约翰荒苷J(rèn)識到是中心任務(wù),而別人已替自己指出來,如果認(rèn)識不足,仍然認(rèn)為是趕臨時(shí)任務(wù),那么這是應(yīng)該放下手頭的創(chuàng)作去趕,趕總比不趕好,只要沒有大錯誤,趕得多總比趕得少好,寫得好總比寫得壞更好。……臨時(shí)任務(wù)根本不能趕好,也不見得,看作臨時(shí)任務(wù)也可以寫好的,只看怎樣寫。寫出來不好還不是最大失敗,寫總比不寫好。
自己過去有些創(chuàng)作在寫的時(shí)候就與當(dāng)時(shí)任務(wù)統(tǒng)一,有的是寫過之后與任務(wù)碰上了頭,有的則是“趕任務(wù)”趕出來的。例如《李家莊的變遷》是經(jīng)上級號召揭發(fā)閻錫山統(tǒng)治下的黑暗之后才寫出來,材料早已有,但當(dāng)時(shí)沒有認(rèn)識到揭發(fā)的必要,直至任務(wù)提出后才寫。
寫作品好比種莊稼,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植物與其生長的土壤有很大的關(guān)系。在黃土高原上,很難指望生長出椰子芭蕉,而只能是“滿山遍野的土豆高粱”。趙樹理的局限性也無法超越他生存的這塊土壤。
韓文洲曾多年擔(dān)任趙樹理家鄉(xiāng)晉東南地區(qū)的文聯(lián)主席,后又成為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的副主席,稱得上是得趙樹理真?zhèn)鞯摹暗谝蝗恕薄?962年在中國作協(xié)召開的那次著名“大連會議”上,樹起了一個標(biāo)兵三個樣板,標(biāo)兵是趙樹理,其中一個樣板就是韓文洲的《四年不改》。趙樹理對韓文洲的作品極為欣賞,他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中說:“韓文洲寫的小說雖然有他自己的風(fēng)格,但跟我的風(fēng)格很接近。如果韓文洲的小說不寫韓文洲而換成趙樹理,讀者不會說不像的。”韓文洲以自己對趙樹理的了解,在我對他的訪談中,這樣說到趙樹理和馬烽的區(qū)別:“馬烽和趙樹理不是一回事。馬烽從來是站在黨的立場,是黨領(lǐng)導(dǎo)文藝的干部;而趙樹理從來都是站在農(nóng)民的立場,是個農(nóng)民的代言人。文革中有一句批判老趙的話,說趙樹理成了落后農(nóng)民的尾巴。”
當(dāng)年批判趙樹理的還有一個觀點(diǎn):“反映落后農(nóng)民觀點(diǎn)的一套復(fù)辟資本主義的意見。”
當(dāng)年山西的省委書記王謙,對先后為“山藥蛋派”代表人物的趙樹理、馬烽有一個極為準(zhǔn)確的概括和評價(jià):“馬烽和趙樹理不一樣。馬烽是為黨而寫農(nóng)民;趙樹理是為農(nóng)民而寫農(nóng)民。所以當(dāng)黨和農(nóng)民利益一致的時(shí)候,他們倆人似乎沒什么差別。而當(dāng)黨和農(nóng)民的利益不一致時(shí),馬烽是站在黨的一邊,而趙樹理是站在農(nóng)民的一邊。”
我一直以為,王謙的話是對趙樹理的夸贊。在對趙二湖的訪談中,趙二湖卻對王謙的這段評價(jià),表達(dá)了截然不同的見解。趙二湖說:“王謙對趙樹理的評價(jià),其實(shí)內(nèi)里含有的是批評意味:即在關(guān)健時(shí)刻不能與黨保持一致。
在趙樹理的主觀愿望上,是心甘情愿做一個“為革命拉磨”的牛馬。但他那愛尥蹶子的“毛驢脾氣”,又往往使他在關(guān)健時(shí)刻,不能與上級領(lǐng)導(dǎo)保持一致。
趙樹理說:“我是一個農(nóng)村干部,就得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負(fù)責(zé),不能叫老百姓沒有口糧,牲口沒有飼料。我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就得對黨負(fù)責(zé),不能說假話,下級欺騙上級,地方欺騙中央。”
趙樹理還說:“我看到由于種種不合理的措施,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帶來的危害,和給群眾帶來的災(zāi)難,我不能熟視無睹。向公社黨委、縣委、地委等人提出,可是說不服他們,為這事,我日夜憂愁,念念不忘,經(jīng)常奔上奔下,找領(lǐng)導(dǎo)想方法。但他們都認(rèn)為我是一種干擾。”
趙樹理的奔走呼號,面折廷爭,招致社、鄉(xiāng)、縣三級干部的反感,認(rèn)為趙樹理是多事,挑毛病,神經(jīng)病。
趙樹理自己還說過這樣一個情節(jié):“過去我有老母,借此探親,能了解到許多真實(shí)事情。但我的脾氣急,性情直來直去,知道后就向上級黨委反映,提供基層情況。后來人家發(fā)現(xiàn)了我這個秘密,回家后沒人給我說實(shí)話了。這些事我也苦惱過。為了他們,他們還避忌我。后來我才知道,他們怕報(bào)復(fù)、受治。我得了教訓(xùn),學(xué)了點(diǎn)乖,再接觸知情人,就講究些方法。”
錢理群先生在《趙樹理身份的三重性與曖昧性——趙樹理建國后的處境,心境與命運(yùn)》一文中寫道:
這樣的雙重性,自然也是我十六年后的新研究的基本視角;但在研究過程中,也在其他研究者的啟發(fā)下,我又注意到了趙樹理的第三重身份,即“知識分子的身份與立場”。這樣,“黨——農(nóng)民——自我主體(知識分子)”就構(gòu)成了趙樹理精神與心理結(jié)構(gòu)的三個層面,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糾纏,矛盾,張力,又造成了趙樹理身份與立場的曖昧、模糊,背后是黨和農(nóng)民,作為特殊的知識分子個體的趙樹理和農(nóng)民,以及趙樹理和黨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這本身就構(gòu)成了一種別有意味的豐富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