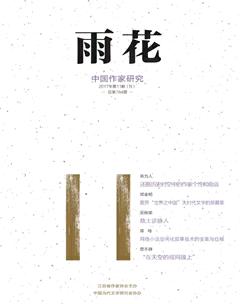“在天空的視網膜上”
思不群
楊隱是我的多年同窗。在詩歌寫作上,他又是我多年相伴而行的同道詩友。人生本無趣,但因為有了朋友,有了同行者,這難挨的時日便多了一份快意,多了一份醇味。當我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十年前我們在蘇大后莊談詩論文、談古論今的一個個瞬間又浮上了心頭,它們構成了我三年研究生讀書生涯最值得回憶的片斷。那時我們還是研一,正在大量惡補理論著作和經典作品,一次次從圖書館搬回一摞摞著作。我們讀累了、讀煩了,就跑到隔壁對方寢室,交流各自喜歡的詩歌、最近讀到的佳作,有時也拿出自己新寫的詩作請對方品讀、挑刺。我們往往是對方詩作的第一讀者,因此,他的絕大多數詩歌我都耳熟能詳。楊隱在詩歌寫作上是虔誠的,也是勤奮的,他像琢玉者一樣,既善借他山之石,又苦練內心之力,孜孜以求,用那些仔細打磨后純美反光的語言,向我們呈現出漢語之美、詩歌之美。
一、細節的暴動
楊隱是一個多愁善感、略帶憂郁的詩人,這種憂郁為他的詩歌帶來了一種基調,一種罩著舊時光的美。這個憂郁的人,睜大了眼睛,靜觀這世界的變幻和人世的悲歡。他的眼睛總是看向低處,看向細枝末節,在一朵花的生長過程中,他只關注“它在一微米一微米地喝水”的樣子,“在一整條河里,唯獨對這一滴水一見鐘情”(《一滴水在流》)。在這個大規模、大數據、大狂歡的時代,楊隱卻情愿把眼光放低,專注于那些小小的灰塵,獨自品味記憶中那些笑臉和汗水、那些思念與眼淚。南朝齊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曾說過:“纖微向背,毫發死生”,雖然他說的是書法,但是我認為它適用于所有的藝術。正是那些幽微末節,顯現出一個藝術家的與眾不同之處,顯現出他獨到的眼光和品質,甚至能讓人將他從眾人中識別出來。詩人都是回憶的俘虜,容易被過去的聲音和瞬間所帶走。詩人消失了,一個個畫面從深海浮出了水面,披瀉著月光散發出美麗和召喚。然而,月亮帶來了潮起潮落,帶來了一次次的沖刷內心崖岸的波浪。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決堤的時刻,他捉筆成文,如一個鬼魂附身的首領,發動那些沉睡的細節舉起草籽與麥芒,聯手發起了暴動,一舉將詩意收入囊中。在這些詩歌中,他用語言的冰塊凍結了時間,并用觸覺的鑷子將時間無限拉長,然后在感嘆與祝酬中將它編織成一個密致、結實的結晶體。
故鄉
首先你得把這個詞
從泥土里拔出來
慢慢的
不要太用力
再用貼身的小刀輕輕賜凈根部
注意:要絕對干凈
殘留一粒泥土也足以擊瞎你的眼睛
然后你坐下來
用一盆清水覆蓋它
看它舒展開身體,慢慢沉下去
這時候,你不要說話
像另一個溺水者
沉默,足以化解你們與生俱來的敵意
《故鄉》這是一個懷鄉病者的自我解剖實驗,他將這些用童年、回憶、親情配制而成的“故鄉”放在顯微鏡下,讓我們看清它的根須和葉脈。故鄉深埋,那些回憶的泥土層層覆蓋,從三十年的泥土和三千里的馬蹄聲中慢慢“拔出”,懷鄉病者驚聲尖叫,“溺水”的恐懼陣陣襲來,在異國他鄉的手足無措中,他獨自撫摸著這溫潤的“實驗品”,陷入了沉默。“故鄉”不是一個地方,也不是一個心理空間,而是一個時間的儲存器,一念孤懸地垂掛在記憶的底部,當我們快步向前時,在不經意間,就會晃動它,甚至在一陣不期而來的創痛中將它連根拔出。幸好,這時止痛藥已經來到:
桃木梳子
從你捉住梳子順發的那一瞬
往后退三個月
那時它還在木匠手里
往后退三年
那時桃花盛開,紅顏遍地
往后退三十年
還沒有你我
它只是一粒種子,在泥土的胎中分娩
詩人多半都是神秘主義者,他們相信臆造的必然,相信身不由己,相信一只隱形之手最初的安排。當初的相遇或許是偶然,但詩人從心靈出發推導出必然的路徑。正如沈從文在《邊城》中說的“凡事都有偶然的湊巧,結果卻又如宿命的必然。”在這首詩中,詩人代替上帝出現,說出了愛的秘密,說出了愛的必然來到。站在今日的晨光中,詩人在一步步地回首,“三個月”前、“三年”前和“三十年”前,一個個瞬間忽閃而過,那仿佛是丘比特寫給他的一封封確認函,并由此回溯,成功地從上帝手中獲得了首肯。詩歌本身很簡單,隨著時間的倒退,那是根據劇情需要進行的重新編排,一幀幀畫面緩緩推出,在最后所到達的地方卻仿佛與出發點天然相連。從詩歌技巧上來說,它是充足而有效的,讓我們在陪同詩人頷首回望中同樣獲得了愛的充注與照耀。2009年我曾寫過一首《童年甕》,與此有相似之處:
從三十歲開始往回
倒退。退一次
探甕取滴原初之蜜,
死皮掉一層,茶味
濃一層。
退到年方二八,總角相伴
天朗氣清,春溪奔流。
或者相反,退到五十歲,風平浪靜。
到最后,速度越來越快。
被一次次掏空的
將甕濃濃地充滿。
《桃木梳子》因為愛的自信給予了詩歌一種正向的力量感和順利到達的暢快感,而《童年甕》因為一種內心的糾纏、因為經驗相互之間的膠著,呈現一種混雜的景象。但是,由于時間的介入和沉淀,兩首詩最后都力求達致一種內在的充盈和滿足。楊隱曾在讀到陳先發的《茅山格物九章》時說:“詩歌就是要說出一些神秘,在情緒、思想的幽微之處發端。”這是楊隱詩歌的特點,他總是從細節出發,在細部慢慢積蓄力量,在細節的相互拱衛、聯結和抬升中,忽然將一種嶄新的詩意端現在人們面前。比如寫那些在街頭攬活民工的《在太平街》:
一張一張被生活擦舊的面孔
聚在太平街的邊上
扁擔、鐵鍬、大錘子
以及洗得發白的舊衣服,以及憨厚的微笑
一絲不茍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