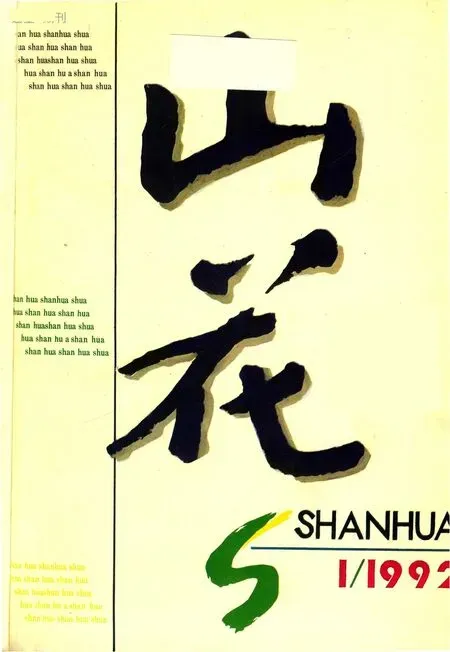失眠癥
盧德坤
1
不夸張地說,三十歲前,我不知失眠為何物。
當然,不是沒有精神勁兒十足而一時無法闔眼的時刻。事實上我得說,那時候振奮的夜晚未免是太多了些。有時候,不是睡不著的問題,是根本不想睡的問題,是如何多霸占一點時間的問題。但是,最后總能自然地沉到夢鄉中去,得到平靜,或以另一種方式延續振奮。
前一陣子,失眠癥出現了。
剛開始時,我誤以為這種睡不著也是一時的“精神勁兒十足”,沒什么大不了。但差異很快顯現出來:明明已經沒勁了,不能堅持了,透支了,那“精神勁兒”卻還在。它有數不清的網格狀毛細管道,傳輸各種各樣的聲音,延綿不絕,使人輾轉反側。我起身,把拖鞋擺一擺端正,將窗簾拉得更緊些。我數數,數不到五十就亂了陣腳。一步一步向上邁的數字,原本似乎能發出不一樣的平和的聲音,但很快被上述更洶涌的、不請而來的聲音給打斷,繼而淹沒——我又被帶到了別的什么地方……
反正大把時間,不如考察一下癥狀是何時出現的也好。
我在一家報社工作,這是一個被認為容易引發失眠癥的所在,雖然我知道有些人睡得很好。
原初,我在國際新聞部,主要工作是發發通稿,偶爾搞些逸聞趣事的編譯。比如,英國有一位健壯的媽媽生了七胞胎。見報時,配一兩張她懷孕時露出的“巨肚”或生產完手擁七胞胎的照片。之后他們會過怎樣一種生活,我們不得而知。照片我們看過了,也就過去了。又如,某位出生底層的彩票中獎者,贏得一筆令人咂舌的巨額獎金,過上了奢侈生活。然而,不過三四年,獎金“燒”完了,刻下生活似乎比中獎前還落魄,整個人看上去就像個撿破爛或睡天橋底的。他是怎么落到這般田地的,只有天曉得。讀者喜歡看這類短時間從低爬到高,又從高處跌落的故事。幸而這樣的人為數不少,因此,相同故事的不同版本登個數十次也不打緊,也還算得上新聞。有時候你不免懷疑,其實他們是同一個人,只不過換了副面孔,再中一次獎,再落魄一次,再上一次報紙。如此循環往復。
工作雖然不甚努力,卻意外得到領導賞識——我不敢說他們慧眼有加,整個人卻因此飄飄然起來——從國際部調到一個新成立的獨立部門,專門負責頭版操作,不用管其他什么雞零狗碎的事。雖有其他部門同事提供素材,但總領其事者只我及另外一位。我和他之前也算相熟的。似乎,責任是重大的。但是,事實上,工作性質并沒什么改變,也就是揀擇一些人們喜聞樂見的新聞、舊事擺在最前面。不過,我喜歡學我搭檔的樣兒,每天都皺著一對眉毛,讓人們去說這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的緣故。那時候,我的睡眠尚可稱得上安穩。
報紙出錯是常事,頭版也不例外。觸目是更觸目一點,人們往往也只一笑置之——雞毛蒜皮出了點錯,也不會讓它錯上加錯,或者錯錯得正。只是,有一天,在一件同樣瑣碎但人們普遍認為有點重要性卻很少有人真正關注的事情上,出了點差錯,事情就有點不一樣了。不巧,我的搭檔那天休息,我得一力承擔責任,雖然第二天我倆碰頭的時候,他的眉頭皺得比以往更深了。
沒想到,遭受領導簡單批評后,人們也只笑笑,好像事情也就完了,一切照舊。但我知道,事情還沒完。至少,我覺得自己發生了一點變化。
同事看我的眼光有點不同了。碰見時,打完招呼,各自離開,我立馬就聽見已經發出的或尚未發出的陰陽怪氣的聲音。我患上幻聽癥了嗎?這時常伴隨失眠癥產生。并沒有,那時候我睡得也還不錯。我的確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他們沒有資格發出這樣一種聲音嗎?當然有資格。我不一定看得起他們,為什么他們一定要看得起我?顯而易見的是,現在,我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那類人物——或者,我原本就是——而且是上不了新聞版面的那種。
凌晨下班回家睡覺,黑暗中開始有些疑影閃現……我一直盯著版面,那個錯誤原本似乎并不存在……疑病癥,乃失眠癥前導,或曰伴當,我大概是“不幸”中槍了。轉念,我又覺得這是必要的“發病”,我因此看到一些原本沒看到的事物,當然也有可能是我因此沒看到一些原本存在的事物。
這樣想著,我自然而然就睡過去了。
隔幾個晚上,我又想,那些嘲諷、欣喜的目光,甚或存在或不存在的加害,其實無關緊要,就像一些人讀社會新聞感到溫馨或惡心一樣無關緊要。那欣喜與嘲諷至少都還是某種表示,說明我是值得被嘲諷、被欣喜的——產生這樣一些念頭,說明我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或愛“作”主義者罷。
真正讓我在意的,是這一錯誤在另一些人眼中仿佛根本沒發生過。就算發生了也是沒發生過的,不覺得有任何表示的必要,而統統只是默默的。
我猶疑著是否需要作一次較激烈的自我批評?最后,我并沒有任何表示。
過一陣子,我又作了另一個他人認為是個笑話的決定:辭職。我有點乏了,不愿再接觸很多人了。當我向領導提出時,他表示非常震驚,似乎事前完全沒想到我有此打算。如果這是演出來的,我覺得他的演技真是沒話說。領導問我為什么辭職?我說想暫時放松下心情,到處看看。這話連我自己都覺得太過敷衍,但領導卻當成是一個理由似的聽下來,并點點頭。過一會兒,他提到之前那次事件,說那其實沒什么關系,而且都過去了。事實上,有些人都不認為那是個錯誤,我不應將此視為恥辱,反該當成光榮。他可以先給我放個大假,等我心情放松完,回來繼續為大家服務。
他為什么在這時候說這樣的話?經過一番快速思量,我決定不僅僅把它當成是挽留我的軟話,我確信,這里面的確有一種善意,然而我無法贊同。我對他說,我心意已決。
我的堅持,讓領導頗失望。他沒再說什么話,爽快答應了,對我微微笑。似乎,我原本不是不知好歹的,眼下才是不知好歹。我露出了真面目。
我得承認,有那么一時半會,我感到不快,自尊心受了點傷。原本想著跟領導辭職得盡量平和,最終卻無法平和——雖然整個過程平平和和的,沒半點火藥味。就算結果仍是一樣,為什么他不多挽回一下?我是把自己看得太微末了,還是太重要了?這是一時無法辨清的。
失眠癥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嗎?我不確定。我傾向于否。
2
我對人說,我想暫時放松心情。我想改變惡劣作息習慣,過朝九晚五的生活。我需多運動,戒煙戒咖啡戒垃圾食品。我想旅行,我想去遠一點的地方。這樣一些話,滑溜,輕易就說得出口,但一開始,我不認為是欺人之談,我也正是如此對自己申說的。
心境的確起了變化,但不能說是輕松的。生物鐘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夜行動物一時難以適應日光。我倒是有一個廚房,書房里有幾本美食書,但我不會做飯,也沒有人為我洗手作羹湯,只能下館子或叫外賣。手機上點點,就有人送貨上門,還能巧妙搭配各種搶來的滿減券,真是時代偉大的進步!無可否認,垃圾食品有垃圾食品的便捷與美味。另外,不知是不是因為慣于久坐,不僅消磨了我旅行的欲望——對旅行的憧憬一息尚存——甚至使我覺得起個身舒個腰都是件麻煩事。
以上種種,總還要跟錢發生關系。多年工作,我存了一點錢。上班時,因社交關系單一,個人無特別嗜好,因此還留有一些。這也是辭職時我看似有底氣的原因之一,當然,最大的底氣是我的幻想癥以及樂觀主義,這是沒有疑問的。有時候,二者為一。
因此,化身中年宅男,是我唯一的看似合理的選擇了。
失眠癥最初來襲時,我否認它是失眠癥。當時是四月初。宅男生活是快樂的,不然哪個傻子愿意作宅男,白白讓世人笑話了,還撈不著半點樂子。睡不著,是樂子來得太快太多太過激蕩的緣故罷,我因此想起年輕時候的日子。看來,失眠癥也好與丟失的青春作伴。況且,我還有件秘密武器,讓我在關鍵時刻睡去,養一點精神,讓自己有繼續“燒”下去的本錢。這件秘密武器與作為幻想家的我有關,也符合宅男的處世之道。
年近不惑,談過幾個女友,多是進報社前的戰果。雖然一只手就能算出總數,但貴精不貴多不是?她們或許已不愿再與我扯上什么關系,因此也不便侈談。說一些個人較深刻的印象,將她們的姓名隱去,或許不至于顯得過于冒犯:
首先浮現在腦海的是甲。奇怪,甲不是那種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以任何標準看,甲長得都低于平均水準,當年我就頗不放在眼里。她主動與我接近,讓我有些意外,畢竟彼時風氣與刻下不一。甲有雙叭兒狗眼睛,時常能專注地盯著人看,似乎打扮打扮,就有一種艷俗的仆傭氣質。有人背地里叫她花癡。她是獨生女,據說家境不錯,偶爾幫你付點錢也是沒問題的,但好像也稱不上大方。我們很快就有些熱絡起來,然而,愈是熱絡,愈不把她放在眼里,倒很欣賞她畏葸以及易受傷害的模樣。
乙是甲的朋友。兩人友情甚篤,風格天差地別。乙長得美,她知道這一點,并時時掛在嘴上說,自我表揚,大概是想暗示我只是她眾多追求者之一罷。她如此坦白,正好說明她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優點,一開始就暴露了一切,因此,愈發顯得妖艷而笨拙,甚至讓人覺得有一種樸實,倒格外誘惑人了。有一陣子,我將乙視為生命中的唯一。在乙眼里,我大概與甲在我眼中的等級是差不多的,但因我功夫下得足,乙又沒什么特別的心眼,便打得火熱。甲知道這件事情,表面看來并不介懷,與乙照常以姐妹相稱,像是后者的仆傭。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從未許諾過甲什么東西,她想介懷,也沒什么資格介懷罷。乙大概認為甲與我只是普通朋友,不可能發生什么關系的,因此完全不在意。有時候,我故意在乙面前說自己與甲打得火熱,乙都笑得花枝亂顫,說我癡心妄想,又以為我是故意逗她的。笑話攻勢是我虜獲乙芳心的招式之一。乙的笑點低,一如其目光淺。某一段時間,我徘徊在甲乙之間,當然更青睞后者,但有一種得享齊人之福的感覺。老實說,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一段時光。我好像在那時候花光了一生的運氣。
丙是唯一一位我進報社后才攀上關系的。我們之間并沒有什么明確的關系,我們之間有一種不明確的關系。丙是一位有夫之婦。她的丈夫我也認識,算是點頭之交。我與丙的關系,原本還淡于我與丙丈夫的關系,平行線一般。忘了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熟絡起來了,但這種熟絡并不是親昵的,而帶有點攻擊性。有一陣子,我們大概是彼此厭恨透了。我想不通世上怎么會有這樣一種女人,她想不通世上怎么會有這樣一種男人。本來,避開點,就相安無事了。大概我們都想去“想通”我們想不通的事情,因此各自進入“敵區”探查,漸漸地,有了一點了解,進而,增加了少許的親昵。作為兩根平行線的我們,在某時某刻,各自發生了一點輕微得肉眼看不出來的傾斜,在極遙遠的看不見的未來,有可能會交叉相遇上。然而,僅止于此。我們沒有牽過手,沒有接過吻,沒有上過床。唯一值得記掛的,只是幾個眼神,幾句話語,幾次不經意間的身體相碰——有一類不受大眾歡迎的言情小說,大概也是這么一種寫法,明明沒什么,倒好上了。很多人都會疑惑,這中間真的存在什么關系嗎?即使是不明確的關系。然而,我確信,我與丙之間是有一種關系的,其程度之深超過我與乙,遑論甲。
或許還可以加上“丁”。丁并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只貓,也不是一個人偶或“仿真人”,更不是一種影子或我腦子里的聲音。毋寧說,她是很多個人、很多只貓、很多個人偶或“仿真人”、很多影子與聲音。她可能是某些在我生命中劃過的流星,也可能是一個我喜歡的女明星、多看了兩眼的路人、商店櫥窗中一晃而過的影子、一個無來由浮現的影像,某種氣氛,等等。
在我怎么也無法入睡的夜里,我命令焦躁不已的自己說:好了,該睡去了!為獎勵你睡去,給你發點蜜糖好了。于是,我召喚甲乙丙丁,好像什么巫師、術士。她們一位接一位來。當其中一位不夠力時,第二位就接著上,總有一位符合要求。記憶棒插上電腦凹槽,我與甲乙丙丁榫卯相接之際,一股輕柔的金黃色的捏一捏還會在上面留下指印的蜜汁,巴黏覆裹在我身上,令人既覺安全又感滿足。“她們是愛我的”,我想。接著,我唯一要做的事便是不再睜眼了,任憑什么力量帶我到隨便哪個地方去。
我不敢一次性將她們全部召喚出來,不是怕自己承受不了,而是怕她們會打架。事實上,像是講好的,她們從未一起出現過。就算我勉力為之,她們也不肯一塊出來,有時候最多只是甲和乙或丁的一些分身一塊來罷了。夠了,這樣已經夠了。
然而,不知道從哪天夜里開始,事情就不再這么順利了。我將甲乙丙以及丁的種種分身依次召喚個遍,依舊無法入睡。我無法再穿上她們賜予的糖衣。事情就好像是,她們之間不打架,她們一個個和我打起架來了。在她們來的時候,隨身自帶的旖旎的金黃光芒中,羼入其他顏色:絳紫、大紅、烏黑……攪得混亂不堪。然后,出現一道熾白的光,周圍的事物統統淹沒在那熾白之中,看不出還有其他顏色。我知道,那是我被喚醒的記憶的尖銳部分。我記起另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從未被忘記過,它們潛藏在旮旯角落里,平常不容易看見。或者,它們就光明正大站在我面前,我卻與它們當面錯過了。大概是需要什么特別的觸媒,我們才能看見。長久的、折磨人的失眠,就是這種觸媒?這么說來,我還得感謝失眠癥了?
我又記起:
乙的身邊很快又出現好一些能把她逗得花枝亂顫的人兒。或者他們之前就存在,只是我沒發現。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么?她早就暗示明示過我了。我總覺得她沒有察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樸實”,而非“妖嬈”,那是我有眼無珠。倒不是說她的“樸實”是裝出來的,是拿來騙人的,讓人以為她才是容易受騙的那一個,而是說她的“樸實”是貨真價實的:她輕易受我的騙,又輕易受其他人的騙,都是真切的;該受誰的騙,就受誰的騙,自然而然的。她的不察覺,正是這種“樸實”本身的體現,她不用特別地去察覺。她受誰的騙更深,她就更愛誰,誰愿意騙她騙得更厲害,或許才是最愛她的。騙子和受騙者早已融為一體,難分彼此,誰也少不了誰。事情就這么簡單,樸實。我比不上人家,便敗下陣來,乙投入了別人的懷抱。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乙了,但也風聞一些她的近況——美人的消息,總是容易流傳開來——據說過得并不幸福。我相信,她并不同意這一點,我也不同意。
甲接下去的發展看似沒什么戲劇性。她升了遷,到別的城市工作。聯絡漸漸少了,偶爾見了面,不特別理會我,也不冷淡,我暗地里發了很大的火。據說經她手的男人絡繹不絕,各式各樣。不管真假,她的確多了一種“大姐頭”氣質。乙后來跟的男人,是甲介紹的,據說是后者經手過的層次較高的一位。甲和乙依然是好姐妹。乙很需要甲,碰到問題就向她請教,甲也樂意奉告,乙也愿意替甲辦事。曾經的三人行,只有我掉隊了。讓我稍稍解恨的是,甲很遲才結婚。見過世面又如何?“大姐頭”又怎么樣?自己的模樣終究沒法變,她也沒去做整容手術不是?可又聽說,倒不是別人挑她,而是她挑別人。最后,甲找了個難看(至少比我難看)的男人,家里倒是有點錢的,用乙的話來說,那就是男版的甲。真是絕配!我也很久沒見過甲了。與對乙的感覺不同,我有點害怕見到甲了,但又希望她能來見我。
重要的事情不妨再說一遍:我相信,我是愛丙的,丙也是愛我的。我們不懼愛上敵人。但我們無法在一起。還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嗎?好像沒有了——有一類受大眾歡迎的言情小說,好像也是這么寫的,但他們最后總能排除萬難,而在一起。在我這里,這“難”像一堵墻,永遠在面前。但是,這真的可悲嗎?我想,我是一個有道德的人,我總是礙于丙已經結婚這個事實,我不愿拆散別人。更可能的情況,是我沒勇氣的緣故?丙是不是正等著我去拆散?愛情面前,談何道德?可是,天假其便,丙自己離了婚,那又如何?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了罷!然而,更細細琢磨,我感到一陣恐懼。眼下,得不到丙,我還有一個借口:她有丈夫。如果她離了婚,我仍舊得不到她,連這點借口也沒有了。還有一種可能,如果得到了呢?那又怎樣?我無法想象我和丙兩個人待在一起的情形。中間好像缺了點什么,我們無法再暢快交流,無法再在無言的情況下也能心意相通。三個人中,二者的沉默不是沉默;兩個人相對的沉默,才是真正的沉默。說到底,丙的丈夫是個重要角色,或者說是愛情的觸媒。重要的事情不妨再說一遍:我相信,我是愛丙的,丙也是愛我的。如此而已。在不在一起無關緊要。可這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嗎?我在這些問題中間打圈,繞不出去。
丁仍舊是安慰我睡眠的最得力之人或物。多虧她,我往往能從黎明開始入睡,一睡還能睡蠻長時間。不過我不確定這是否全部是丁的功勞。黎明未來之前,窗外開始鳥聲啁啾,漸漸地,出現了一些人的活動聲,細微的交談聲,接著,汽車開始發動。這些天光的聲音,一般被認為是干擾睡眠的,可對我來說,它們擾亂了房間里寂靜的飛行著的意義混亂的言語,反而使我的精神沉下去,深落到某個點上。我大概光顧著和我的甲乙丙丁打交道,和世人隔絕得太久了。但叫我輕易走出房間,和他們在一起,又是難以辦到的。或許,我也可以把這些窗外的聲音歸入“丁”的范疇,讓所有的功勞都讓丁領了去。可這是不對的,這些聲音跟丁沒什么關系。最近,這些天光的聲音也漸漸失去“藥性”了,它們與房間里的聲音交融在一起,兩頭夾擊。等到一般人吃早飯的時間,我仍舊睜著眼睛。只不過,我原本面對的是黑暗,現在與之抗爭的是光亮。
我的愛人分作甲乙丙丁,我的仇人事實上也可列為戊己庚辛。既然,甲乙丙丁對我已失效用,那么戊己庚辛會不會意外起什么特殊作用?經過實際操作,我發現,想著戊己庚辛,對安然入睡并無助益,對憤而起床倒挺有幫助的。
顯然,我失去了一些東西,不僅是我的睡眠。我還失去了我的甲乙丙丁。說甲乙丙丁,似乎太缺血肉、人性,人們因此要責我對愛人沒心沒肺了?其實我還給她們取過另外的名字:梅蘭竹菊——這樣的名字似乎更能催人入睡?或許吧。我失去了我的梅蘭竹菊了嗎?自然,她們不在我身邊,這是一種失去。可是,她們不也以一種鬼魂的形式,纏繞在我的身邊,無法散去嗎?可即使繼續糾纏上三生三世,她們的心,我也只有一點認識,或者不如說,全無認識。沒有得到,也就無所謂失去,只是純粹的不可能而已。
我失去的是另一樣東西,我的幻想力,我作為幻想家的資格。那道白光是從哪里來的?這是好事?壞事?這問題也夠我失眠一陣子了。我總覺得,這不是特別好的事。原來幻想家也不是誰想當就能當上的。或許,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甲乙丙丁可供我幻想幻想。
“或者”“也許”“但是”“似乎”……我喜歡這些詞語,又十分痛恨。該死的“或者”“也許”“但是”“似乎”……
或者,這一切都是我想多了,腦子里某個部分出了錯。“她們還是愛我的”,我對自己說,腦子也是可以醫好的。什么甲乙,什么丙丁,什么梅蘭,什么竹菊,話說得是不是過于怪誕、饒舌了?請將這些話當成我的夢囈罷。
雖然我還醒著。
3
厘清與甲乙丙丁的關系,被我視作一種“碎片重整工作”。至此,仿佛終于完成一幅不大不小的拼圖,暫時可松一口氣。我較以前容易入眠了。
但很快,出了別的一些始料未及的事。甲乙丙丁,可視作我精神系統內糾纏不休的影像,接下來的事,我覺得更多地分屬另一系統,兩者之間好像沒什么關系——當然,肯定會有人說,兩個系統是緊密相連的——在其中,我遭受的是某種“物理攻擊”,失血不斷,睡眠因之陷入完全紊亂的狀態。
事情的起因稀松平常。我這人沒什么別的能力,化平常為極端倒不在話下。某天,我想起一本以前讀過的舊小說,想再讀一遍以作消遣。手邊沒有,搜索時發現一個叫“烏有鄉”的網站,在上面以極低廉的價格買到了。
“烏有鄉”是個值得深挖的地方。這是一個網絡跳蚤市場,舊貨集中地,店家林立,可店內訂購外,還有專門的拍賣區,拍品每日換新,東西可賣到高價,也可能讓你“撿漏”。品種不可謂不多,除舊書,還有舊字畫、印章、雕刻作品、明信片、郵票、錢幣、收音機、唱片、手機、手表、碗筷、衣物、兒童玩具、有時間限制的機票、二手車……不久我還發現,以上物品,不少還有全新品可供選擇。眼花繚亂。
不逛“烏有鄉”,我還不知道自己興趣廣泛。我又買了幾本書,接著瀏覽唱片區,不久還發現有各種影碟。年少時,我就有收集影碟的習慣,以小國冷僻電影為主,大部分還留在身邊,收在柜子內層積灰用。當年,有這癖好的人不算少。
如同其余事物,“烏有鄉”影碟琳瑯滿目。在其中一家店,沒翻多少頁面,我就發現一些名頭如雷貫耳而從來沒見過的,且價格都在我接受范圍之內,有些甚至稱得上便宜,不一一訂下,有暴殄天物之感,也對不起自己。但總體數目實在大,重復品種也多,一晚上只瀏覽了三十頁——光這一家店,總共有兩百多頁。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能瀏覽多少算多少罷,我頗為遺憾地想。我還想起,家里的影碟機已經壞了多年,上一次配新電腦時也沒裝光驅。的確,數碼時代,很多東西網上就能看得到,人們大概很快就不知道光驅長什么樣了吧。不過,晚上選的,還是先買回來罷,以后修好影碟機或裝上光驅,就可以大飽眼福。
我得說,在“烏有鄉”逛一圈,我得到一種許久未體驗過的滿足感,躺在床上覺得現世安穩,不過凌晨四點,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光景。恍惚間,我被刺耳的門鈴聲吵得仿佛已經死去。沒人會在這時間找我,事實上,最近任何時間都沒什么人來找我。這鈴聲,大概是從夢境深處傳來的恐怖之音吧,我再睡得熟一點,大概才能將之消除。然而,它持續不斷地響著,襲擊我的耳膜。
我一躍而起,披頭散發,扯著一條只穿到膝蓋的睡褲去開門,是某家快遞員來送我昨天在“烏有鄉”訂購的書。店家真有效率。我怒氣沖沖地簽完字,收了貨,重回到床上。
讓我最憤怒而氣不休的并非身體的疲憊,而是某種被“刺破”的感覺,仿佛我是一個繃緊的氣球,那鈴聲是一根針,那快遞員是執針人。但眼皮實在沉重,我清醒地意識到很快就會重新睡過去,那個被刺開的破洞,很快就能彌縫起來。希望如此。
睡的確是睡過去了。沒過多久,我再一次被相同的鈴聲吵醒。鈴聲持續的時間似乎更長,我的反應也更慢。我再一次被刺破,馬馬虎虎蓄了三格的元氣一泄而光。看一下手機,不過十一點。往常,凌晨四點我能睡著,起碼要睡到下午一點多。開了門,是另一家快遞員來送昨晚我訂購的幾張影碟。剛剛收書的時候,怎么沒想到還有這一出?
眼下,我極需清靜。窗外一個嬰孩牙牙學語,一輛汽車倒車出庫,都能讓我火冒三丈,無法克制。幸虧窗關得比較牢靠,簾子拉得比較深,世界聽起來還是比較安靜而與我無關的。我開了燈,摩挲一陣剛收到的影碟,小心翼翼地擺在架子上。書有精裝平裝,影碟也有盒裝簡裝。這是一套盒裝瑞典電影,深綠色外殼,整齊豎立著,漂亮極了。我想,大概只有我知道它們的價值,“烏有鄉”上其他買家都是不識貨的,只有我會愛惜它們,而它們也會愛惜我。心緒平衡了,我又倒床上去了,一直睡到近下午五點才起身。夢里看到了一片綠。
醒來時,元氣滿格,但不能回想那鈴聲,只能多望一望架子上的收獲。我意識到快遞問題,趕忙去“烏有鄉”看剩下的訂單發貨了沒有,如果沒發貨,請店主在快遞單上標明“下午送貨”。
運氣不錯,剩下的還沒發出來。我發消息給店主,店主很快回復,稱沒有問題,很高興能為我服務,請我別忘記在收到貨后,打個五星,并寫幾句好評。我對店主說,沒問題,十個五星都沒問題。順心之余,我又看了幾頁貨,訂了新產品。也去別的店里看了看,訂了貨,也著重提醒,“下午收貨”,合作愉快。
夜里睡得踏實,完全沒料到悲劇即將再次上演。第二天九點鐘光景,昨天中午給我送貨的那位快遞員,又出現在門口。他說,我光顧的那家店肯定是分批次發貨的,如果是同一個批次,我肯定一次性就能收到,他只需給我跑一趟就好。他的聲音里帶著不耐與憤恨,我終于按不住火氣,指著快遞單一個框格里幾個因復寫而變得模糊的藍字:“下午送貨”,大聲問道:你沒看見嗎?下午送貨!說好了下午送貨!他“哦”一聲,不說話了,黑臉離開。事后,我有點后怕:字跡比較模糊,而當時我正處于眼花耳鳴階段,倒確實看見了那幾個字,要是我一頓光火,大吼大叫,手指的地方并沒有那幾個字或整張單子上都沒有那幾個字,如何是好?
第三天,快遞員似乎長了點記性,一點鐘才給我送貨,雖然那時候我也沒完全清醒,待會還是要去接著睡。交接時,我和快遞員都不作聲。第四天,仍然只九點鐘就來。一切似乎都回到原點。我惡狠狠地盯他看一眼,還沒說話,他硬聲硬氣地先開口了,我忘記了!就把包裹往地上一扔,轉身走了。我連字都沒簽上,在門口愣了一會,灰不溜秋地關了門。后來,我想到,我有我天造地設般的時間表,他們大概也有他們鐵打的日程單,我的強硬要求,亦不啻于對他們日程單的嚴重干擾。第五天,早上十點鐘光景,仍是同一家快遞送貨,只不過換成另一個快遞員,聽說另一位今天休息。我雖感到疲累不堪,但也覺得喘過一口氣來。完全沒有脾氣。
與此同時,我在“烏有鄉”的訂單量直線上升。此外,我還發現了幾家與“烏有鄉”性質相類的網站,多了比價的機會,添了購物的熱情,然而仍無法饜足。我回過頭來,到有國際資本參與、知名度更高、顧客更多、以新貨為主、價格可能更高也可能更低的大電商那里買東西,他們更老道,有自己的物流網絡和售后服務,其中幾家還推出“海外購”服務——我覺得我的眼界更開闊了,只不過面前的天地,廣闊得使人顫栗。我盡量買自己沒有的影碟,但一部電影,買不同版本的影碟,也是有其必要性的,專業人士謂之“洗版”是也。更高清的、更多花絮的固然要買,影像比較原始的、版本較早的也要收,人們說,里面往往藏著舊時光的靈暈。我的舊影碟機還沒修好——我懷疑它已經根本修不好了,零件不再生產,修理師不再干這營生,最后賣給收廢品的也只能得個十塊八塊——也沒給我的舊電腦配個新光驅。我把新買的寶貝暫時擺到架子上,擺不下的,連同一些我買了之后就覺得后悔的,收到箱柜里去。起初還分門別類,但很快作罷,收攏在一處就好。我不知道何時能再打開箱柜,一一品味它們,可能收攏好,從此不再見也不一定。一個意外的收獲是,我在網上看片子倒看得多了。我覺得先把網上免費的看完,再看自己花錢收藏的,才符合經濟之道。
除了影碟,現在我還大量收集舊電影雜志,國內的不說,英文的也收,后來,法文、日文的看見了也不落下。聽說法日電影雜志格調遠超英語國家的,雖然我根本看不懂,但起碼還會翻上一翻,不很快收到箱柜里去,似乎也能體會那種格調是怎么一回事。我覺得,異國文字并未能阻擋我親炙這種格調,而是讓這種格調變得更高深了,更令人有親近的欲望了。此外,我對各國唱片也漸漸發生了興趣,沒人喜歡聽的尤甚……
不管怎么說,它們都使我愉悅,可以抵擋失眠所帶來的小小不快——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房間里的灰塵味會大一點,可反正會被吃剩的快餐湯汁味給蓋過去,融為一體,不分彼此,沒什么差。如果說,真有什么忿恨的話,我只忿恨自己錢賺得太少,不能把我想買的東西全部買下。關鍵時候,得有所取舍。不需要取舍的人生,才配稱得上幸福不是?
我認識了更多家快遞員。有那么一陣子,不理會我的時間表的快遞員都被我看作是命定的災星,前輩子有仇的。如果有幾個包裹是在我睡飽后收到的,我會覺得是前輩子修來的福,偷來的運氣。可是,漸漸地,有幾位快遞員因為固定來,可以說上幾句話了。倒稱不上是朋友,但我們說的話,的確比我手機里留有號碼的幾位親戚朋友說得更多。
有一位相熟的快遞員問我,包裹里是什么東西,看上去挺大的,拿在手上還算輕。我說是影碟片。他撇撇嘴說,現在還有人買這東西呀,網上不是都能看得到嗎?網上都已經看不完了。我笑了幾聲,打發過去。他說,沒準以后可以賣個好價錢。像“你”這樣的搞收藏的人還是挺多的。我沒對他說,我從來沒有再賣出去的打算,我就是想把它們屯在一起,齊齊整整的,看著安心、舒服。后來,又有一位問我相同的問題,我就說是吃的。合理得很,誰不要天天吃?于是,就沒有不必要的下文。
有位好心的快遞員建議我說,如果我還在睡覺,不想收貨,不必理會門鈴聲就是,他們遲點總要給我送的,不然貨沒送到,他們也虧。可我不開門,他們還是會打電話給我,即使手機調成振動,也足以把我震醒。反正已經醒過來了,不如早點收了罷。事實上,我自己不也打心底里希望能早點收到?刻不容緩地,最好是在我下單的那一瞬,東西就能從電腦中的幾個字、幾張圖,變成實物,穿過屏幕,跳到我手里,再納入我的箱柜中,何須要等睡過一個晚上?我想,即使門鈴聲、電話鈴聲、震動聲統統變成無聲,我好像也能聽到那聲音。因此,即便痛苦一些,我愿意在快遞員按響門鈴的第一刻醒來,然后再怒罵幾聲,發泄一下,好像這種快樂且痛的苦境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旁人的錯。當然,話還是要盡量說得和氣一點,不然他們真生了氣,把我的東西搞不見,那我就得不償失了。我說過,我沒有脾氣了。這位好心的快遞員還跟我說,現在又十分流行一種快遞柜子,快遞員把貨物裝在柜子里,再發一條短信給買家,買家可以在忙完事情或睡飽后憑收到的驗證碼去開箱取貨,這樣一來,快遞員和收貨人都方便。可惜我們小區沒幾位像我這樣的買家,不然的話,早裝上了。不過,據他預測,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柜子也會越裝越多的,數都數不清。
可是,到時候即使連貨物柜都爆倉了呢……我又起了新的擔憂。
此刻,痛苦歸痛苦,我相信到最后還是能通過一段段零碎的睡眠恢復元氣的。我終究會活下去的。然而,事情又有了點變化。
現在,我已摸清幾位主要快遞員的送貨時間表。凌晨四五點睡下時,我一直想著九點鐘就有人給我送東西,到時我一定會被吵醒……腦中似乎有一個鬧鐘,擺在一角,雖然很安靜,但像隨時都會“叮叮叮”吵將起來,雖然它看上去仿佛永遠都不會真正吵起來,炸裂開來,因為我在時刻警惕、提防。因為這警惕、提防,我怎么也睡不去了,睜得眼睛干澀,閉也閉不攏,一直到九點,果不其然東西到了,腦中的警戒聲才解除。
我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不用再領教那種“氣球刺破”之苦,雖然換成一種等待的焦躁、不安,以及似乎散布于每一個角落的疲沓。
九點鐘過去了,東西拿到了,我想我終于可以睡覺了……不,等一下,十二點鐘還有一撥不是?如果現在睡去,三個小時后我會被再次吵醒,那么,之前的等待就變得全無意義了。說起來,三個小時也不是很長嘛,我可以再等等……送佛送到西,收貨收到盡……然而,沒有比這三個小時更漫長的時間了。我懷疑在這三個小時里,我身處一個慢倍速率的宇宙中。疲沓在發散,空虛在凝滯:躺在床上,只讓自己更焦躁,不如起身走幾步……沒走幾步,身體似乎整個虛脫了……坐電腦前看一點東西,字符、畫面如跑馬燈般,在眼前晃過,全無意義。茶、咖啡、煙,統統失效。或許,喝點酒,會舒服一些?迷糊之中,一個尖銳的念頭劃過腦際,如果我估計錯誤——以前不是沒發生過——不是十二點鐘,而是下午一點鐘送來,那可怎么辦?鐵打不動的時間表,也會出現誤差、漏洞。我們生活在一個密閉、漏洞、補丁的世界里。打電話過去,盡量讓舌頭不打結地問話,可快遞員的回答往往含糊,十二點或一點,他們說,一定會送到。使命必達。最后,的確在十二點,或十二點半就送到了,但我自己的猜疑是如此沉重,仿佛籠罩了一切,那些到手了的貨物,也變得不像是真的了,或許,它們沒到手時,也不是真的,任何時候都不是真的。也許,我只不過是今天運道比較好一些罷了,還說得上是順利,明天呢?此刻,我極希望能回到之前被吵醒和再次吵醒之間能零零碎碎睡一會的金子般的時光,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回不去了。
我知道這種狀況是一種慢性自殺,甚至是一種帶點兒理性的慢性自殺。不過,像我這樣的“自殺”無趣得很,大概是連報紙逸聞趣事版,也沒資格上的。
我開始注意到身體出現的一些小狀況:我時常處于一種牙齦腫痛狀態。扭曲的夢中,我總感覺有一條舌頭在舔牙齒,牙齒搖搖欲墜,而舌頭還是忍不住去舔它。有時候牙齒被舔掉了,有時候沒掉。或者掉了,重新又長了出來,繼續搖搖欲墜。如此循環往復。清醒的時候,我也不斷用舌頭去舔腫痛的牙齦,牙齒雖然不像會馬上掉下來,但的確有松動的跡象,著實令人擔憂。
有一天起床時,我發現枕頭上,頭發一掉一大片,梳頭時也掉,梳齒間雜草叢生般。我想,不梳頭,大概能減少掉發量,反正沒多少人看見,不必在乎社交禮儀,就讓它蓬亂著罷,反而有一種憂郁的氣質不是?但洗頭時也掉。嚴重時,花灑勁道調小了,光清水從上往下流,也能掉上一茬。現在,網上流行一個口號為“禿頭促進生產”的民間組織“禿頭會”。一些禿頭人士在里面分享癥狀、經驗,討論治療方法以及人生未來,我感覺我可能很快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還不是最讓我煩惱的癥狀。忿恨惱怒的極點出現在某個夏日的某個時刻:我汗涔涔醒來,發現手機按鍵竟然不起作用了,按下去全無反應。莫非潮濕空氣侵入我的大腦之外,還圍攻起堅硬難摧的金屬零件,使它們也敗壞了嗎?一切都全然地敗壞了嗎?不過一瞬間的事情,我抓起手機,往對面墻上狠狠砸去……倒也痛快!不是什么大事,等我精神好一點兒,可以去網上訂購一部新的。
在這一切可見的癥狀之外,天知道還有什么更深的更密不透風的病癥是我不自覺的。說句公道話,似乎不能全怪在失眠頭上。如果人生飲食男女各項都是一場大考的話,我不是每一科都不及格?
不如去看醫生?還是免了吧。一來,我不信任醫生。他們沒有什么特別的難以令人信任之處,他們只是和普通人一樣令人難以信任;二來,我怕醫生一見到我,就宣判我已無藥可救,那實在沒有看的必要。如果能網購安眠藥,我倒想買來一試。我搜索了一下,倒真有人網購安眠藥自殺的。但我搜索了很久,都不知道哪里有賣,當然,最后我真的找到,買到的也可能是假安眠藥,吃了讓你更精神也說不定。我沒有勇氣再探索下去。
剩余的理智告訴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必須發起一項阻斷行動。
網上很多人說,治療失眠,其實很簡單,只要卯足勁,堅持整個白天不睡覺,晚上自然就會睡過去。此后,只要保持相同的作息時間就行了。聽起來,的確是簡單明了,像模像樣,之前我怎么沒想到?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治好我的日夜顛倒,還能讓我變成跟大部分人一樣的人,在白天輕松收快遞,晚上好好睡覺,發黑夜夢才是正經事。
第二天,我下午四點睡去,凌晨三點醒來。過完一段清醒期,喝了好幾杯速溶咖啡,我就想撲倒在床上,一睡了事。期間,我做了好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最后發現都不如死磨死磕,挺著具僵直的身體罷了。一直捱到晚上八點,我才上床。我想,終于,我快要徹底解脫了。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從凌晨三點到晚上八點,十七個小時過去,我必定能一鼓作氣、酣暢淋漓地睡到明天早上六七點,然后,到晚上八九點再睡下去。一切都將恢復正常。我還會是這世界上的人。
我醒過來了,精神奕奕,但窗外還黑著。大概不過早上五點吧,比預料的早一點醒來。不打緊,不差這一時半會,太陽快出來了。一看手機,不過凌晨一點。那一刻,不夸張地說,有一種天崩地裂的感覺。但精神好是事實,我起床,開電腦,看一部電影,心想大概能熬到九點鐘,收第一批包裹,然后再睡。只能如此了。凌晨四點半時,電影還沒看完,我哈欠連天。這樣也好,大概能再睡三四個鐘頭的回籠覺,我就補足了精神——陰差陽錯,這不是跟原計劃差不離嗎,于是欣喜地又上床了。這一覺睡得昏天暗地,醒來時已經早上十點半。又過頭了。罹患失眠癥的同時,我顯然也得了嗜睡癥。一種有關失去的病癥,加上一種有關囤積的病癥。
也可能是我下的藥還不夠猛,應該熬到晚上九、十點鐘再上床的。接下去兩次,我熬了近二十個鐘頭才睡下去——有了前一次經驗,煎熬的痛苦并未減少,而是加倍了——但都是凌晨一、二點就醒過來,清醒一陣,接著又是一番長眠不醒,隔天下午十一點半、十二點半時才有知覺。我知道我的阻斷行動已告失敗。
但并非完敗不是?至少我發現,每次我遲睡兩個鐘頭,都能遲兩個鐘頭醒來。中間那一次醒覺,差不多是一個貪睡的普通人睡一次午覺的時間,只不過我的午覺是在午夜時分睡的,而且對精力回復作用不大,更像是種拖累。阻斷行動,不能一刀切,要慢慢調理。這樣一種緩慢的延遲,如果能通過一個“小周天”,最終或能大功告成:今天我十點鐘睡下去,中間醒一會,隔天中午十二點半再醒,第二天我大可十二點鐘睡下,中間醒一會,隔天下午兩點半再醒……以此類推,我還將在下午四點半、晚上六點半、八點半、十點半,凌晨十二點半、兩點半、四點半醒來,最后到早上六點半醒來。整個過程,大約需花費十天時間。問題是簡單的,仿佛是道小學生都會做的算術題,一目了然。在這十天,我要斷絕網購,實在熬不住,可下一兩單解解饞。多下幾單,好像也沒關系,暫時不付款,累積一下,“療程”后半段,我白天醒著的時間比較多。整個“療程”失敗了也無妨,每天多熬兩個鐘頭,比一次性熬二十個鐘頭人性化,難度系數降低許多。我說過,我還是有理性的,我沒瘋。
事實上,只花了九天時間,我就成功地在下午五點鐘睡去,早上五點半醒來了。中間醒過一次,兩個鐘頭后再次睡去。之后整一個白天,我堅持住完全不睡覺。中間還是有累的時候,但并不特別想念床鋪。之后三四天,我順利地調整到晚上七八點睡覺,早上六七點醒來,中間很少醒來,醒來也會很快睡去。阻斷計劃成功。
沒有比那幾天更美好的時光了,我覺得自己重返了人間。那種瘋魔的停不下來的進度條到這里就快終止了。日出時分,我出去和早餐店的人說幾句話;快遞員喜歡什么時候送貨,就讓他什么時候送貨;晚上,臨睡前,我可以去稍遠一點的地方逛逛,適當的運動,對晚上的安眠更有助益。
經過微調,我一般在晚上九點入睡,早上七點醒來。我的作息時間,與那些身體健康、精神矍爍的老年人一般無二。
可是,我的入睡時間越來越遲。沒過幾天,不到十點,我不會睡去,第二天則在九點鐘醒來。我對自己說,這沒什么,八九點睡覺太早,十點睡覺正好,第二天九點醒來,對一般要上班的人來說有點遲了,對我來說,則是最佳時間。又過了幾天,可能是看多了一點電影,多翻了幾頁雜志,我十一點才睡去,第二天十點鐘才醒來。之后越睡越遲,也越醒越遲。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我的阻斷行動的后遺癥:一旦啟動這項行動,不是我說停止就能停止的。我以為我到了終點站,其實只是經過一個普通的站點。就算真有終點站,也會重新變成起點站,就像一輛繞城公交車,起點站與終點站是同一個地方。
盡管如此,我還是努力作了幾次掙扎,但過了一個月,我終究又回復到凌晨三四點睡去,中午十一二點才醒來。經過幾次打擾,我醒來的時間越來越遲,僅余的睡眠再次呈現碎片化狀態。
在接下來的四五個月中,我的生物鐘一直在循環當中。其中有兩個時期,我再次回到朝九晚十的狀態,但很快再次消逝。
講真,這一切到底有完沒完了?如果是有什么東西在玩弄我的話,也早就玩夠玩膩了罷。或者,我正身處人們傳說的無間地獄?原來無間地獄就長這樣子,好像也沒什么特別怪奇。
氣餒之余,我想起尚可實施另一項阻斷行動。唯一的拯救是自救,我還是能救自己于火坑之中的。之前,我一直在一個封閉系統內耍些小花招,為什么不跳出來,在系統外想想解決辦法呢:既然無法固定我的生物鐘,我至少可以戒除網購癮。據說,只要能保證一長段不間隔的睡眠時間,日夜顛倒也沒什么要緊,至少比生物鐘的完全紊亂來得好。以前在報社,我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那時候,我是個健康得多的人。
我與自己約法三章:不是不準你買,完全不消費了,你肯定也就不能稱之為人了,但一定要控制控制再控制,只買那些真正值得買的東西。其他什么的,就視為糞土罷,終究是與你無緣的。給自己念一段這樣的話,的確起作用。一段時間內,我的訂單數銳減,害得幾個相熟的快遞員都抱怨了。抱歉,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零七八碎的東西不買了,真正值得買的東西倒更值得一買了。以前嫌貴的東西,需要取舍的東西,現在都可以拿下來了,即使銀行賬號的數字天天遞減也在所不惜——哪一天,銀行數字真的見底了,我才真正得到解放的可能也說不準。那么,就讓這一天早點到來罷。這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睡眠質量有所上升。
這是一樁可持續行動,但中間也出了一個小漏洞。有“約法”,就有漏洞,這是近來我體驗最深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在“烏有鄉”拍賣區發現一套不全的原版法國電影手冊,這是極難得的東西,是真正值得買的東西,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識貨的不多,我以為能輕松拿下,想不到晚上九點時,有人跑出來跟我爭。互不相讓,一直過了我的心理價位很遠,還沒能停下來。晚上十一點,價碼還在相持上升中。這是真正值得買的東西不是?那么,就要買下來的。我想,如果對方是個早睡的人,那么他會首先放棄,在不睡覺這方面,我比較有優勢。果然,十二點時,對方停止出價了,也差不多到了我睡覺的時刻。這時候,我才發現,天殺的賣家不知道哪根筋沒搭牢,竟然將拍賣結束時間定在凌晨五點鐘,那時候我正呼呼大睡呢。不能從這會兒等到那時候,不然我的整個阻斷計劃前功盡棄。不過還好,拍賣區設置有“代理競價”功能,我設置了一個高于目前競價兩倍的價錢,然后關了電腦。
自然睡不著,我給自己作很多工作: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不能因為買幾本微不足道的雜志給阻斷了。比起那些電影手冊來,睡眠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而且,你的競拍價已經很高了,沒人比你高了。五點鐘你起不來,人家也不一定起得來。就算起得來了,出了比你更高的價格,就讓它去吧,讓它去吧,不要再執著了……在一片“讓它去、讓它去”的自我催眠聲中,我成功入睡。
猛地,我醒了過來,沒半點預兆的,一躍而起。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手機上如此顯示。開電腦一看,對方果然已在線,好像原本就一直等在那里,與我作對。競價早在三點鐘時,就已經超越了我的設置代理價了。無需思量,戰斗必須進行到底。再出三四次價,對方沒聲息了——這下結束得倒快——東西歸了我。我心滿意足,又倒床上去,出乎意料睡了個好覺。醒來時,我才開始琢磨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時,我是怎么醒過來的?當時,睡著而無夢的我似乎聽到了一種切實的召喚,猶如神諭,促我醒來。
這是一個小小的漏洞,對我的睡眠似乎也未造成什么大的影響。近來,我也睡得越來越好了,但我常常想起那道無由來的“神諭”,覺得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