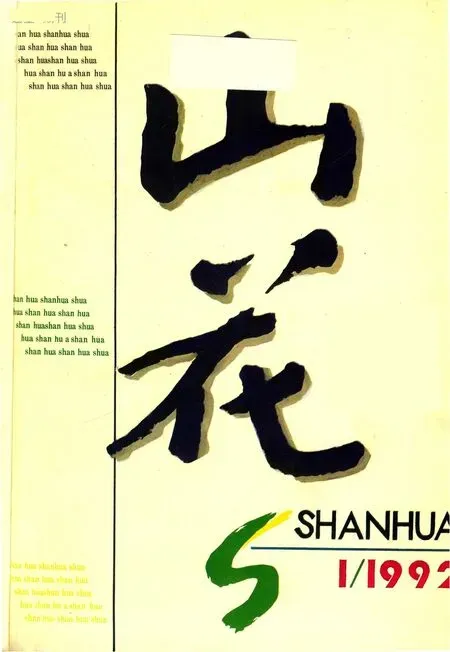磚頭永遠不夠
文珍
“那可以和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分享的天底下最好的事。”
1
作為一個對世界長期過敏的病人,我一直很難找到一種真正的歸屬感。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人面前,老是有一種浮生如寄匆匆過客的錯覺;比方在飯局里,常常因為感覺太過漫長煎熬,面前會悄然出現一小堆粉身碎骨的餐巾紙,碎無可碎之余,還被細心而病態地一個個揉成了細如芥子的紙粒。在無法專心寫作的時候,時常連一張CD都不能耐心地聽完,會不斷切換回我最熟悉的那一首。不斷地replay……重復性壞習慣,除了撕碎紙和單曲循環,還包括一寸寸折斷牙簽、永遠無法留起指甲、控制不住地撕掉還沒長好的血痂……能讓我感到安全的東西實在太少;而這種無聲的焦慮也同樣傳遞給別人某種輕微的不安。
但解決這看似痼疾的神經病的辦法其實也簡單:扔給我一本書,讓我住在里面。
小學時因為爺爺是本地一中的校長,因此奶奶家就在學校教工宿舍。對面鄰居也是高中語文老師,印象中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最顯著的特點是極其舍得給獨生女兒買書。他女兒比我小兩歲,是個有點羞澀內向的姑娘——然而或許也是我沒能努力了解更多她的真實性情。不是不想,是根本顧不上。偶爾去她家作客,我總是忙著坐在地上翻看那些不能全借回家的書,并無心思和她聊天。都是獨生子女,都怕極了孤單,她一開始還很歡迎我去她家作客,漸漸便發現醉翁之意不在己,端的生出許多復雜心緒。首先是立規矩:書許看不許借。不幾日再加一條:看久了也不行,要時不時陪她說話和玩。這也難怪——五歲孩子已經大到足以產生私產意識,須怪不得她小氣。我記得小時候有一種北京牌方便面,不用泡開,隔著袋子捏得粉碎再撕開料包均勻撒上,可以用手拈起碎末當零食吃。小孩子通常沒什么錢,這樣粗糙的吃食已是難得的美味。在實在沒機會看書的時候,我就和她一起共享這挫骨揚灰的方便面,友愛地互相禮讓著,你一口,我一口,這次她買一包,下次我再買一包。可惜談心仍然不多——小孩子差一兩歲本就有代溝,何況我的心思還一直在剛剛放下的某本《奧茲國歷險記》上!說起來,我也是在她家才知道,家喻戶曉的《綠野仙蹤》原來僅僅只是美國作家弗蘭克·鮑姆所著奧茲國系列冒險故事中的第一本,而這個系列總共十四本,全是文字,不薄,而當時我這個小朋友家里居然就有全套——這簡直成了吸引我去她家的最大動力。因為太貴,也因為永遠無法借回家,那段時間去奶奶家的動力都大大增加——奶奶家本來是我視為畏途的,爺爺常不在家,奶奶又兇,家里又沒有什么適合小孩子看的書。
為了看完這個鄰居的那整整兩柜子書,我和那個小朋友一起在奶奶家樓下的竹林里至少分享過三十包北京牌方便面。六歲的她很滿意,有一次還特別抒情地對我說:這個世界上怎么會有這么好吃的東西!怎么會有你這么好的朋友!
而八歲的我卻慚愧地想:天哪,世界上怎么會有比《奧茲國歷險記》更好看的書。
此外,幾乎所有隔壁鄰居家都是我打家劫舍順手牽書的目標。我自家對門住的阿姨據說有肝炎,媽媽曾多次嚴重警告過我不能隨便吃她家的東西,但她家也有過一本非常好看的通俗小說《翼王傘》,鄂華寫的。樓上的小哥哥和我一樣癡迷鄭淵潔童話,我們倆經常一起去街心公園的新華書店買書,也和班上的其他幾個同學分頭集齊了十二生肖系列互相交換。樓下劉雅的爸爸則給她弟弟——并不給她,因為重男輕女——買了一整套的《米老鼠和唐老鴨全集》,很快就被那個小崽子糟蹋得破爛不堪,我也只好忍著對書頁上口水和零食痕跡的惡心,快速翻完了那套畫書。隨媽媽去她相熟的同事家里,她們進行她們的婦女閑聊錄,我則可以趁機翻看那些叔叔阿姨家的雜志和藏書,不過戰果時常都讓人失望,多不過《青年文摘》《佛山文藝》《民間傳奇》之類——和媽媽一樣,他們都是電力系統的工程師或者工人,閱讀趣味通常都不會太高,偶爾能找到幾本《女友》,已經算是意外之喜了。而媽媽出差的日子,隨爸爸去他早先在工廠的徒弟家蹭飯則是最教人失望的,因為通常連《故事會》都踅摸不到一本,最多只有《彩色電視機維修一百例》《31s×2b型黑白電視顯像管說明書》之類,有一次居然發現一本《隋煬帝艷史》,讓我驚喜極了。更多的時候,幾口扒完飯,他們開始在昏暗的燈光下打牌,我寧肯冒著春雨深一腳淺一腳早早回去喂家里的貓。
而我父母都是工科大學生,家里書本來就少,少歸少,至少魯迅的《吶喊》《彷徨》還是有的,《紅樓夢》也有,而且不光岳麓書屋那個最流行的版本,還有全套繡圖本連環畫——我媽也算愛給小孩買書的。從小到大她給我訂過不少兒童雜志,什么《小朋友》啦,《小蜜蜂》啦,再稍微大一點,就訂《讀者文摘》,我最早就是在那上面看到了若干外國微型小說,記得有屠格涅夫的《白菜湯》,還對一個小女孩被謀殺埋在后院的故事印象深刻。偶爾媽媽也會慷慨地給我錢讓我自己去買,說是為了提高作文成績,但我幾乎從沒主動買過任何作文選。有一個雨天,和小哥哥一起冒著牛毛細雨走到街心書店,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書中,居然神奇地找到一本《窗邊的小豆豆》——當年大概這本書才剛剛引進中國,根本不是什么家喻戶曉的暢銷書,我卻拿起來就不肯放下,從此結識了小豆豆和巴學園……我后來一直認定,千萬不可小覷兒童挑書的直覺和鑒賞力,當年的我就一直認為《安徒生童話》比《格林童話》要高級,而葉君健的版本又比其他人譯的安徒生好;鄭淵潔的《魔方大廈》和十二生肖系列明顯優于《童話大王》其他連載;而任何一本童話,如果有不同版本,通常都是任溶溶譯得最有趣……當然受限于閱歷見識,也有過完全失敗的購書經歷,比如有一次就買了一本《自古英雄出少年》,然而里面的少年究竟如何英雄,卻是一個字都記不得了。
2
遠親不如近鄰,家里的親戚家通常更指望不上。
但孩提時印象最深刻的書,卻也有一本來自表妹。書名叫做《洋蔥頭歷險記》。那時候我已經上初一了——我從小讀書早,又是五年制,因此十歲便上了初一,還是愛看童話的年紀。
我對這本著名的羅大里童話可謂是一見傾心。記得初遇是在回湘鄉老家掃墓的途中。旅途勞頓,夜晚小孩子們都被一一安頓在光線昏暗的炕頭上,表妹突然從背囊里拿出這本書來,看了幾頁又不經意地放在一邊。我順手一翻,登時如被一個黑洞強力吸入——撇開情節生動不談,行文的簡練迷人就已讓人無法抗拒。而且翻譯又是那個譯《吹牛大王歷險記》《假話王國歷險記》和寫《沒頭腦與不高興》的任溶溶!里面讓人印象深刻的句子俯拾皆是:
“哪里有洋蔥,哪里就有眼淚。”“‘你說到哪兒去啦,孩子。他爸爸溫和地打斷了他的話:‘監獄里關滿了正直的人。”
在鄉下洗完腳就要關燈。而我為了貪看幾頁書,一直拖到水完全變涼,堂兄表妹們都已經紛紛上床,還在光線昏暗的炕頭愛不釋手。一邊讀,一邊擔心在堂屋聊天的大人隨時走進來催促睡覺。最后二伯母過來關燈的剎那,我正好看到番茄騎士那只可憐的狗卡斯蒂諾在太陽下口渴無比地伸出舌頭來。雖然它是一只壞狗,夢里我卻還在擔心地想,它到底喝到水了沒有呢?
每次回老家掃墓對于嬌生慣養的城里小孩,都算是某種難得的磨礪。吃得遠不如家里精細,肉菜也少,一天只有兩頓飯——早晚各一頓。床上還有虱子,而大人們永遠都在談小孩子們不懂也不感興趣的話題:墓地、老屋、田宅面積、種子和化肥成本……然而這本有趣的書讓所有難以適應的一切都變得可以接受了。我在鄉下那些低矮的紅磚房舍和田壟間走過,會想起南瓜大爺那個因為磚少而不能容身的小房子——數磚頭蓋房的那一節對于小孩子來說太辛酸了一點,卻有某種結結實實的迷人細節:原來房子是用一塊一塊磚砌成的,只要磚頭足夠,房子就可以搭得足夠大!
“我用這些磚蓋座極小極小的小房子,”他一面蓋一面想。“我又不要什么宮殿,我本來就很小。磚不夠,用泥湊。”南瓜老大爺蓋得很慢很小心,生怕他那些寶貴的磚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塊一塊地砌得那么小心翼翼,好像它們是玻璃做的。他很清楚每塊小磚值多大的代價!“瞧這一塊,”他拿起一塊磚來,像撫摸小貓一樣撫摸它,自言自語說,“就是這一塊,十年前我過生日的時候好容易才弄來的。我用積來買雞過生日的錢買了它。等蓋好了房子再吃雞吧,現在不吃也過得了。”他拿起每塊磚都深深嘆口氣。可是等到磚用完了,他還有大大一肚子氣要嘆。他的房子很小很小,像個鴿子籠。
“我要是只鴿子,”可憐的南瓜老大爺想,“我待在里面就非常非常舒服了!”
小房子就這樣蓋好了。南瓜老大爺打算進屋,可膝蓋把天花板一頂,差點兒沒把整座小房子頂塌。
成年后很久,我也幾乎沒有看過比這段更好的形容農民赤貧狀態的描寫。而且還寫得那么隱忍,那么溫柔敦厚。就是這樣來之不易的小房子,最后也還是被番茄騎士搶走當了狗屋——這樣巨大的情感落差,便足以激發起一個小孩的階級義憤來。
因為不斷要走路,不斷見鄉下的陌生長輩,不斷跪下磕頭——在鄉下的第二天我仍然沒能看完書,第三天表妹就向我索要了。千求萬求,她總算同意再續借幾天。我到家后極快地看完了第一遍,舍不得還,帶到學校又打算看第二遍。就是這一念之差惹了禍——帶到課堂上剛拿出來幾分鐘,就被老師發現并沒收了。
這真是始料未及的毀滅性災難。我固然淘氣已久——在初中課堂上不光看書,而且玩玩具。坐我后面的男生有一次忍不住問:你怎么每天帶的玩具都不一樣?——然而錫兵在用課本搭起來的城堡進進出出而從未被沒收,而這本借來的寶貝書卻如此命運多舛。
接下來的幾節課我聽不進去任何內容,忍耐力只夠用到那天的午間休息。老師鎖上辦公室門回家睡午覺去了,教室瞬間空蕩蕩的。等所有人都離開后,我翻進了語文老師的辦公室——從門上方的窗戶進去的,那窗戶對于一個小孩子來說顯然太高,也不知道當時的自己是在怎樣強烈的感情驅使下完成這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老師辦公桌上《洋蔥頭歷險記》和一些其他花花綠綠的被收繳的漫畫放在一起,看上去格外破舊、格外親切。我重新把它緊緊攥在手里,差點兒哭出來。
那樣巨大的狂喜我成年后也沒有經歷過。幾近于失而復得的愛。與之近似的,還有某種求之不得的委屈。
3
還有那些對小孩子而言的禁書們。
我不大記得小學時代自己是怎么弄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的,只記得里面不乏讓人臉紅心跳的宮闈秘辛床笫描寫。躲在房間里看時,只要一聽到媽媽的腳步聲就立刻塞進枕頭下面。后來舉家搬到了深圳,有一次隨父母去一個相熟的叔叔阿姨家,那家也是年輕夫婦,新婚不久,又是夏季,一進門不久我就發現了異樣——男的光膀子坐在沙發上,女的穿一條短短的家居裙,側坐在沙發的扶手上。丈夫的手很自然地放在太太裸露的大腿上,來回輕輕摩挲。他們和我見過的任何大人都不一樣,更親密自然,動作也更大膽。我的父母和房間里的其他大人們都目不斜視,假裝沒看到。又坐了一會,我說要寫作業。那個阿姨便把我帶到他們的書房。福至心靈地,關上門我便徑直走到書架跟前,果然找到了兩本別處找不到的書:《潘金蓮之前世今生》《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又過了一兩年,才知道同一個作者原來也寫了《霸王別姬》和《青蛇》。
就在很短的三個小時里看完了兩本書。房間里定時冷氣什么時候關掉都不知道。只記得武松原來未必全然是英雄,而潘金蓮也未必注定就是蕩婦。
那年大概十二歲。我的三觀受到了嶄新的震動。但很奇異地,我也知道翻案文章其實易作,也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文章。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還可以看什么書?我不記得那一年還看過哪些禁書。很多當代文學作品大概還是去深圳之前在婁底一中的閱覽室里借的。那個時候當校長的爺爺已經去世了。而我渾渾噩噩,抱著閱覽室老師徇私開放給我的圖書室的一大摞書,穿過夕陽照耀下的操場,回到奶奶家里,又坐在床上一本一本狼吞虎咽完。這些書里,包括八幾年到九二年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選,一些著名童話集和一些民間故事,《佛山文藝》仍然是里面出鏡率很高的雜志。我記得有一本是袁珂先生編選的中國神話故事,里面說到豬婆龍就是鱷魚,會用尾巴敲自己的肚子打鼓,非常有趣。另一次無意間讀到一個當代作家寫初潮,用筆極細致大膽,那個時候我自己正是心智未開的懵懂少女,只覺觸目驚心,又模糊認識到所有的女孩,最后都要變成一個女人。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個作家大概就是莫言。而那本書倘若不是《豐乳肥臀》,就是《紅高粱家族》。
后來就隨父母轉學到了深圳。不斷搬家的學生時代,手頭的書總是極為有限,也總是如饑似渴地讀能找到的一切書。因為那些書都不是自己的,因為和書的緣分總是在朝夕之間。
回憶中青春期仿佛總是在孤獨地讀書,和友伴出去野游的記憶很少。一種可能性是四肢不夠發達,因此游戲總是玩得沒有別人好。在游戲中,我感覺不到自己被眾人需要……而看書是相對自足的,近乎和自己游戲。
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沒有什么比讀書更好,更適合獨處時完成。設若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那么,將那些無處安放的時光托付給書本,比托付給任何人事也許都更安全。
到現在我忘記了自己少年時代看過的很多書,卻深深記得那些岑寂無人的下午,就在那個曾經和表妹游戲過的奶奶的房間,坐在床上面向窗戶借著漸漸黯淡下來的天光看書。一本接一本,只要還有沒看完的書,就從未感到匱乏,也不覺得疲憊。
而成年后,手頭永遠有看不完的書,看書速度卻緩慢了許多。
去北京讀研之后有一次回到深圳家中,一本書看了很久都沒有看完,總是匆匆翻幾頁就放下和朋友聚會。那天晚飯媽媽突然說:我覺得你不如以前愛看書了。
她當然不知道那本書就是以難讀著稱的《尤利西斯》。可是她這句話仍然讓我怔忡許久,到現在依然無法作答。
我懷念那個不顧一切翻進老師辦公室里偷《洋蔥頭歷險記》的少女。正如懷念那個恍然不知自己身處對知識最大也最急迫的愛中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