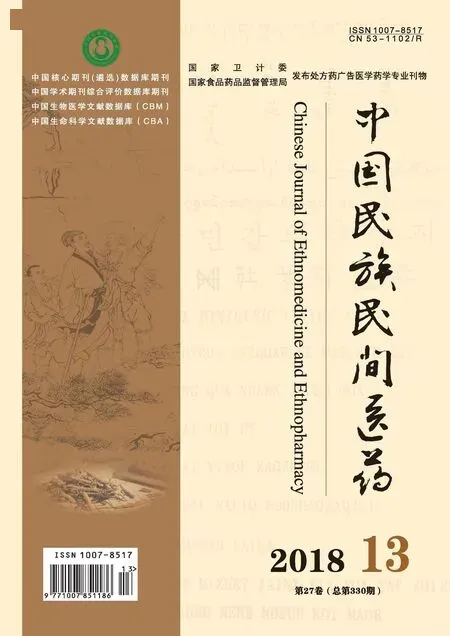丹梔逍遙散治療失眠應用心得
1.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8;2.河南省中醫院,河南 鄭州 450002
失眠,中醫謂之“不寐”、“不得眠”、“不得臥”,是以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睡眠時間及(或)深度嚴重不足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病癥,其病機總屬陽盛陰衰、陰陽失交,其病有虛有實,虛者多由陰血不足、心失所養,實者多是邪熱內盛、擾亂心神[1]。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工作和生活壓力致使很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問題,且以肝郁化火為臨床常見的證型[2]。其臨床癥狀主要表現為心煩難以入眠、急躁易怒、口干口苦,或有胸脅脹痛,舌質紅、苔黃、脈弦數等。丹梔逍遙散疏肝健脾、養血安神,臨床用于此種類型失眠療效顯著,筆者結合病案,將臨證心得闡述如下。
1 組方分析
丹梔逍遙散出自清代薛己之《內科摘要》,又名加味逍遙散、八味逍遙散,是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所載逍遙散的基礎上加丹皮、梔子化裁而成。方中丹皮清熱涼血以清血中伏火,梔子瀉火除煩并能導熱下行,兩者合用以平其火熱;柴胡長于疏肝解郁,使肝郁得以條達;白芍酸甘,斂陰養血、柔肝緩急;當歸辛溫,養血活血,歸、芍與柴胡相伍,使血氣和而肝氣柔,養肝體而助肝用;白術、茯苓、甘草益氣健脾,一取《金匱要略》“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之意,實土以防木乘,又因“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補脾胃以助營血生化,再則借茯苓寧心安神之功以助眠。全方宗《黃帝內經》“木郁達之”、“火郁發之”之意,共奏疏肝健脾、清熱養血、寧心安神之功,由此則肝郁得解、肝火可清,而夜寐自安。
2 病案舉例
2.1 病案1 荊某,女,于2017年9月4日就診,主訴:入睡困難2月余。
初診:入睡困難,急躁易怒,氣短,手心汗出,納食可,舌體胖大,質稍暗,苔薄黃,脈弦。詳查癥狀,觀其舌、脈,證屬肝氣郁結,橫逆乘脾,陰血虧少,火熱內生,治宜疏肝健脾,清熱養血,方選丹梔逍遙散加減。處方:丹皮10 g,梔子15 g,柴胡10 g,白芍20 g,當歸20 g,薄荷10 g,茯神30 g,白術15 g,酸棗仁15 g,夜交藤30 g,夏枯草30 g,法半夏30 g,香附15 g,川芎15 g,貫葉金絲桃10 g。水煎服,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連服7劑。
二診(9月13日):藥后手心出汗消失,煩躁減輕,自覺咽中有異物感,舌稍暗,苔膩,脈弦。上方去當歸,加厚樸15 g,紫蘇葉10 g,薏苡仁30 g。再服7劑,囑其飲食宜清淡。
三診(9月20日):入睡困難較前好轉,心煩、急躁易怒減輕,口干,舌稍暗,苔薄白,脈弦。上方去丹皮、梔子,加丹參30 g,合歡皮30 g,繼服7劑。
四診(9月25日):未訴入睡困難,偶有多夢,舌淡紅,苔薄白,脈弦。上方加紫石英30 g,甘松10 g,繼服7劑。
五診(10月25日):睡眠已基本恢復正常,遂囑其停藥。
三個月后回訪,未訴不適。
按:肝主疏泄,喜條達而惡抑郁,若肝氣失于條暢,使氣機郁滯,“氣有余便為火”,肝火上炎煩擾心神,陽盛不能入于陰則致夜寐不寧;再則,火盛可以傷陰,陰血不足則肝魂無以藏,亦可致心煩不寐。方中柴胡疏肝解郁,當歸、白芍養血平肝,白術益氣健脾;丹皮、梔子清熱涼血,薄荷透達郁熱,夏枯草專清肝火,共除其火熱;患者失眠日久,茯神、酸棗仁、夜交藤合用以加強寧心安神之功;“治火先治氣”,故用川芎、香附活血行氣解郁,貫葉金絲桃疏肝解郁兼能清熱利濕;厚樸、紫蘇葉合法半夏取“半夏厚樸湯”之“辛苦行降、痰氣并治”之用。縱觀全方,肝脾并調,氣血并治,共奏疏肝健脾、清熱安神之功。
2.2 病案2 孫某,男,于2017年7月17日就診,主訴:入睡困難半年余。
初診:入睡困難,心煩急躁,伴頭昏、乏力、頭痛,舌淡紅,苔黃膩,脈弦,平素口服“阿普唑侖片 0.4 mg qn”,既往“冠心病、頸椎病”病史5年余。觀其脈、癥,此系肝氣郁結,氣郁化火,釀生痰熱,蒙蔽清竅所致,治宜疏肝清熱、除煩安神,方選丹梔逍遙散加減。
處方:丹皮10 g,梔子15 g,柴胡10 g,白芍20 g,當歸20 g,淡豆豉15 g,法半夏20 g,夏枯草20 g,丹參30 g,膽南星10 g,酸棗仁15 g,夜交藤30 g,合歡皮30 g。水煎服,日1劑,分早晚兩次溫服,連服7劑。阿普唑侖片(北京益民藥業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11020890, 0.4 mg×20片) 0.4 mg,每晚1次。
二診(7月24日):服藥后入睡困難較前稍好轉,頭昏、乏力較前減輕,仍有頭痛,舌苔薄黃,脈弦。上方加黃芩15 g,菊花15 g,繼服10劑。阿普唑侖片 0.4 mg,每晚1次。
三診(8月7日):入睡困難明顯好轉,未訴頭昏、頭痛、乏力等,苔稍黃膩。患者要求服用中成藥調理,遂予其 丹梔逍遙片(湖南天濟草堂制藥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Z20054941,0.35g×36片)6片/次,每日兩次;疏肝解郁膠囊(成都康弘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Z20080580,0.36 g×36粒)2粒/次,每日2次;阿普唑侖片減至0.2 mg。
四診(8月14日):停服阿普唑侖可正常入睡,囑繼續口服“丹梔逍遙片、疏肝解郁膠囊”鞏固療效。
兩個月后回訪,未訴不適。
按:清·唐容川《血證論》有云“蓋以心神不安,非痰即火。”然痰與火雖系兩端,實可互化,痰郁可化熱,熱盛即為火;火熱灼傷陰津,又可煉液為痰,痰、火皆為陽熱之邪,擾亂心神則致心煩不得眠。方中柴胡、當歸、白芍養血平肝解郁;丹皮、梔子、夏枯草清肝泄熱;患者心煩急躁明顯,故用淡豆豉清心除煩以安神;頭昏、乏力、苔黃膩皆是痰熱上蒙所致,故用膽南星、法半夏清熱燥濕化痰;酸棗仁、夜交藤、合歡皮共用以增強全方安神之力;酌加丹參取其活血止痛、寧心安神之力;因其頭痛明顯,故用黃芩、菊花清上焦之邪熱以利其清竅。全方補中有散,行中有收,以達疏肝養血、清熱除煩、寧心安神之用。
2.3 病案3 王某,女,2017年10月23日就診,主訴:入睡困難伴早醒半月余。
初診:入睡困難,早醒,夜間睡眠2 h左右,心煩急躁,日間乏力,頭暈、頭腦不清醒,胸悶,長嘆息,口服“阿普唑侖片 0.4 g qn”,效差,納少,二便可,舌質偏紅,苔白稍膩,脈弦。詳查病情,審其脈癥,此屬肝郁乘脾,脾失鍵運,濕邪困阻中焦,上蒙清竅,復加郁熱化火,擾亂心神,治宜解郁清熱,寧心安神,方選丹梔逍遙散加減。處方:丹皮10 g,梔子15 g,柴胡10 g,白芍20 g,當歸20 g,薄荷10 g,茯神30 g,白術15 g,黨參20 g,丹參30 g,夜交藤30 g,酸棗仁15 g,柏子仁30 g,龍骨30 g,牡蠣30 g,貫葉金絲桃10 g,香附15 g。日1劑,分早晚兩次溫服,連服10劑,同時配合黛力新片(丹麥靈北制藥有限公司生產,H20080175,10 mg×20片)10 mg/次,每日兩次;米氮平片(華裕制藥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20041656,30 mg×10片)15 mg/次,每晚1次調節情緒,阿普唑侖 0.4 mg,每晚1次。
二診(11月6日):藥后睡眠控制尚可,近日心悸、頭暈,舌尖紅,苔薄白,脈弦。上方加桂枝15 g,甘草10 g。繼服15劑,西藥同前。
三診(11月20日):睡眠一般,飲食、體重增加,心悸,口苦,舌紅,苔薄黃,脈弦。上方去白術、黨參,加生地50 g,夏枯草30 g。繼服15劑,西藥停米氮平,阿普唑侖減至0.2 mg,黛力新片同前。
四診(12月6日):睡眠已基本恢復正常,諸癥悉除,遂囑其停藥。
三個月后隨訪,未訴不適。
按:女子屬陰,以血為本,以肝為先天,肝氣有余則易于郁滯,肝郁則氣盛,氣盛則化火,火性炎上,煩擾心神;再則,木郁乘土,中焦失司,運化失職,飲食、水濕不化,困遏胸陽,上蒙清竅。方中丹皮、梔子、薄荷瀉火透熱解郁,柴胡、當歸、白芍養血柔肝、疏肝活血;患者胸悶、太息明顯,以香附、貫葉金絲桃理氣開郁;其納食減少,故以黨參、白術健脾益氣,培補中焦;患者起病急,病程短,癥狀突出,茯神、夜交藤、合歡皮、柏子仁合用以養心安神,瀉火解郁,再以龍骨、牡蠣重以鎮之,安其神志;后以桂枝、甘草溫通胸陽,緩其悸癥。全方攻補兼施,相伍相成,共達清熱解郁,理氣健脾,養心安神之效。
3 小 結
臨床觀察發現,肝郁化火型失眠的發病人群集中在青、中年患者,這與其學習、工作、生活壓力過大,熬夜過多,思慮過甚,以致肝氣郁滯,疏泄失職有關。《黃帝內經》有云:“肝藏魂,主情志,喜條達,惡抑郁。若數謀不決,或情志不暢,則肝氣郁結,氣樞不轉,欲伸則內擾神魂而致不寐。”[3]失眠的病位雖在心,但追本溯源,實與肝之疏泄正常與否密切相關。肝為剛臟,最易動蕩,其氣以通為順,若情志不遂,氣郁化火,或久病暗耗陰津,陰虛陽亢,火熱妄動,擾亂心神,皆可發為不寐,正如《太平圣惠方·卷四》言:“若陽熱內擾,心陽充實而不入陰分,心火燔灼神明,神明為之躁動不安而不居其所,精神情志則亢奮不寧,使人煩亂,難以安靜入睡,或睡而不實、夢游、多驚、畏懼不安。”此乃母病及子,相生之謂也。臨證應注意辨證論治,詳查病情,對于肝郁化火之失眠證,可以丹梔逍遙散為基本方,酌情加減,以提高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