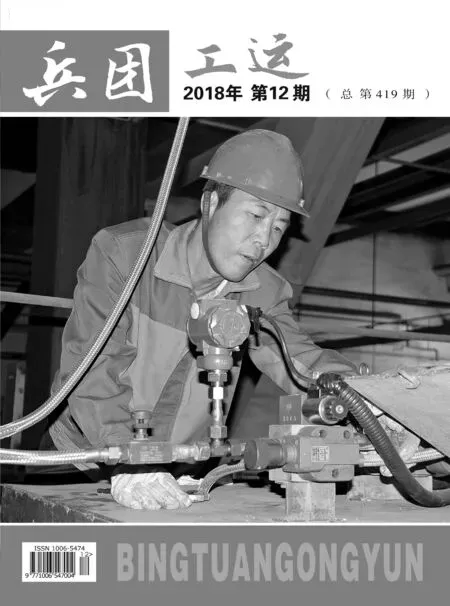軍墾魂
□李江帆
2017年12月的一天,接到師市宣傳部的任務,要為中央采訪團安排兩位老軍墾接受采訪,第一時間,我想起了李慶堂,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軍墾。就在幾天前,我在社區活動中心碰到了老人,他正在和幾位老伙計討論著團場改革的問題,“以前是只揮坎土曼,現在是既要會用坎土曼還要會挑貨郎擔”,帶著河南口音的一句話,點中了此次改革的要旨。
老人在這里已經是三代同堂了,十九歲入疆參加工作,輾轉烏魯木齊、焉耆,隨后按照組織安排,挺進塔里木,在昔日“風頭水尾”的十四團扎下了根,從此再也沒有離開。
認識李慶堂,是在兩年前的一次拆遷工作中,那一年,十四團城鎮范圍內開展危舊住房改造,老人住了三十年的土坯房列入拆遷范圍,工作人員上門做工作,老人表示同意搬遷,但卻遲遲不在拆遷協議上簽字,這讓雙方產生了些許誤會,當工作人員再次登門,詢問老人是不是想得到更多拆遷補助時,老人生了氣,“這不是錢的事!”。
后來,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溝通一番后才知道,老人是舍不得自己收集在門前老院子里的一些老物件,這些老人參加工作以來,逐步收集起來的坎土曼、老馬燈、鐮刀等勞動工具,在老人眼里都是寶貝,沒給這些東西找一個妥善的歸處前,老人還是那句話“堅決不搬”。
此時,老人執拗得像門前的那棵老胡楊樹,“這些東西都是團場的文物,我就想著團里找個地方把它們存起來,給后人留點念想,這些東西有了去處,我才能放心搬家”,老人講起了自己的初衷。環顧四周,老人住在三十年的老土坯房中,可以沒有有線電視、可以沒有自來水、甚至可以沒有電,但卻唯獨少不了這些老物件、老伙計,在這個問題上,老人絕不妥協,和不遠處那棵挨著沙丘長著的胡楊一樣。
在之后和老軍墾這個群體接觸多了,才知道這股較真勁是他們的共同秉性。
謝運華,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入藏戰役的老兵,1956年回家探親的他,聽說部隊要開拔去新疆,想也沒想,就踏上了追趕隊伍的路,一家老小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已經是一年之后,此時,他已經在塔里木深處的十四團開了半年的荒......
“有一次我和他帶著大家去上工,走著走著,我看他頭上都是汗,腰也直不起來,就過去問他怎么了,他說肚子疼,去解個手,讓我先帶人去勞動,大概過了二十多分鐘,我一看他還沒回來,覺得不對勁,就往回走去找他,結果看到老連長把坎土曼一頭頂在胡楊樹上,一頭頂在自己的胃上,汗水在他腳底下濕了一片,后來才知道,那是在戰爭年代留下的病根,這個辦法是他的‘止疼藥’”,謝運華曾經的老搭檔胡建清回憶老連長時邊說邊敲茶幾,“他真硬,跟這茶幾上的石頭一樣”。
多年后,退休后的謝運華因胃癌去世,曾經的老戰友、老搭檔胡建清一路扶棺,送老連長最后一程,從此后,“我再也沒見過這么硬的人”。
每年的清明節,十四團黨委都會派水車從十四團團部出發,往一個叫做“七零三”的地方灑水,“七零三”在這一天,成為了所有十四團人洗滌靈魂的所在。
“七零三”,在十四團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每一個生活在此軍墾人的魂之歸處,在這塊被濃密的胡楊林覆蓋的地塊上,一塊塊開裂的胡楊木板、一節節水泥殘柱散落其中,但更多的還是一個個隆起的土丘,唯有胡楊作伴,“這下面有十四團已故的政委、團長、營長、連長、排長,還有普通戰士,在地底下,他們的編制也是完整的”,在此執行守墓任務的李栓柱講道。
每到夕陽西下,陽光穿過濃密的胡楊林,我似乎又聽到了那聲集結號,昔日的荒原成了綠洲,軍墾人也成了胡楊。
2016年,十四團建團五十八周年,這一年十四團團史館正式開館,在這個不大的空間里,一顆巨大的紅色五角星鑲嵌在天花板的正上方,十四團的前世今生在環形的大廳中一一展現,行走在這其中,有兩鬢斑白的老者、有風華正茂的青年、也有剛剛學會走路的孩童,當問起其中的一位老軍墾,這個博物館建得怎么樣,老人用樸實的語言回復我“好、好、好”,隨后,在一盞老馬燈前陷入了沉思。
一盞盞布滿蛛網的馬燈,一把把銹跡斑斑的鐮刀、坎土曼,一張張發黃卷邊的糧票、布票,靜靜地向人們訴說著逝去歲月里的軍墾故事,軍墾人老去了,軍墾魂卻永遠留在了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