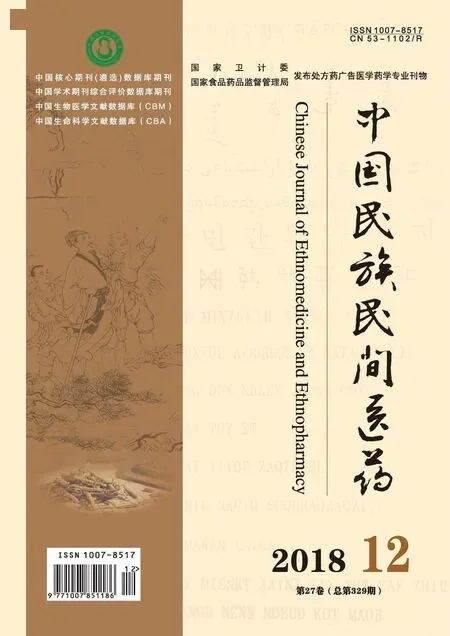從民族藥中尋找新藥到中藥現代化
——曾育麟民族藥學理論構建及其實踐
云南民族大學,云南 昆明 650031
1983年,在云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召開了首屆全國民族藥學術會議,中國藥學界的一個新名詞——“中國民族藥學”在本次會議正式誕生,這意味著一個新的醫藥學研究領域將被開拓,那就是中國民族醫藥學。中國民族醫藥有別于傳統的漢族中醫中藥,它自成一體,別有系統的觀點,終于得到了學術界的完全認同,可見此次會議的重要意義。
1987年,在印度舉辦的首屆國際民族醫藥大會,曾育麟《從民族藥中尋找新藥》一文引起各國與會學者的普遍關注和贊揚,其也成為云南省民族醫藥研究的先行者與奠基人,繼而越來越多的學者踏上了挖掘、整理、開發民族醫藥的征程。跨世紀以后的十年,民族藥一詞已經得到相關學科的普遍認可,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學科研究及教育體系,也為大多數民眾所接受和理解。2017年7月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明確:“中醫藥,是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醫藥在內的我國各民族醫藥的統稱,是反映中華民族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認識,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獨特理論及技術方法的醫藥學體系。”這標志著國家第一次從法律層面明確了中醫藥包括民族醫藥的重要地位、發展方針和扶持措施,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故而有必要對民族醫藥學科形成發展做出一些歷史性的回顧,也對隸屬于中藥這一領域中的民族藥現代化進行探討。
1 篳路藍縷:《玉龍本草標本圖影》及其他
與《滇南本草》相比,《玉龍本草》的知名度遠遜,但內行人士皆知云南滇北(西北)地區本草匯聚編著最重要的是《玉龍本草》。正是這一南一北兩部本草,撐起了云南民族藥用動植物譜系的主體構架。目前能找到最早、最可靠的版本是于1959年出版的《玉龍本草標本圖影》[1](以下簡稱《圖影》),這部一改李時珍《本草綱目》式的傳統本草書寫結構模式,對古老的《玉龍本草》中所收集的藥用植物,以現代植物學的編寫方法進行了重新分類和鑒定,并采用國際通行的標準方法,用拉丁文對植物進行命名,以滿足專業性的科屬比對需求,且標本的制作十分規范,體現了編著者高水平的專業素養,以及所具備的現代西方藥物學科的操作理念。《圖影》共收入藥物標本328種,其中圖影的制作,達到了圖文并茂,十分有利于讀者的辨識和理解,這是傳統本草書籍所不具備的功能。《圖影》的出版,不僅是對瀕于毀滅的納西族古老民族醫藥典籍的整理和搶救,更是運用現代的藥學理論對傳統藥用植物與用藥方法進行標準化整理的一個成功嘗試。這種以西學手段灌注于中國古老醫藥典籍整理,并由此產生對傳統藥用植物與用藥方式應該要有標準制定的想法,在當時實屬超前的理念,與曾育麟的求學經歷和就業時局緊密相關。
曽育麟(1930-),字憲宗,號仲平,四川成都人。1947年,17歲的曾育麟考入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1952年,畢業留校的曾育麟響應號召,主動申請赴云南邊疆工作。當時全國行政轄屬以地區劃分,云、貴、川三省按軍制劃為大西南局。曾育麟由大西南局分配到新建的云南省藥品檢驗所(以下簡稱藥檢所)工作,擔負起了云南區域內的民生用藥、醫療用藥等質量把關的重任。
作為技術帶頭人,曾育麟著手規劃藥檢所的格局和建制,設立各個不同的功能部門,除了主導這些行政管理的布局外,面對當時整個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實行的最嚴格的經濟封鎖,全國西藥制品嚴重匱乏的局面,如何保證云南地區醫療看病用藥的需求?如何保證普通民眾的用藥安全等問題,成了他工作中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百廢待興之際,他做出的第一個決策就是做市場調查,掌握第一手藥品供給狀況的材料。在調查中曾育麟驚訝地發現,本地中藥材之豐富完全能滿足民眾的基本醫療需求,甚至某些需要抗生素類藥品治療的疾病,也可以嘗試通過云南的地方藥材來治療。但同時他也敏銳地看到當時存在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云南藥材市場管理十分混亂,藥材真偽的識辨和使用都是經驗性操作,全無標準可言,這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個接受過現代西方藥物學專業學習的研究者,曾育麟十分清楚,沒有實地勘察和實物比對的經驗,沒有實驗室里確鑿和嚴格的分析數據支撐,藥材真偽辨識的手段,藥物使用安全標準數據的獲得都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為了填補自己在地方藥用植物知識上的空白,他常背著一部老舊相機,走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踏遍云南的山川河流,訪問上百位藥農、藥工,相機有故障了就用手繪植物圖樣,從根、莖、葉、果、子的形狀,到界、綱、類、科、屬、種的準確鑒別,再到形、色、味、效的詳盡記錄。終于完成了滇北(西北)地區的藥用植物典籍——《玉龍本草標本圖影》的編著工作,成就了中國第一部圖譜式地方本草典籍。
然而,《圖影》的出版只是他所從事的民族藥研發事業開端的一小步。與此同時,曾育麟主要參與的另一項工作,即對云南白藥原料調查、配方核實,以及適合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所需要的藥品標準制定、原料供給可能性等重大問題的論證。該項工作因周恩來總理的過問,成為當時云南省醫藥工作中的一項大事。1958年,《圖影》還在編寫中,而“云南白藥原料金鐵鎖的研究”、“熱帶藥用植物的調查”兩個項目已完成,他由此涉入對云南彝族醫藥體系的深入探查,獲得了云南熱帶地區藥用植物的第一手資料。這一年里的勤奮工作,多篇優質學術論文的發表,使年僅28歲的曾育麟榮獲1958年“全國醫藥衛生技術革命大會成果獎”。以此為始,他研究成果多樣而卓著,迅速成為中國藥學界的新秀而聲名鵲起,影響漸大。
入行六年的曾育麟,已對云南各民族醫藥文化歷史的鉤沉、研究與實驗、藥材的鑒別與有效成份分析、藥品的標準化制定等有了一整套的思路。他意識到這是十分龐大的事業,他必要窮盡一生把民族醫藥這一個寶藏挖掘出來,為人類健康服務。論文《云南三分三的調查和生藥學研究》[2]、《云南金剛散的調查研究》[3]等多篇優秀論文的發表,填補了藥用植物原產地研究的空白。而《中藥形性經驗鑒別法》[4]的出版,基本解決了藥用植物采集收購中出現的辨識、誤判等長期疑難問題。
2 繼往開來:《中國民族藥志》及其他
20世紀80年代,曾育麟主編的《中國民族藥志》(一、二卷)[5]的問世標志著“民族藥”概念的規范界定和藥物標準化進程的跨越發展,這是民族藥走向現代化,走進國際視野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此之前,曾育麟參加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977版)時,他以扎實的文獻材料為基礎據理力爭,促成國家級藥典對民族藥物的收載,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國家藥典中第一個擁有民族藥標準的國家,結束了民族藥沒有法定標準的歷史。為了完善各民族藥的標準化,他倡導和組織有藏民生活的六省區民族醫藥工作者,共同完成了《藏藥標準》(1998),收載藏藥材174種,藏藥成方290個。主持編制了《云南藥品標準》,收載了包括20個民族的75種民族藥標準。民族藥標準化的實現,為民族藥的新藥開發和市場運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技術性和法定性支持。
曾育麟很清楚,民族藥要被充分認識和研究挖掘,除了繼承,更重要的是培養研究型人才。1985年,為了恢復和重建云南中醫學院中藥系,曾育麟被調入高校,他由研究者轉變為教育者,由實驗室走進了課堂。從人員調配到實驗室規劃,從財務預算到學期課程安排,事無巨細,全身心投入,廢寢忘食。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建設了民族藥教研室,他親自編寫《民族醫藥概論》講義(后以《民族藥學》定名,在1989年由云南中醫學院作為專業選修課教材印制),為學生講授關于民族藥的基本概念和常識,云南中醫學院亦成為全國首家專業培養和系統教授民族藥理論課程的大學。在教學過程中,他對以往民族藥用植物調查、用藥經驗總結、方劑的實驗分析等積累下來的大量資料,做出具有理論意義的梳理總結,通過客觀而具有深度的審慎思考并提出以下觀點:
第一,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醫藥學傳統和體系,這個體系的構成是兩大部分:即有記錄的“文傳民族醫藥學”(Ethno medicine on word traditions),以及“口承民族醫藥學”(Ethno medicine on oral traditions)。作為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這兩個構成部分都應當予以一樣的重視。正如他為《土家族醫藥學》一書中所作的序所言:“任何一個民族有沒有本民族的傳統醫藥學的問題,尤以對沒有本民族文字者而言,回答應該是肯定的。民族、歷史、醫藥學總是密切聯系著的,只承認其中之一或妄圖否定其中之一都是無望和荒謬的。最終讓有志者用事,去一個一個地證明吧,像這本《土家族醫藥學》[6]那樣。”基于這樣的觀念,他不僅在文章《民族藥的概況及展望》[7]中闡釋其觀點,更是身體力行,主持云南少數民族醫藥傳統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如《檔哈雅》(傣族)[8]、《聶蘇諾期》(彝族)[9]、《德昂族藥集》(德昂族)[10]以及普米族、水族、基諾族和佤族的醫藥書籍。每個民族在本民族的醫藥史上都大量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發展痕跡,不惟漢族醫藥才有。培養民族醫藥人才,也不僅僅是單一向度的線性傳承,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價值發現,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亦屬于中華大文化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應因社會發展的時間延展或是教育引導的偏誤而湮沒不存。
第二,民族醫藥與中醫藥體體系的差異存在,不會形成中藥與民族藥的對立,相反二者是互補的。大量的實證材料表明,中藥與民族藥的使用情況大相徑庭,很多藥用植物、動物和礦物,中藥不用的民族藥離不開,中藥少用的民族藥卻常用;同樣的藥物中藥使用的部位、方法、病癥在民族藥使用中相似者少,相異者多。這就給后來的研究者對病理、藥理同異性進行剖析的科學性驗證、提煉、精細化等方面,提供了巨大無比的研究空間。這既能彌補中藥藥用范圍的空白,也是以天然藥物抗衡化學合成藥物不利因素的重要法器。由此,從民族藥中尋找新藥的主張便應運而生。當然,藥學是一門最客觀的實證性科學,再好的主張也必須要付諸實踐。從民族藥中尋找新藥的實證有:從納西族藥三分三中成功提制出硫酸阿托品,快速終結了我國依賴進口的歷史;從傣族和漢族均使用的“臭油”中研制出中國稀缺的新型栓劑基質——香果脂,再次填補空白,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歷年版均對其收載;從民族藥用植物蘿芙木中研制成功當時緊缺的高血壓用藥降壓靈;還有一批原料名稱仍在產權保護有效期內,以民族藥為基礎研發出來的新藥,如可供口服亦可外用的孔雀萬金油,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傣血通,防治中風的龍燈膠囊,主治肝膽病的青葉膽片,用于放化療和白血球降低癥的升高白血球用藥的千金藤素片。而諸如血塞通、昆明山海棠片、益脈康、治近定眼膏等,已成為了常用藥而為民眾所熟知。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便有了1987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首屆國際民族藥大會上獲得金質獎章的成果形成,即《從民族藥中尋找新藥》論文,引起了世界同行們的共鳴。
在扎實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經過一年的教學科研建設,云南中醫學院中藥系在1986年成功申辦了民族藥碩士研究生學位點,并在同年招生,成為當時云南省高校為數不多的碩士研究生培養單位,這為民族藥的發展做了高級人才的儲備,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民族醫藥研究者建立一個學術園地。另一方面曾育麟積極籌辦學術刊物,落實刊物的批文、資金、編委會人員構成等。1992年7月,云南省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會主辦的第一期《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正式出版,并向國內外公開發行,曾育麟為該雜志的主編,一干就是十幾年。《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的成功出版發行,為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民族民間醫藥的學術研討提供了平臺。
專業人才的培養、系統理論的構建、學術刊物的創辦、藥用價值產品的研制等,是民族醫藥研究領域不斷壯大的重要因素。民族醫藥踏實地服務于萬千民眾的治病需求,在近半個世紀的奮進和努力中,成為了一個新生的學科領域,得以淵源流傳,造福于民。
3 推陳出新:《向歷史要藥》及其他
曾育麟發表于1986年的論文《向歷史要藥》[11]在當時并未引起多少關注,如今再讀這篇論文,不難發現文章中涉及到今天一個非常重要也很急迫的問題,那就是藥用資源嚴重匱乏當如何解決?這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發問,它充分顯示出一個科學家所具有的敏銳頭腦和前瞻性眼光。曾育麟在文章中指出,面對天然藥用資源因過度開發和環境污染,尤其是土地污染,山林水土流失,藥材資源的供給能力日漸萎縮的狀況,當可從兩個方面尋求應對之策:
其一,從歷史資料的存留中深度梳理,把大量可作為藥用的植物、動物、礦物資源挖掘出來,對目前藥用資源可起到有效的查漏補缺的作用。文章通過大量的資料列舉,證明了歷史典籍記錄留給今人的很多利好,同時也提醒今人,應繼續整理和出版還在流失的醫藥典籍,記錄現在的民族民間醫藥行跡,對歷史做出有效性的延續,因為今天是未來的歷史。
其二,指出采用人工培植藥用植物的可行性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人工培育動植物,規模化種植,雖說是一條滿足藥品工業化生產,規范市場化運作的最佳途徑,但是對于培育中可能產生的藥性衰減,種植中出現的品種退化,土地污染后置影響等問題,都須要有足夠的認識,要保持高度的重視,不能僅為各種利益的所獲,而放棄了藥品本身是一種特殊商品的基本概念。科學的培植,應該更多向歷史學習,采用傳統方法中的科學理念和方法,從歷史的經驗中汲取養分,為規模化種植服務。
這篇論文雖然簡明,但內涵厚重。充分說明隨著天然藥物越來越被醫藥工業和藥品市場所青睞,新藥研制課題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態勢已經形成。換言之,研究一個新藥,不僅是藥物本身的基礎研究、臨床功能研究、毒理藥理研究,還要考慮產地環境變化,考量野生與人工培植的同異性等因素,重視生產工藝的科學化等。例如,在燈盞花素的發現過程中,曾育麟通過普查,發現了苗族、彝族、白族、納西族和藏族都有使用植物燈盞花入藥,民間醫生入藥主治口鼻歪斜等中風后遺癥,普通人家則當作菜肴食用。通過實驗室提取了燈盞花中的重要成分燈盞花素后,藥理實驗并無效果。面對失敗,曾育麟不放棄,勤思索,再次奔赴丘北,一次次走訪當地民間老醫生,終于了解到燈盞花在民間使用須是用油炒過方才有效。他藉此認定,實驗失敗的原因應是提取方法的問題。之后,根據他的提議改用脂性溶媒獲得了成功。而今,燈盞花素片劑和針劑均成功上市,并成為心腦血管疾病的搶救用藥之一。由此可知,對民族藥研究外延的關注,不僅是一個研究方法和路徑的問題,更是促使中藥走向現代化的基礎性問題。
如何去實現中藥的現代化?曾育麟認為,從向歷史要藥入手是重要的途徑。首先,對固有的中藥內涵進行更新擴容。21世紀的中藥概念,應該是包括中華各個民族藥的藥用藥方內容,而不再是僅有漢族一脈的藥用藥方。其次,僅依賴傳統的原料構成和制作工藝已經很難滿足當代人類的用藥需求,中藥現代化的問題,必然成為新藥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而所謂的現代化,不僅只是設備和制作的先進,更是劑型、檢測標準與手段、效用組合與提取工藝等富含科技含量的高水平成果的集合,且一切的研究成果還必須能夠充分轉化為市場所用,能產生真實的社會效益,能夠真正服務于人類的健康。
曾育麟從他的知識結構中“萃取”現代藥學理論的科學思維和理念,一方面繼續收集、整理、出版《中國民族藥志》[12],另一方面延續對藥用成分進行有效性獲取的研究工作,以期能符合現在醫學臨床使用,《滇產雪上一枝蒿的生藥學研究簡報》[13]、《滇產胡黃連與進口胡黃連化學成分的比較》[14]、《傣藥“埋嘎篩”極其制劑的研究》[15]的發表,“降壓靈的研究(生藥部分)”、“一種新的國產的栓劑基質—香果脂的研究”、“進口藥材國產資源的調查研究”、“云南白藥的研究”、“腐植酸鈉的研制和臨床應用”、“竹紅菌治療外陰白色病變和疤痕疙瘩的研究”、“尖吻蝮蛇去纖酶的研究”、“豆腐果甙的研究”、“抗癌藥順鉑的應用研究”、“三七總皂甙注射液的研究”等課題的研究,一系列新藥的成功上市,碩果累累,為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研究新藥的同時,曾育麟對藥品質量的檢測手段更加重視,尤其對于知名的藥品品牌,更要有近乎苛刻的完善的科學檢測手段,才能保證有不變的質量和恒久的口碑,“云南白藥質量標準和檢驗方法的研究”的成功,就是優秀的案例之一,它開創了以藥品自身為檢測標準的先河,改變了以往以其他物質作為標準的慣例,這是一個首創,解決了處方不能公開,無法公開檢測各項物質的難題,如今此法依然沿用在藥檢工作之中。
4 小結
總之,曾育麟對于民族藥領域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做出了開拓性和基礎性的巨大貢獻,被尊稱為中藥學家、民族藥學家。在結束本文之時,筆者借用曾育麟先生在他的著作《滇人天衍》[16]中的“史話”來進行總結性的陳述:
我國是一個沒有中斷過歷史進程的文明古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與民族心理、性格融為一體,滲透在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醫藥也不例外。傳統像一張細密的網,制約著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也必然制約著自身的醫藥傳統,對各民族的醫藥史產生著影響。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行程中,云南的26個民族為了生存和繁衍,都經歷了與自然和疾病作斗爭的歲月,由此而逐漸積累和形成了本民族的傳統醫藥學。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歷史悠久的醫藥史,記錄下了各民族人民在醫藥學方面不斷向前發展的每一個歷史腳印。
由于各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和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同,對疾病的認識有先后,醫藥學的形成也就有快慢。從目前看,各個民族的醫藥在理論上就有所差異,實踐上各有高招,各具特色。有的民族的醫藥學理論已自成體系,十分成熟;有的民族還只停留在操作階段,尚未上升為自己的醫藥學理論;有的民族則因醫和藥的發展不平衡,即藥早于醫,藥多于醫,便借用其他民族的醫學理論來闡釋自己民族的用藥原理。但不論情形怎樣,云南26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醫藥文明和歷史。